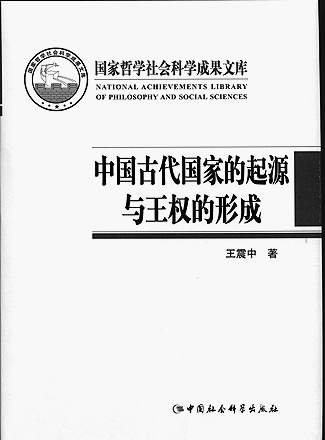 数千年来,国家起源以及权力形成等关于起源的话题一直都是哲学家头脑里一直盘桓不去的问号。《韩非子》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是古人对社会复杂化的感性认知。西方哲学家如黑格尔、康德等都有着自己关于社会起源及演化的整体图景。随着近代科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兴起,学者开始利用考古学、民族学材料解释古代社会,并形成了一系列的解释模式。著名的如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野蛮、文明等不同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接受了这样的社会复杂化演进几个时代的划分,并做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等阶级和国家起源的理论创新,对各个时代社会复杂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为学术界广泛采纳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艾尔曼·塞维斯的学说,他将社会复杂化过程分为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等四个阶段。以上的学术观点扼要概括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形态,学术上称之为“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以及“社会复杂性演化”(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omplexity),它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一直都很具吸引力,成为解释社会演化的便利工具。 然而,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六个地区之一,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深入西方学者的视野。西方学者依据世界各地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所做的上述理论建树,并不包括中国的材料。因此,在对古代社会复杂性进行解释的过程中缺席了重要的中国案例。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40年代初,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可视为当时的中国学者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的代表性著作。其后,在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上,不断有中国学者孜孜以求解。王震中教授《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简称《形成》)一书正是这一学术领域新的重要成果。该书在对以上学说进行扬弃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古代社会进化的情况,提出了一整套新的解释模式,创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其理论建树和研究突破所具有的意义,令人欣喜。 每一种理论创新和解释模式的提出都需符合其所研究对象的实际,就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而言,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深有造诣的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商代的社会形态使上举社会进化分类里的酋邦与国家之间的分别产生了定义上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是把殷商社会当成常规以外的变态,还是根据中国古代的情况重新考虑上述社会分类?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形成》一书对于上举西方理论模式作了批评,例如书中指出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模式,“是按照社会进化观点将民族学上可以观察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加以分类排列而成的,因而其逻辑色彩很强”。结合中国的案例,《形成》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演化与国家形成的解释模式: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初步不平等及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都邑国家→复合制的王国→中央集权制的帝国。这一解释模式的关键在于提出了“中心聚落”的概念和“复合制国家结构”论。所谓中心聚落,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具有亲缘关系的聚落群中突出的某个权力相对集中的聚落。这种聚落规模较大,聚落中集中了手工业生产、贵族阶层以及宗教建筑,并且对其周围的普通聚落在民事或神事上有一定的管辖权。可以看出,中心聚落阶段是由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一步。原本平等的人因为血缘、政治、经济等关系而产生身份上的不同,此一阶段也正是权力集中、王权形成的开始。 《形成》提出的解释模式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古代社会演化中长期存在的氏族因素。20世纪上半叶,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曾提出“城市革命”理论,认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地球上某些地区的人们摆脱了血缘藩篱,发展出结构复杂的大型都市。这种论断并不十分符合中国的情况。侯外庐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途径与西方不同,古代希腊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最终取代家族,中国古代虽亦是由家族而国家,但国家却依旧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上。《形成》一书充分关注到了此一问题。书中对大汶口、凌家滩等中心聚落墓地的分析即主要从父权家族角度着手,认为当时社会的诸种不平等的产生以及社会分层的出现,都应与父权家族或父家长权的出现相关联。而且在其后的龙山时期乃至夏、商、周三代,以父权家族结构为基础的阶级分化与对立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问题历来是我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形成》一书提出了“复合型国家结构”概念加以解释。《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定程度上虽有理想化的嫌疑,但由宗族而百姓而万邦的多层次结构,却不失为对三代国家形态的传神描绘。三代国家的核心即是王族,与王族共存的“百姓”指其他贵族家族,王族与百姓的联合构成了国家最核心的军事、政治权力。这一点在商代甲骨文中有深刻体现,甲骨记载商王在日常祭祀、行政尤其是行军出战时,都需要“比”“呼”“命”其他贵族家族。核心层之外的万邦则较为复杂,既有王朝分派的邦国,像周代分封在王畿四围的鲁、齐、卫、燕等诸侯国,主要目的是对抗当地的土著国族,控制一定范围的国土。同时还有一些慑服于王朝武力的土著势力,像楚国以及《宗周钟》铭文中提到的南夷、东夷二十六邦等。此外就是文献中所谓的“荒服”族群,时叛时服,不时与中心王朝产生冲突。“复合型国家结构”就是对这种多层次政治结构的精炼概括。这样的概括,揭示了三代历史特征;克服了主张夏商周三代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论者所忽视的三代的地方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郡县制之下的地方行政并不相同的问题;也克服了把三代的各个王朝看作是由许多“平等的”方国组成的联盟的论者所忽视的夏王、商王和周王对于地方诸侯邦国的支配作用的问题。三代政治特点即是对内宗法统治,对外服而不灭。在邦畿以及分封国中实行尊尊亲亲的家族式统治,将大小贵族都统合于有血缘联系的阶级体系里。对四夷土著国族则以服国为目的,实行羁縻式统治。可以说“复合型国家结构”这一概念与三代政治结构的特点密契相合,这也是理论创新的魅力所在。 任何一种研究归结到最后只是一种叙事,社会复杂性研究也不例外。西方人类学家的宏大叙事中往往缺少中国案例,致使其研究结果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情况格格不入,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实际相违。像柴尔德的研究,最终只得出了一种直线进化的社会发展路径:欧洲青铜时代的金属制造者独立发展出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并最终点燃了近代工业革命的火炬。片面研究只会导向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事实证明,中国的相关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理所应当地被利用来说明早期国家社会复杂性问题。《形成》一书就是在充分利用、解释国内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收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社会复杂性演化过程的一次深入的有重大学术创新意义的探索。若将这种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情况而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式和对中国国家演进过程的阐述,称之为社会复杂性研究的中国叙事,可能是恰如其分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