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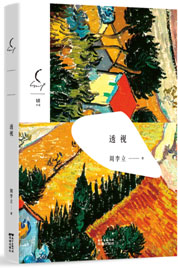
如果说《欢喜腾》的写作有关青春,那么周李立的第二本中短篇小说集《透视》则与青春无关。在这部作品中,周李立多关注那些在都市生活中伤痕累累的人,故事隐去了伤口的形成原因以及痛不欲生的伤害,她要写的是“结痂后的疤痕在意外的天气里突然隐隐作痛”。生活中有意的隐藏和忘却以及突然觉醒的瘙痒和隐痛,你是否也在经历着这般的孤独和无力?
问:《透视》收录了七篇小说,在选择的时候有特别的考虑吗?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周李立:我猜想,每个人都经历过某种微妙的时刻吧,比如一个不适宜的天气,你以为已然痊愈的伤口,突然发痒,令你坐立难安、倍受困扰。往事的蚂蚁,细小的骚动的腿脚,不安分地攀附在脊背上,成为难言之隐。
这大概是我小说中那些人物的基本状态。
然而坏天气终会过去,你也终将恢复平日的乐观开朗,笑脸如花、侃侃而谈,旁人看来,你嘻笑怒骂、欢天喜地,但只有你自己清楚,那种痛苦和惧怕如何存在于身体的某处,你是一个有伤口的人,你不知道哪个伤口会在某一天突然将你一击而溃。这种惧怕证实了你实质上的软弱,与你表面看起来的样子何其迥异。你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大相迳庭的两个自我。这本小说集里,几乎每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带着伤疤的,但那又如何,他们还得好好活着,也许还会受伤,伤口又再结痂。谁不是伤痕累累地每天吃喝拉撒着?
就是这样,我不直接写伤口如何形成、不直接写伤害带来的痛苦如何让人痛不欲生,我写的是结痂后的疤痕在意外的天气里突然隐隐作痛。
问:《透视》这篇短篇小说与2008年四川地震有关,但你并没有直接写地震,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处理方式?
周李立:《透视》确实是因汶川大地震而起。作为四川人,512是我从那时至今一直耿耿于怀的数字。我不想描述那段时期我遭遇了什么,事实上,那段日子我已经在北京生活,而家人朋友们在成都所经历的,我也只是通过他们的描述来体会的。这种间接的经验,是另一种恐惧,就像人类对鬼怪的恐惧一样,因为那个东西,因为没有具体的形象,你的想象反而会更加强化它的狰狞,对,就是“脑补”。
八年过去了,我越来越厌恶对待地震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对苦难的消费,将灾难作为谈资,在无话可说的旅行中、冷场的餐桌上,把那场地震端上来,仿佛一盘下酒菜,引来足够的惊叹和唏嘘。另一种是泛滥的抒情,我总以为那些哀伤痛苦在极致的抒情表达中,其实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说到底,还都是消费。八年的时间应沉淀下足够厚实的土壤,生发出足够的理性,意识到地震造成的创伤,那是永久的,虽然此刻大地的沉稳也如一种永恒,仿佛它从来也没有开裂过。
灾难结束的那一刻,灾难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带着创伤活下去。我们不都是带着一道道伤疤好好活着的人么?我在《透视》中对地震的处理,是在这样一种意识的前提下进行的。
问:《透视》是你第二本小说集,和第一本《欢喜腾》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周李立:《欢喜腾》出版于2013年,收录10个中短篇小说,基本是我2008至2013年的全部作品,那是我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期,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写得很少,也很慢,一直在摸索,方向不明确,5年写10万字,十分不勤奋。
2014年,我30岁,写作的需要突然强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2014年和2015年,我发疯一样写了三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其中不少短篇,都只用了一天时间,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短篇不过夜”的说法。那种感觉,就像在黑夜中,你只是想要找到一点光亮、找到一条路,然后走出去。我反而不在乎这条路通往的方向,只是想要有条路可以走。有路就意味着你无法停下来,我害怕停下来,哪怕只是片刻。
就这样,这批中短篇陆续发表,选出七篇,汇成一本书,成为《透视》。相比较而言,我始终认为《欢喜腾》与《透视》是两个迥异的我,根本无法融合。《欢喜腾》基本是青春写作,我怀疑自己并不会写青春,才会到不再青春的时候幡然醒悟,领悟出小说应该怎么写。《欢喜腾》中的小说,现在我基本不敢翻阅,唯恐看见那个不擅长的黑暗的青春,但《透视》不一样,《透视》与青春无关,我对青春其实特别恐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