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敦,原名张东旭,生于1982年,河北枣强人,写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现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
于枭:张敦老师你好,请你简单谈一谈《兽性大发的兔子》这本书吧。这是你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吧?
张敦:于枭,很高兴能与你对话。说起来,这本书的出版算是个意外的惊喜。从写小说开始,我就梦想着能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因为我很喜欢短篇小说,买过很多作家的短篇集子。发表过几篇后,大概是因为我跟“文坛“的距离比较远,并没有出版社表示愿意给我出书(当然我也没联系出版社)。这我是可以理解的,市场偏爱长篇小说,短篇集几乎已被大众遗忘。前年冬天,朋友介绍我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林潍克编辑认识,他比较年轻,也正因为年轻,参加工作不久,脑子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热情高涨地想挖掘并推出一批新作者,经过沟通,他看中了我的作品,并给我编了这本集子,非常感谢他。这本书有17篇小说,基本都是短篇,最后一篇长点,两万多字,接近中篇,但也可以说成是短篇。最早的一篇是《小丽,好久不见》,写于2004年,那时刚来到石家庄,在一家图书公司打工,做文字编辑,租住在城中村,晚上下班非常无聊,当喝酒、读书、看电影这些事都干烦了的时候,就想写写小说,于是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于枭:这一篇是所有“我和小丽的故事“的第一篇?
张敦:对,从写作时间上来看,确实是最早的,而且写的是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一次失败的约会。这篇大概是唯一一篇不掺假的作品吧,别的篇目都有大量的虚构成分。
于枭:真实的故事?我一直很好奇,这些创作和你的生活经历关联很大吗?比如你的很多部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石家庄人都十分熟悉的地名、人名,还有摊鸡蛋灌饼、踢毽子等日常活动,让人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

《兽性大发的兔子》,张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3
张敦:从编辑内容来讲,这本书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北漂生活、石家庄生活和校园生活。每篇小说都与我的生活关联极大,可以说都来自于生活经历。我喜欢将真实的地名放入小说中,因为这样一来,同一个地方,分别处于两个时空,它们会发生关联,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如果是纯虚构的地名,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也可以说,我还处在写自己的故事的阶段,这挺低级的。
于枭:我觉得不是,小说中将极端化日常和更加极端化荒诞之间刻意混淆的使用就是一种技巧
张敦:是一种手段,从日常入手,慢慢进入故事,找到故事中荒诞的一点,并及时打住,当然,我写的日常可能太日常了,是别的作者不屑于写的,但我总觉得,如果不写这些,那就没别的东西可写了。
于枭:哪种没得可写?是缺乏素材的没得可写,还是除了这种日常的话,其他的书写不能引起你的注意?
张敦:我的写作就是这样。目前来说,我还是更加关注日常生活经验。
于枭:我记得李敬泽老师说,现在小说写不过生活,因为生活远比小说要荒诞得多。类似你这种掠地飞行式的写作,很有那种剧中人又是剧作者的感觉。
张敦:对,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充满荒诞感,能不能感受并发现又是一个问题。你说的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也这样说:既是主演又是导演。在这本书的作者简介里,我特别提到一句,“所写故事基本来自个人生活经历,自己觉得挺现实的。”之所以加这句话,是想提醒读者,要注意这些小说的现实性,不要被表面的荒诞所迷惑。
于枭:你在小说中总是把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看到过、体验过,但不愿意再提的回忆拿出来,按着读者的头,告诉我们——不要试图忘记这段经历。
张敦:哈哈,按着读者的头,我很粗暴的样子。
于枭:这是我在与你同龄人的小说中很少看到过的,这也是我的直观感受,确实很粗暴。
张敦:嗯,从表面上看,我的方式确实有点简单粗暴。对于小人物在生活中的窘态,我不但毫不掩饰,还有意夸大,读者只要有类似的经历,就会感同身后,甚至坐立不安。我写的都是小人物在生活中弱的一面,人作为一种动物,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需要足够的信心,本能中不愿承认自己的弱,潜意识中,我们会反复暗示自己很强,干什么都无往不利、游刃有余。我的小说所呈现的是一种无力之感,即使有人能从中看到力量的话,那也是无能的力量。崔健有一首歌,就叫《无能的力量》,我很喜欢。
于枭:另外一点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在你大部分小说中,生活满是的残酷和疮痍,你的书写似乎也不打算带点儿温度;在叙事过程中你大都也是一种对读者爱答不理的态度。
张敦:从2004年开始,我一直在为生存的问题所焦虑,你可以想象,一个师专毕业生,放弃了当一名小老师或电视台小记者的机会,在城里四处找工作,我写的好多篇都是这样的故事,说它们是生活的残酷和疮痍,就有点过了,这应该是很多青年都应该经历的生活,就像上一辈人的上山下乡。当然,上山下乡的故事比浪迹城市的故事好玩得多,而且还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于是他们那代人就特别爱写那段经历,不只是一个人写,而是一大帮人写,多到可以形成一个流派,所谓的知青文学。到了我们这代,农村青年几乎都要汇集到城市,尤其毕业于普通大学的那部分青年,高不成低不就,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又都有知识,有思想,不是行尸走肉,内心的苦闷可谓无边无际。那么,为什么作家们很少写他们呢?尤其是八零后中成名已久的那批作家,他们笔下的人物好像都衣食无忧,压根不存在生计问题。也许,生计问题,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一个人一旦在生存上出现问题,难免与都市生活拉开距离,沦为不入流的边缘人物。没有人会关心边缘人物,即使是身处边缘的作家。你上面说,我对读者是爱答不理的态度,我倒是感觉不到,相反,我觉得自己对读者挺好的。从讲故事的方式看,我不喜欢绕弯子,故事情节发展直来直去。语言也尽量简单易懂,短句子为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当然,我的本意并不是为读者考虑,而是为自身而考虑。我这样写着感觉非常爽,有快感,希望读者能体会到同样的快感。当然,总体来讲,我的叙事温度是偏低的,甚至接近于零度,这是风格的问题,是我在装酷。
于枭:我很能理解那种焦躁抑郁。反映这段生活焦虑的小说是在当时当下奋笔疾书写出来的吗?还是在那个阶段过去之后,回想当时经历而写出来的?
张敦:大部分就是在当时的生活里写的,最典型的三篇是《烂肉》《毽客》和《去街上抢点钱》,这三篇写于同一时期,那时我刚结束了北漂生活,回到石家庄,一个人租了套房子,自己做手工巧克力在网上卖。我既是商品制作者,又是淘宝客服,甚至是快递员。我不能总是待在屋子里不出门,那样会让我非常焦虑。我每天都要骑电动车出门送货,一年的时间,几乎熟知石家庄的每一个角落。因为每天都是一个人,所以特别无聊,就练习着写了几篇小说。每到暑假,房东从县城回来,我就只能搬到小屋,他们一家住大屋,等暑假结束,他们就走了,我就搬回大屋,把小屋租出去。住在小屋的日子里,天气炎热,巧克力无人问津,我只好写小说,编造几个与自己差不多的人,陪着我。
于枭: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状态?
张敦:对,而且我还是要交房租的。除了暑假,那房子就是我的天下,一到暑假,他们就过来了,我就成了寄人篱下。那种感觉很奇怪。我一个单身汉,与一个幸福的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当然我的房东也不是有钱人,起码他们都有正式工作,一个是教师,有暑假,一个工程监理,挣钱多,我每天窝在小卧室里,对着电脑。他们都觉得我很奇怪,是个颓废的小淘宝店主。
于枭:可能是这种环境带来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有一种自尊心和自我价值认可的崩坏反映在了小说里。
张敦:当时非常焦虑,孤独与焦虑如影相随。《烂肉》所表达的,其实就是那种生存焦虑,而生存焦虑,几乎是我多篇小说的主题。
于枭: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把你笔下的“我”或者“牛力”或者“小丽”这样的人,去和鲁迅笔下国民拿到一起去比较,无知、愚昧、暴戾、残忍。
张敦:我的小说还没到那种程度,不能和鲁迅比,私以为可以和郁达夫那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比。他那篇写的就是一个落魄青年的故事,我非常喜欢,大概就是他的真实经历吧。我之所以说没到鲁迅那种程度,是因为我不代表全体发声,充其量只代表一个个体。
于枭:你小说里的主人公都不愿意思考,甚至抵制思考,对吗?
张敦:这样说吧,是我不愿让他们思考,我不喜欢太过理智的思维,凡事要有一个干脆的判断,最好爱憎分明,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种力量,斩钉截铁的力量,文学作品不是社会分析论文,作家也不是学者,考虑得太过周全,反而很没意思。你觉得公知有意思吗?现在中国每天都要出事,有时还是挺大的事,每到这时,公知必然站出来说话,他们从来不对事件本身表态,而更关注其他人的想法,他们会高深莫测地告诉大众,你们都是错的。比如战争吧,有些公知总说,你们不要老盼着打仗什么的。他指的你们,这群人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关心打不打仗的?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判断力,虚构了大众的无知。这种人一点也不可爱。对于小说家来讲,思考的东西不宜直接表达,而应该通过故事本身来呈现。比如,《带我去戈壁》那篇小说,你能说这故事没有深度吗?当然是有深意的,其出其不意的荒诞性,会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让读者去思考吧,把问题推给读者,是我惯用的方法。好多问题,并不是小说家可以给出答案的,而是我把这些材料展示给你,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判断。小说家只要发现问题就可以了。
于枭:荣格说,最可怕的事就是全然地接受自己。我觉得你的小说就在帮助读者去补全不愿直面的那一部分,长久以来,我们对于人性本能的压抑不能正确认识接受。那些别人不耻或者不愿提起的往事,你偏要大书特书。
张敦:谁都不愿提及自己最糟糕的岁月。我最受不了的是那类小资作家,动不动就写咖啡馆,写吃西餐,喝红酒,一些女性作家最爱这样写。这是虚荣心在作祟,生活本来就是粗粝的,不讲情面的。粉饰的只能是所谓的太平,而我这个人,就不爱粉饰自己的经历,我喜欢自嘲,喜欢自我解剖。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对自我的解剖就是对人类个体的解剖。其实我个人最卑鄙龌蹉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我现在还处于练笔的阶段。
于枭:你的小说里充满了愚蠢、贪戾、妄言、暴食……七宗罪似乎犯了遍,也从来不刻意写人性向善的那一面,这是有意的?还是生活本该如此?
张敦:七宗罪毕竟是人类的原罪嘛,确实温暖的成分少一些,是有意的,觉得这样写酷一些。这也是作家的一种选择,你是选择写温暖,还是选择写冷酷,只有下放到生活的残酷和疮痍里,小人物的生命和爱恨才显得可爱。
于枭:还有就是你小说里那么多粗话、脏话,读的时候很过瘾。
张敦:粗话、脏话也是有意保留的,但不宜太多。比如在《小丽的幸福花园》里,“我”隔着防盗门质问小丽,喊出了振聋发聩的脏话。写的时候,似乎其他词语不能表达那种情感,只能用上脏话。在日常生活中,粗话和脏话是我的语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讨厌俗话,比如“年轻人火力壮”“太有才了”这类话。写小说的时候,如果不能产生黑色幽默的效果,是绝对不会用这种话的。
于枭:我记得有谁说过,你的小说就是失败者的、放逐者的小说,这一点你认可吗?当我们这个时代习惯了所谓的成功和成功学之后,你认为自己小说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张敦:这一点我是认可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失败者的故事,会引起共鸣,比如卡佛的小说,更多的是电影,比如《搏击俱乐部》《阳光小美女》等等。大众之所以热衷于成功学,是因为大众是平庸的,这才恰恰遵循了动物本能,即挖空心思多占有各类资源。成功学就是教你怎么去占有资源。占有资源多的人,就成了成功人士,是大家崇拜的对象。而没有资源的人,则是失败者。这我是认同的,我也想当个成功人士,也想拥有各种好东西。我的小说并无核心价值,只是我个人实现成功的一次试探。哈哈,这么说有点讽刺。正常点说,我的小说只是道出了年轻的失败者的愤恨,对当下资源分配不满而产生的愤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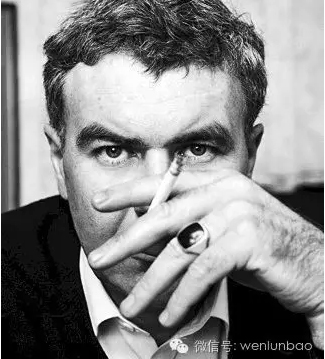
雷蒙德·卡佛(RaymondCarver,1938—1988),“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
于枭:不少人说你现在的写作路子不宽、视野太窄,对于这种批评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张敦:听了那些人的批评,我认真反思了自己的写作,确实存在那些问题,挺感谢他们的,他们是我最好的读者和老师。我以前觉得写作题材不应该是作家的缺点,作家不都在建立自己的小说王国吗,不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吗?现在,我是这样认为的,小说家的视野应该尽可能地大,公平对待笔下的每一个人。现在我写的人除了主人公,其他人物都很脸谱化,这是很大的缺点。所以,我在有意识地开疆扩土,比如农村题材,犯罪故事。
于枭:我一直都很喜欢“我”和小丽的故事,但是你这几篇小说里,“我”和小丽的故事时间线很乱,这里面存在一个正确的阅读顺序吗?
张敦:每篇小说中的“小丽”不是同一个人。喜欢过很多女孩,好几个人名字里都有“丽”这个字,写小说时,我懒得给人物起名,索性都叫了“小丽”。小丽有时是这个她,有时是那个她,也有时是完全虚构的。我喜欢主人公的名字是普通而平常的。给小说人物起一些文雅的名字也是一种装腔作势
于枭:以后小丽还会在你的故事里出现吗?“她”或“她们”存有一个内在的共通性吗?
张敦:要写故事,女主角还是叫“小丽”,她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共性,她们是不一样的人。
于枭:嗯……她们都会有一个什么结局?
张敦:她们没有结局,就像我们中的任何人一样?生活本身就没有结局,我们都是普通人,我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故事,没必须要写得那么有仪式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