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拓性的探索 美好的“惊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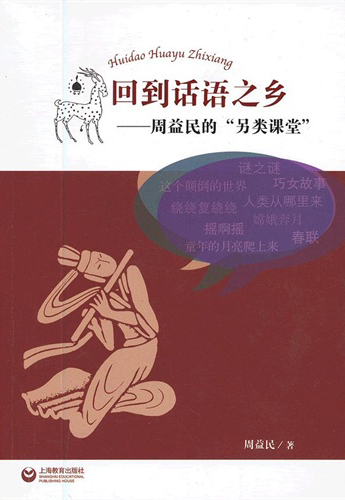 《回到话语之乡——周益民的“另类课堂”》 ,周益民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我很欣喜,很震动,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位教师把绕口令纳入到小学语文教材中。虽然低年级语文教材中出现过一些民间传统童谣,但还没有出现过颠倒歌、绕口令这种类型的传统童谣。所以,我认为周老师的做法是个创举。” ——金波 前几天,阅读了周益民老师的新著《回到话语之乡》,感觉到周益民既在实践,也在研究,他的教学研究具有文化学、社会学、儿童论、课程论、教学论以及语言学、教材建设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他不想标新立异,更不想故弄玄虚惊动大家,但他的实践和研究还是“惊动”了我们。 他“惊动”了我们的教材观。语文教材理当是千百万年来人类馈赠给孩子们的文化结晶,理当让孩子们去触摸人类那唇齿间的智慧,去亲吻田野上的花朵。也许我们走得太远了,忘了出发的地方,忘了为什么而出发,现有的教材总是有着缺憾,那“母歌”总是在遥远的地方深情而又微弱地呼唤,那人生的摇篮曲总是离我们的生命而去,以至于在教材中老去。周益民,以他的专业敏感以及他的专业理性,默默地做着“补救”工作。这件工作之于语文教材究竟有何意义和价值?儿童文学作家、国家语文教材审查委员金波作了这样的评价:“我很欣喜,很震动,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位教师把绕口令纳入小学语文教材。虽然低年级语文教材中出现过一些民间传统童谣,但还没有出现过颠倒歌、绕口令这种类型的传统童谣。所以,我认为周老师的做法是个创举。” 周益民的公开课。我也曾听到少数人这样议论:周益民的公开课为什么不教语文教材上的课文,却要自编教材来上语文课呢?这样的议论当然不奇怪。以往我只是从新课改理念去理解,比如,课改提倡教师是课程领导者的观念,周益民完全可以去创造教材。比如,当一本语文书不能满足儿童发展需要的时候,教师完全应该在教材的基础上超越教材。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教材只是一块起跳板。走进周益民的内心世界,我们发现公开课就应该是试验课、研究课,就应该是创新课、探索课。我想,语文及语文公开课,应该当作最幸福的礼物让孩子们领受。周益民创造了这件礼物。 返本而开新。周益民返回故里,开了语文教学改革之新。返本绝不是简单的返回,而是回归中的提升。在对传统的“母歌”珍视、捍卫的同时,要加以时代的解释。维特根斯坦,这位英国哲学家旨在凭借语言的界限来解释思想的界限,曾提出“语言游戏说”,指出由意义结成关系,但“意义在于使用”。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活动,并努力将这种活动嵌入人的“生活形式”之中。这亦即是巴赫金所认为的“话语是独一无二的行为”。周益民把童谣、颠倒歌、对联、神话、猜谜语、巧女故事作为教学内容,作为语文教学的一场“语言游戏”,让它们在教学中复活,彰显出应有的意义。值得强调的是,周益民在教学中细心地引领孩子们领悟其中的道德意义、真理的力量和审美的意蕴,把人性之美、智慧之美、崇高之美悄悄地阐发得如此细致、准确、到位。这是一种文化重建、价值重构,当然更是文化启蒙与思想启蒙。语文教育应当“惊动”一下文化和价值。 周益民是“诗化语文”的倡导者。周益民的语文教学试验,与他的诗化语文是何种关系?我以为,这些试验是诗化语文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对诗化语文的提升。高尔基曾经这么评说诗歌:“诗不是属于现实部分的事实,而是属于那比现实更高部分的事实。”歌德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应该拿现实提举到和诗一般高。“和诗一般高”就是崇高,就是里尔克所说的,将诗人的工作阐释为“我赞美”。马克思·范梅南认为:“所谓诗化不仅仅是诗歌的一种形式,或一种韵律的形成。诗化是对初始经验的思考,是对最初体验的描述。”歌德在《浮士德》里也这样写过:“太初有言”、“太初有思”、“太初有力”、“太初有为”。“最初”的、“太初”的、“初始”的,在哪里?在那些“母歌”里,在唇齿间,在田野里。能不能这样说,周益民试图用诗化语文来给自己的语文“立法”——他自己要“惊动”自己的诗化语文。 周益民不惊动儿童。周益民爱儿童,呵护儿童,他自己像“大男孩”。但他从来没有忘掉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引领儿童发展。我被周益民童谣里“变大还是变小”的话题所吸引,这是一个极富穿透性的话题。孩子要变大,成人要变小,变大是成长,变小也是成长。周益民通过语文课上的讨论,让孩子们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又变小,就在变大与变小的过程中,孩子们回到话语之乡去了,怀着乡情,怀着梦想,从源头起飞,在语言的上空盘旋。在周益民的语文课堂里,孩子们变大了,成人也变智慧了,变年轻了。 《中国教育报》2012年11月26日第11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