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玫
赵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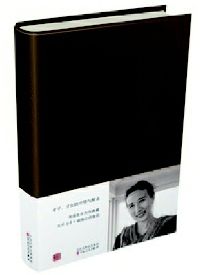 《矮墙上的艳阳》
《矮墙上的艳阳》
显然,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并且是有些冒险的。 一切由李庄起。 那林林总总的爱与凄惶。 便由此而想到,能否写成小说? 不,不单单是小说,而是一些,似小说,又非小说的文字。或者,在故事与言论中游移的某种诉说。 自2010年最初的设想,到我此时此刻进入实际的写作。几年间,书店里已遍布了关于那女人的前世今生,于是我犹豫是否还要忝列其间。但到底那女人的故事让我难以割舍,哪怕很多人在编织她的童话。终归不同的写作者会有不同的视角,文字的质地以及感知的方式也会迥然不同。所以,对于有创造力的写家而言,你写的,就是你的,仿佛某种基因,每一个字都会镌刻下你自身的印记。 由李庄而起的这个故事确实美丽。那爱与死的挣扎和毁灭。那已逝的,不单单是诗人的死,还有爱过并被爱过的花样人生。当这种爱被升华到精神的维度,便必然地为人们留下了神圣和永恒。 单单是体味心中那诸般的苦。单单是斯人已去的那无望和悲凉。于是便有了女人写给挚友的那封坦诚的信,说她是爱着逝者的。说自己有时的心,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又说是逝者警醒了我,他已然变成了一种激励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或恨,或怒,或快乐,或遗憾,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 写这样的爱的心路,一定是美的,却也很神伤。 或许这女人,从灵魂深处就迷失了。 然后,慢慢地读,关于那女人所有的琐碎篇章。林林总总地,却最终在心中勾勒出一片迷人的景象。这个被称之为倾城倾国的女人。这个被比喻成旷世聪慧的女人。她的存在之所以能成为瞩目的焦点,当然不单单是因为她水中净月的貌,更因为她蕙心兰质的心。于是这种在知识圈中优雅的妇人,大抵是要让风流才子神魂颠倒的。这不是她的错,亦不是爱她的那些男人的错。 徽因随父游历英伦前后8个月。偏偏那位以诗为歌者,成为她生命中的第一个追求者。 那时她大抵已被征服,诗人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妻离婚。 但无论怎样眷恋,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远离。在迷茫与无奈中,回到北京雪池的家。不久后便落入梁家的“圈套”。这曾是梁任公自诩的一个杰作。且年轻的思成风度翩翩,有着常人不及的家道和学养。于是两个年轻人彼此相悦,类似两小无猜的青涩与浪漫。 不久后诗人打道回府,才知道悔之晚矣,伊人已去,万念俱灰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将所有情怀投笔于《新月》,以诗词歌赋,浇心中块垒。此间,徽因也常来《新月》游弋,和诗人有着丝丝缕缕的文学联络。当诗人终于知其不可为,便不再为之,任凭英伦的往昔化作天边云彩。 灿若晨星的胡适、志摩、林长民及梁启超,让《新月》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短短长长。志摩和林长民自伦敦交好,而志摩和梁启超又有着忘年交。尽管梁启超对志摩的行止多有诘难,却始终坚称自己是爱着志摩的。在如此复杂而斑驳的关系中,唯其爱,才是其中最美好的,但这爱却又委曲纠结着,绝不是志摩或思成所能驾驭的。一个团体的兴衰,竟被一个女孩的命运所牵系,或者这就是所谓《新月》的悲剧。 在如此纷繁而隐忍的关系中,偏偏又迎来了泰戈尔的到访。对志摩来说,那是他最欣悦的成就。泱泱国中,大概也只有他能将大师请来。于是某个可能的机会应运而生,泰戈尔在华期间,志摩和徽因始终全程陪伴。其时已心有所属的徽因并不曾拒绝,因那是《新月》共同的盛事。在泰戈尔的照片中,总有志摩和徽因的来踪去迹。但终究劳燕分飞,哪怕泰翁亲自说情。于是诗人痛断心肠,在无望中独自嗟叹。 不久思成偕徽因前往美利坚游学,从此彻底断绝了诗人的念想。便是这人生的挫败,让他终于迷途知返,将早前的凄切付之一炬。随之掀开新的篇章,小曼登场。而这对于诗人来说,又几多风雨。原以为小曼终于成了诗人镜花水月的归宿,就像他诗中写的那般“甜美的梦撒开了青纱的网”。但不久后诗人便奔波于上海、北京的各个讲堂,赚取银两,以满足妻的翩跹妖娆的纸醉金迷。 倏忽间4年过去,思成与徽因返国。此时他们已完成婚礼,度过蜜月。伊人相见,已不似当年景象。徽因和思成很快便远赴东北大学任教,荒寒中,徽因少年时罹患的肺病复发。志摩闻讯出关探望。随之,思成将徽因送回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养病。其间老金、从文等一干朋友每每结伴上山,探望徽因。志摩自然也常来常往,流连于香山的病榻之间。此间志摩身边既无小曼,思成也已返回教职,于是漫不经心中营造出某种心驰神往的氛围,一种彼此守望的炽烈与辉煌。他们的关系仿佛又回到某种从前,以至于香山成为了彼此最贴近的地方。 那些从清晨到黄昏的时光。这可从他们的诗歌和通信中觅得端倪,尤其徽因那些热烈而澄澈的诗行。绝美的诗句甚至令志摩无限慨叹。或者,那就是徽因的文学起步,从此她写出无数动人的诗篇。“忘掉曾有着世界,有你”“落花似的落尽,忘了去”“吹远了一缕云,随那风冷”“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那一天你要看到凌乱的花影”“陪伴着你在暮色里闲坐,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它知道,知道是风,一首诗似的寂寞”…… 倒是,志摩因他的《爱眉小札》,抑或不尽如人意的晦暗的婚姻,反而变得不那么高蹈,写给徽因的信中尽是悲戚与无望。及至最后,才有了他为自己和徽因的《你去》。在信中,最让人伤感的是最后一语:“我还牵记你家矮墙上的艳阳。” 那矮墙上的艳阳。 接下来,《我们太太的客厅》,那部小说,像硝烟一般地弥漫在北总布胡同的徽因家中。太太的客厅,或者,下午茶,其实不过是延续了欧美上流社会的某种交际的方式。来此做客的,当然是那个年代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学者。由此以私家客厅中相互切磋的方式,最终奠定了《新月》这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 不幸80年后的某个春节,《太太的客厅》突然被拆毁。曾经多少爱与恨的故事发生于此。但这一切的一切,终究归于虚无。于是,悲凉,愈加为小说抹上了惨淡的色彩。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有一天,志摩竟真的会飞升了去。此前在清华的茶会上,徽因夫妇还见过志摩,并提及他翌日回上海。当晚志摩再访梁家,未及相见,遂留下“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的字条。旋即徽因打去电话,问及志摩往返行程。约定19日赶回北京,听徽因在协和礼堂向外国使节讲述中国古建筑。19日当天,徽因收志摩登机前从南京发来的电报:“下午三点抵南苑机场,请派车接”。下午,思成驾车前往机场,志摩的“济南号”却迟迟未到…… 当晚徽因讲演大获成功,却始终记挂着何以没有志摩的消息。焦虑中,朋友们齐聚胡适家中,直至《晨报》刊发了诗人罹难的消息。随之思成、老金等前往济南,会同从文、一多、实秋等料理志摩后事。思成代徽因向志摩灵柩献上了亲手赶制的花圈。返回时,又遵徽因所嘱带回失事飞机的残片,从此白绫包裹,置于家中,直到离世。不久后,徽因在《晨报》发表了《悼志摩》的文章,句句令人肝肠寸断。4年后,她再悼志摩,依旧饱含着痛与悲伤。 显然,诗人爱得最苦的并不是他的妻,而是那“永失我爱”的林徽因。自世间有了这女子,她就再不曾离开诗人的心。而志摩爱徽因,则必定是爱得很凄惨,也很悲凉。而诗人的死,或者就因了,他再不想承受这人生的苦,不想再被虚妄的情怀所煎熬,亦不想在悲哀的守候中挨着无望的希望。于是冥冥中,他终于洞穿了自己的命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爱的女人写下了悲凉的《你去》。亦有论者说,志摩的人生,是将他的负心与伤悲、暗淡与心碎化作了光辉和迷醉。 然后是谦谦君子的梁思成,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持着贵族般高贵与斯文的男人。他生性平和,沉实敦厚,有着一颗包容的心。而那时的徽因就像一束散乱的花,寻到思成后,才知道自己到底拥有了什么。 不是什么人都能像思成这般,将爱情提升到一个宽广而崇高的境界。他或者从一开始就知道,徽因必定会置身于人们的爱慕中。当徽因最终选择了思成,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徽因的朋友当作家庭的友人,从此往来唱和,不曾生任何嫌隙。思成爱徽因,是爱到了不让徽因有哪怕一丝局促的地步;爱到了,倘若徽因爱上了别人也不会有任何阻遏的境地。于是才会有那么多风流才子,尽日沉湎于徽因的客厅。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迷恋着这个被思成所描绘的“我那迷人的病妻”。或者就因了思成的大度,反而让喜欢徽因的那些友人,无形中有了某种底线。自此,无论谁,都不得不将这爱的感觉变成高贵的情怀,让曾经的迷乱化作缕缕飞烟。 所以,徽因说,她不悔在生命中选择了思成,倘若给予她重新选择的机会,她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是的,她可以飞扬,可以浪漫,可以写下那真诚的诗篇,但唯独在她的生命中,不能没有思成。 只是,读志摩的诗,总是不胜唏嘘,流潸然的泪。觉得志摩一路走来,爱得好隐忍,好艰辛,那,璀璨的苦。也知道,徽因,其实也从不曾放下过这位远逝的朋友,从不曾停息过刻骨的怀念。于是临终前,她才会特意在病榻前约见张幼仪,或者就为了,那个始终活在她们各自心中的诗人…… 如今徽因、思成、志摩及老金,均已是老照片中的故人,于是许多当年的细节都已无从考证。时至今日,这段久远而凄美的故事,已慢慢变成传奇。所以人们今天追述的,往往已不再是岁月留痕的种种往昔了。 对我来说,这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悱恻故事已成为某种由头。写作中,自是拒绝陷入那斑斓的历史真实中。我只想在凄切的迷惘中探求人性的真伪,只想在叙述中找到那个精美的角度,只是想在虚实之间,让文字行云流水…… 为此,我让小说中的人物承担起他们沉重的负荷。无论属于他们,不属于他们的,浮生若梦般的悲凉。于是演员成为了小说中最具表现力的载体。唯他们能将当年的风云人物再现于舞台。为此,他们自身的人格也会随之变得丰富,不仅要完成自身的表演,还要出神入化地诠释人物的命运。于是,自我,非我,进而分裂的人格。或者仍旧终将不过是“花非花”的某种俗套。 总之,不忘五月时油菜花开的美丽时节。不忘由李庄而起的这段迷人的往事。不忘走进李庄的那一刻,就笃定了,要“陪伴着你在暮色里闲坐”。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涂抹出《矮墙上的艳阳》。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作协主席)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