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2月24日,遭日军轰炸后,重庆街头仓惶的难民。

范稳采访大轰炸受害者陈桂芬。她的头脑里至今还存留有当年的弹片,曾两次到东京上诉。

1940年8月19日,轰炸后的重庆大学校门口。

2015年6月5日,在重庆举行“六五大隧道惨案”纪念大会上,两个日本律师专程赶来祭奠并向受害者谢罪鞠躬。

敌机轰炸渝市郊。1940年2月24日,难民看着残破的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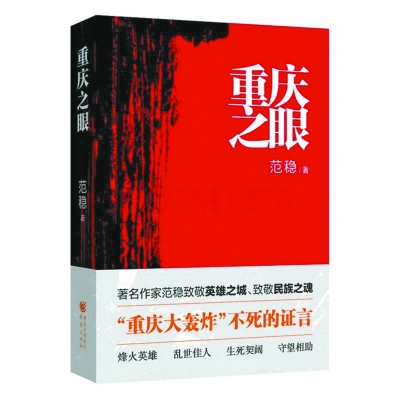
范稳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每座城市都有它特定的纪念日,重庆的纪念日是6月5日。1941的这一天,晚九点,由于日军飞机在重庆上空的无差别轰炸,造成抗战中堪称“三大惨案”之一的较场口隧道惨案。据悉,在这条6600米的隧道中,因为时值周末,隧道中聚集了一万至一万二千左右的人。窒息死亡的人主要集中在三个洞口附近。专家估计,死亡人数大约在3000到4000人左右。
而事实上,这样在敌机轰炸下艰难求生的日子,对于重庆来说,从1938年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1943年8月。美国的记者雷伊·斯科特曾用镜头,记录下重庆大轰炸中的真实场景,这些震撼人心的画面,后来进入一部名叫《苦干》的纪录片当中。这也是西方人有关重庆大轰炸最完整、最震撼也最史实翔实的记录。
有关重庆大轰炸的纪实作品、影像作品不时被推出,而在今年,云南作家范稳也为这个题材增加了一部厚重的小说《重庆之眼》。大量重庆方言的对话运用,提示着他与这座城市更早的渊源,而在书写了云南抗战老兵命运的《吾血吾土》之后,这部《重庆之眼》应该被视为他的“文化抗战”小说系列的第二部。它同样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也同样展示出中国人奋起抵抗外侮的坚强与不屈。更重要的是,在战争的延长线上,小说让我们看到,经历了战争惨痛的人们,如何带着伤痛的记忆,继续坚韧地前行,并力图通过这种捍卫记忆之姿,唤起世人对历史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思考。
《重庆之眼》还将笔触延伸到重庆大轰炸受害人对日索赔案当中。这一部分尚属现实时空的正在进行时,是新闻追踪的热点,但未必是小说家能游刃有余处理的内容。但是范稳却将三十万字的一半笔墨都花在这一部分,显示了小说家还原历史之外的雄心。
事实上,正是这一部分,让我与他有了这个对谈。因为我所热爱的美国学者托尼·朱特曾提示过世人:我们不应为记住而记住,为纪念而纪念,因为这样“都不能强化我们对过去的评价和意识”。一种面向未来的写作,即使是在书写过去与当下,也应该提出一种思考。而就这个题材,它应该启示大家的仍然是:我们该怎样作为,才能对得起这苦难积累的财富,为人类的尊严与和平尽一份责任?
一 在这些民间对日索赔人员身上
我看到了战后遗留问题的真实存在
孙小宁(以下简称孙):闷暑天谈论这本书,话题会显得沉重。但就像某些历史你想绕开,但它总会在特定时刻突然做现实的反弹一样,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你的写作题材一向沉重,《重庆之眼》更是如此,以至于读完很多天,都不想和人交流,甚至也不想和你交流。因为总感到,一时半会儿,还不太能完全消化这背后的沉重。这,不仅指你所写的历史——重庆大轰炸事件本身,而更是它在现实中的处境。真没想到,你的笔触会延伸到当下的民间对日索赔案中来。这一部分通常会见于新闻报道,但作为小说素材且占了相当比重,在我视野当中,还是少见。一方面有些意外,另一方面又觉出新意。因为一个重庆大轰炸题材,影视剧都有了好几部,如果还是历史的还原,无论怎样深入,格局还就是:就苦难写苦难。而你把这一正在发生的事件纳入小说当中,无疑让人对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又多了一些思考。大家都知道,太近的现实反而不容易写好,你是怎样做这方面功课的?
范稳(以下简称范):诚如你所言,在构思这部作品时,我不想把它写成一部就苦难而写苦难的小说。在我接触这个题材之前,这段历史已被人咀嚼了十来年了,史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它不再是一段被遮蔽的、或者隐秘的历史(如果一个小说家占据上述两个条件,你知道,是很得先机的)。一些小说家也有介入,写得更多的是非虚构文本。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史实基础,但也给我提出了挑战,人家都写成这样了,你怎么办?而对日民间索赔这个概念,我也是在重庆采访期间才听人提起的。当时我就脑子里灵光一闪:或许这是个突破口呢。后来通过当地朋友介绍,我成功地“打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
孙:那一段时间通电话时,感觉你一直住在重庆?而不是常年生活的昆明?
范:对,那段时间我从昆明暂短地移居重庆,在一个小区租了套房子,“假装”自己是重庆人。多年前在重庆求学的经历让我对这座城市相对熟悉一些,许多风俗和市井生活一接就通,毫无障碍。原告团里多是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他们是退休老人,下岗职工、小本生意人,无业游民,很少有家境富裕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人很好也很善良,在这个喧嚣的社会里更显孤单。我的介入令他们感到自己似乎有了一个“友军”。因为在有些人看来,他们是草根,文化层次低,原告团内部也很混乱,有组织无纪律更无经费,缺乏体制内人们常见的那种秩序。但是我认为他们是一群真正的中国人。参加这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暮气沉沉的对日索赔原告团,自费到日本打官司,有人甚至不惜抵押了房产。我承认律师承诺的一旦胜诉便可得到多少赔偿金,是他们参加对日索赔的主要目的,那是他们终其一生也挣不到的数目。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身上不时闪现出来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这些方面他们同样可以代表找到了自我价值和尊严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回忆中有切肤至骨的苦难,有至今仍未愈合的战争创伤,有要求讨回公道和正义的合理诉求。而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战后遗留问题最具体真实的存在。
孙:其实写战争伤痛,也写战后人的境遇,你在小说《吾血吾土》就已开始。只是《吾血吾土》中,你着重写的是抗战老兵战后的命运,以及战争中的双方当事人,怎样在战后面对。而在新作里,战争的受难者,多面对的是战后一代的日本人。而且是通过这么个特殊官司来面对。
范:每个作家动笔之前肯定有个思想价值判断或者某个明确写作方向。我进入抗战题材的写作以来,一是专注于文化抗战,二是开始思考一些战后问题。战争只要是正义的,胜利终将属于正义一方。但胜利以后怎么办,怎么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怎么清算战争责任找回公道与正义?我们似乎想得不多。至少和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兴起的战后反思文学相比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那些勇敢地走上日本法庭的普通老人,我认为他们是在用生命的余辉,做一枚枚勇敢地砸向石头的老鸡蛋。
二 民间对日索赔
历史与现实的症结
孙:但这无疑又给本身就沉重的题材又加上了一重砝码。一些胶着的成分。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的索赔是以失败告终,所谓的“生命不息,索赔不止”,不仅预示着,无论是对受害者及其亲属,还是对出于理想与正义,做法律援助的中日律师来说,民间对日索赔,都是一条看不到边际的艰辛路。为什么如此艰难呢?
范:战争灾难题材的小说,沉重是必然的,你无法使它更轻。对日索赔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前景极不乐观。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小说家,我或许比那些原告团的成员们看得更远、更清醒一些。对日索赔表面上是个人和一个国家的较量,其实它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更关乎国际政治格局与气候。
从历史上来看,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于1951年9月和48个战胜国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这个和约在我们看来,让日本逃脱了战争责任,从战败国而成为了一个正常国家。我们国家至今也没有承认它。到了1952年,日本又和台湾的国民政府签订了《日台和约》,由于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状况,战争的受害地在中国大陆,而国民政府又偏居于台湾,它就没有对日索赔的主张权。日本便迫使台湾国民政府从法律上放弃了对日索赔,这个条约我们当然也没有承认。到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条约》签订,中国政府承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在政治上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扫清了障碍。现在对日索赔在日本法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我方认为我们放弃的只是国家间的战争赔偿,民间的个人赔偿从没有放弃,我国政府的一些领导人也发表谈话支持这个观点。而日方认为我们放弃的战争赔偿,既包括国家间的,也包含民间,亦即放弃的是所有的战争赔偿。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在于:二战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件个人对国家的战争索赔案胜诉过。国际上对此类案件的判决依据不同的法律体系(如大陆法系或海洋法系等)有不同的判决标准,日本采用的标准便是所谓“国无答责”,即因为战争是国家行为,国家就对个人没有义务作战争赔偿。我曾仔细阅读过日本法庭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案的几份判决书,也不能完全说他们强词夺理,糊涂官判糊涂案,人家的法律条款在那里摆着的,你控诉得再动情,他虽然也不得不承认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在他那里法就是大于情。我也采访过此方面的国际法专家,他认为要打赢这样的官司,得先从立法上入手,不仅是中国,日本也要重新制定法律条款,否则就一直在面对“国无答责”这样的老条文。索赔的路有多长,便可想而知。
孙:对于小说家来说,这目前还处于胶着状态的东西,下笔写来应当很棘手的吧?我在心里为你掂量,恐怕你用在这部分的气力与心力,要比还原重庆大轰炸历史场景要大得多。虽然我知道,你一向是不做一番田野考察就不会动笔,但是面对小说中有关日本的那部分,中间涉及到日本法律、法庭庭辩,还真是难为你。
范:的确如此。在处理对日索赔的法理依据时,花费的功夫比较大。这相当于你得去学习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还得熟悉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如二战结束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日之间的关系,从民间到官方的外交来往史,这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现在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教训是无法避免的,有些东西又不能不令人扼腕。但我也知道我们不能仅仅站在现在的立场评判当年。历史的一个功能就是用来学习、借鉴、总结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
我参阅过几次对日索赔的庭审记录和日本法庭的《判决要旨》,本来还计划去日本参加一次庭审,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采访了数十个去日本上诉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成员,据他们介绍,庭审时,日方代理人和代理律师几乎不作辩论,最多简单问几句。也许他们也清楚,大轰炸这样的历史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他们最后的判决书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史实,如果在法庭上辩论,只能是让他们的国家曾经犯下的罪行更加昭示于天下……我的感觉是:这并不是一桩简单的民间对日索赔案,后面涉及到的东西太多。
写作中,为了营造某种情节张力和塑造人物,我虚构了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的激烈交锋。这些交锋是以日方在《判决要旨》里体现出来的狡辩和推诿为依据的。
三 参与打官司的日本人说
这样不仅是在帮助中国人,也是为了日本的未来
孙:同为抗日题材,我对比了一下你在《吾血吾土》中塑造的战后日本人。能感到你在塑造日本人方面,形象多元丰满了一些。我甚至能感到一种角度与立场的变化。《吾血吾土》中的抗战老兵,当他得知昔日的老鬼子要重返故地之时,他的姿态是对决的。甚至视为生命“最后的对决”。这让人想到,让他们那一代人去做战后的和平之沟通,是不可能的。但在这一部,有了一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尤其是,有了参加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官司的日本律师。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有人物原型的吧?
范:在重庆采访期间结识了两个为大轰炸受害者志愿打官司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和田代律师。在为受害者长达十来年的代理诉讼中,他们至少三十多次自费来到重庆,所花的费用大约在几百万人民币。他们和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建立起了很深厚的友谊,当然他们自己也明确表示,自愿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打官司并不仅仅是在帮助中国人,还是在为日本的未来着想。这是两个自觉肩负起了大和民族责任的日本人,他们是彻底的反战派,认为日本应该牢记历史,谢罪赔偿,才不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我多次参与了他们的调查取证,见证了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也和他们一起喝酒、讨论、长谈。他们让我认识到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另一面。
其实每一个社会都是复杂而多维的,更何况人心和人的性格。一个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尽量厘清这种复杂性。包括我们原告团的成员,他们受各自文化的、社会属性等方面的影响,性格也体现出多重性,暴露出一些人性弱点,这些也并不因为他能走上日本法庭打官司就有所减弱或改变,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会把这种缺点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放大。
孙:在这些方面,你同样没有回避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范:但我是这样看的,对于一个来自草根阶层的普通百姓来说,让他承担某种社会责任,有点像让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演员唱主角,难免也会有演砸的时候。我认为对他们应持包容、理解的态度。他们不是平民英雄,而只是一群把自身利益无形中和民族情怀、家国责任连接在一起的普通百姓。他们骨子里还时常透露出重庆这个水陆码头城市的某些性格特征——耿直、豪迈、粗犷、坚韧、乐观、永不服输。而我们的某些历史,常常是由这些人在书写。
孙:不管战争的创伤怎样惨痛,和平依然是人类不得不做的思考题。和平的前提是理解,是倾听。在你这本书中,当作为日本人的菊香贞子,和长她很多岁的重庆女人蔺佩瑶成为朋友后,好奇于她的身世经历,竖起耳朵倾听的时候,体现出动人的倾听与理解的意愿。无论如何,这种恣态都令人感动。菊香贞子这个人物,有原型吗?还是你有意识地从来中国的不同日本人身上,综合出这么一个理想典型?
范:菊香贞子在和女主人翁蔺佩瑶的对话中有这样一段:“现在不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了,是和平与发展、对话与沟通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在梳理我们的近现代史时,我们很少认真静下心来,在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枪炮声早已远去的时代,反思战争、展望和平。长期的阶级斗争二元对立观,让我们总觉得到处都充满敌意。我想,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去做那种化解敌意、建立起对话和沟通平台的事,就像我们现在搞的“一带一路”,不就是要搭建沟通平台,求和平谋发展嘛。
所谓化干戈为玉帛,应算是世界上最值得庆幸的事情。中日之间,虽然我认为建立起对话和理解的机制还有待时间和机遇,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在民间,我们的确看到日本反战人士对日本当局的反对和发声。他们让我们看到中日友好的民间基础和今后的希望。因此,在我的这部作品中,菊香贞子这个人物是带有很大理想色彩的,她或许是我看到的许多个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站在一起,在东京街头散发声援资料的日本友好人士之一。一个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街头得到一个日本友人的支持,其受到的鼓舞远远大于在国内一百个同胞的掌声。
四 对小说家来说,被摧毁的爱情,
更能呈现战争的残忍与荒谬
孙:自从做了“人文”版面之后,我越来越不会从纯小说角度看小说了,总是想从中探讨一些历史与现实层面的问题。不过,如果尊重小说家的创造,还必须回到小说的人物与情节塑造。这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你小说中的爱情,好像沿袭着一种套路——《悲悯大地》、《吾血吾土》里都有,就是女主人公到晚年,总要面对两个爱她的男人。而在这一部里,作为初恋的飞行员刘云翔,最后还担起了呵护蔺佩瑶夫妻的责任。
范:或许这跟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些因为战乱、动乱而受到冲击的爱情悲剧太多有关,也或许跟我对命运的悲情主义态度相连。写重庆大轰炸,作为一个作家,讲故事的人,我想用一个被轰炸摧毁的旷世爱情来诠释战争的残忍和荒谬,应是比较妥帖的。在大轰炸的历史背景下讲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悲情的人生命运,总比空洞地描述灾难的惨状和死亡的数字好。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所爱,或一个男人被两个女人追求,这些都是亘古不变的爱情故事,亦即你说的套路之一吧,关键看你如何讲好这个故事。当然作家应该去写出套路之外的爱情故事,我想这也是每个作家的梦想。
孙:再有就是时空的穿插。《水乳大地》中,其实也存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你是以不同章节来隔开的,而眼前这部,一个章节里,就同时处理了两个时空。这无形间使人觉得,现实中的扯不断、理还乱,和过去的联系更紧密了。但也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让人觉得,每个人的现实性,因此拓展的维度不多。
范:时空的转换和时间的交错应该算是现代小说常见的一种技法。长篇小说这种表现形式给了你这样的空间,在同一个章节、甚至在同一个段落里转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空间,这都不会对读者造成某种阅读障碍,因为读者的阅读能力常常超越作家的表述能力。在时空转换中有时我会追求某种历史沧桑感,人物命运感,同样一个人物,在上一节里他正当年,雄姿英发,指点江山,而转眼到了下一节(段),就是他的暮年,饱经沧桑,历尽艰难,老了,认命了。我认为这里面会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经常借用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所有人的过去和现在,又怎么分隔太远,或者分割开来?当然其间展开的维度也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你认为该展开,我认为该省略。每个人读书都是根据自己以往的阅读经验来审视作家所提供的文本。
五 写这部小说
相当于回到青春原乡
孙:后记中你说,“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为它写一部书。”现在,你也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敬意。谈一个题外话,如果将重庆与你现在生活的城市昆明相比,你觉得它们带给你的创作刺激有什么不同?你还会继续写与它有关的小说吗?
范:重庆是我的“青春原乡”。我在那里上的大学。读书的时候并不惜福,不认为它会在将来的生活中如何影响我。只有在历经岁月的磨砺和时间的淘洗后,那些没齿难忘的片段,才会在回忆中熠熠闪光,传递出念旧的温暖。因此,回到重庆采访,体验生活,就有点回到“青春原乡”的感觉。如果说刺激,此为一种。尤其是,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对自己当下的生活心生厌倦,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了。三十多年前,我离开重庆来到昆明,感到这座城市如此明媚灿烂,如此清新奇妙,因此我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年华奉献给它了。现在我这个浪子想回到故乡去了,因此在创作《重庆之眼》时,很多时候我心底里将之视为“归来之作”。遗憾的是,又由于另外一些原因,故乡依然回不去,至少在目前这几年。至于下一部,它应该是一部和昆明有关的小说,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算是对接纳我的这座城市的回报吧。但愿我能做得尽量好,不让它失望。孙小宁
本期历史图片选自重庆出版社《抗战记忆——台湾征集图片集》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