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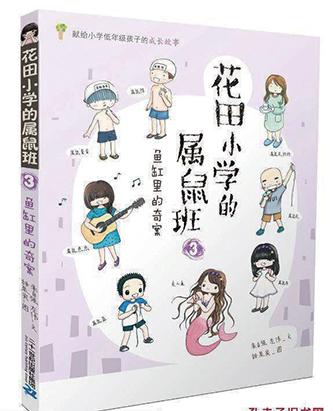


记 者:在儿童文学领域,您不仅始终坚持在场的批评,及时关注新人、新作,同时也对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有浓厚兴趣,出版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等著作,可以说,从史料发现、出版到现场评论,您的研究涵盖了儿童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您是如何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朱自强:如果把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它像成人文学一样,拥有自身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这三个领域。我本人对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有浓厚的兴趣,我的十卷本《朱自强学术文集》就汇集了这三个领域的学术成果(还包括语文教育和儿童教育)。
我认为,儿童文学史研究与儿童文学批评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历史目光与当代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有学术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才有价值判断的定力。对一个当代作家,对一部当下新作,如果将其放在一个历史的时空维度来考察,会作出更为合适乃至准确的价值估量。另一方面,儿童文学批评的见识也会影响到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如,对冰心的《寄小读者》,我会充分肯定它的文学史意义,但是,不会像有些研究者那样,在当代还将其视为儿童散文创作的艺术范型,也不会像有的研究者那样,在1990年代还将其视为“深沉博大”的儿童文学的样本。
记 者:如果说创作和批评是文学的两翼,那么您可以说是两翼齐飞。在从事评论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您还推出了《会说话的手》《花田小学的属鼠班》等原创作品。有人认为理论批评的理性思维与创作所要求的自由、想象力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自强:批评和创作属于不同的领域,正像你说的那样,这两项工作可能会发生矛盾,席勒就曾经说,在他自己那里,“时常碰到想象干涉抽象思维,冷静的理智干涉我的诗”。不过,我的感受也告诉我,理性和想象力并不总是必然矛盾、对立的,来自丰富的艺术体验的理论,对于创作是有帮助的。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我曾说:“我认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该是一种理想、一种预言,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该运用‘心’的想象力,揭示出当下还不是显在,但是不久将成为巨大问题的隐含状态。”这句话表达的是我对批评家这一身份的理解。我的《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和《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误区》,在“儿童文学热热闹闹,莺歌燕舞,形势一天比一天好”的情势下,指出“新潮”潜藏的“误区”。《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中,对“困境”和“出路”的阐述,以及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分化期”观点,都是我作为批评家,试图运用“‘心’的想象力”的一种努力。
我的理论批评来自我的艺术感觉。我不希望人们所说的“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这一情形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证明批评家的思想也可以是鲜活的。我想追求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境界。
虽然文学艺术在发生之初,可能是感性的,但是,随着人类心智的发展,今天的文学创作已经不可能排除理性的介入,特别是在作品的谋篇布局这一艺术结构的营造方面。举我自身的创作为例作一下解释。《花田小学的属鼠班》里的《夏老师叫什么名字》这个故事,写小学一年级男孩属鼠灰对夏老师油然而生的情感。最初,属鼠灰只是与夏老师去开玩笑,第一次下课,他跑到夏老师身边问,“老师,你是不是姓夏?”“我是姓夏。”“你是不是叫夏天?”“是,我是叫夏天,要不,今天怎么这么热呢。”第二次, “老师,你是不是姓夏?”“我是姓夏。”“你是不是叫夏(下)雨?”“是,我是叫夏(下)雨,一会下大雨,一会下小雨,有时还下冰雹呢。”属鼠灰和同学们捂着脑袋,“快跑,老师下冰雹了!”第三次,属鼠灰让夏老师“下”了雪。第四次,属鼠灰对夏老师说,“老师,今天你叫什么,你猜不到。”他突然把背在身后的右手举到夏老师面前,手里是一只癞蛤蟆。夏老师吓得往后一跳,“今天你叫夏(吓)一跳。”夏老师老老实实承认:“我是吓(夏)一跳。”第五次,要下课时,夏老师对大家说,“你们猜猜今天我叫什么?我叫夏(下)课。你们老师来上班了,明天起我就不给你们代课了,但欢迎你们有事到办公室找我。”说完,下课铃声响起,夏老师走出了教室。接下来结尾的情节设计就与理性、逻辑思维有关了。按照故事的逻辑,属鼠灰肯定会对夏老师依依不舍,但是,他会怎么做呢?我们为此费了心思。最后想到,开了那么多次玩笑,属鼠灰并不知道夏老师叫什么名字,于是写下了这样的结尾——“属鼠灰看着夏老师的背影,心里一阵恋恋不舍。他突然想到,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夏老师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属鼠灰站起来,飞快地朝夏老师的背影追了过去。”这个结尾的处理,就有理性思维在起着重要作用。逻辑不清、逻辑混乱的人,也许就想不到属鼠灰问来问去,就是没有问夏老师的真实名字这件事。另外,这个结尾的构思,也与我和左伟想把故事写得既有趣、又有益这一创作理念有直接关系,与我们对某些浅薄搞笑的写作的不满有关系。
绘本《会说话的手》的创作灵感来自旅途。我在飞机上看到从椅背前面伸到过道里打斗的两个孩子的手。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绘本的创作素材,因为作为绘本研究者,我知道绘本创作必须是“视觉的”!而在这本表现“身体”的绘本的背后,也有我的儿童教育理念支撑。我在2005年撰写的一篇儿童教育哲学的论文中就提出,身体实践的生活对于儿童教育是第一位的。
在《会说话的手》中,情感、想象与理念结合的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结尾的画面:小狗虎头用手对“我”说,“抱抱我”。梅子涵教授曾说,因为有这一情景设定,《会说话的手》“大”了起来。我理解他所说的“大”是“厚重”的意思。我在我校的行远书院所上的核心通识课《大学之道》,有一讲是“人与环境”,就涉及到人与自然沟通的思想。我也知道在儿童的成长中,小动物的陪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仅靠这些“观念”未必能生出“虎头也会用手说话”这一创意。就在我写《会说话的手》的前几个月,我儿子捡回来一只三个月大的流浪猫,我们给它取名叫克洛伊。那时,克洛伊每天在我怀里,我用“手”爱抚它,它会扬起脸回头看着我,像小羊一样,“咩”的叫一声,我感到就像叫“妈妈”一样。克洛伊要我陪它玩儿,或是要我给它拿好吃的,也会走到在电脑前正在写作的我的身边,站起来用左前爪搭住我的右手臂,我一转头看它,它就走开,意思是说,“来呀,来玩啊”。如果没有我与克洛伊这样用“手”进行交流和表达的情感生活,我很难想象我会凭空想出绘本中虎头用“手”说话的这一情节。
记 者:我注意到,近年来您多次提到关于图画书的相关问题。在当下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图画书的主体是引进外国作品,原创的图画书缺乏市场竞争力。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原创图画书的整体水平?
朱自强:原创图画书刚刚兴起,我认为,图画书评论界发挥的作用很重要。图画书研究者、评论者的鉴赏能力也有一个需要提高的问题。从目前的某些图画书评奖包括评论中所体现的图画书艺术评价标准来看,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点,对图画书的创作而言,必须重视创意性。我感到,目前的某些图画书评奖中包括评论中所体现的图画书艺术评价标准,对创意性是有所忽视的。
第二点,对给幼儿的图画书关注得不够。创作给幼儿的图画书,是对儿童图画书艺术创作能力的严苛考验。衡量今后中国原创绘本的发展水平,幼儿绘本的创作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记 者:多年前,您曾提出“快乐语文”的概念,并且主编过“快乐语文读本”,强调语文阅读的趣味性、艺术性和教育价值相结合。在当下,“趣味性”是目前语文教育的一大缺失。您认为当下语文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朱自强:当下的语文教育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谓一言难尽。不过,首要问题是要树立健全而有效的语文观、文章观。目前,被普遍奉行的是“工具论”语文观,语文教学的许多“少慢差费”的情况,其实与“工具论”语文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一书中,反思“工具论”语文观的局限,在其对立面上,提出了“建构论”语文观。我所谓的“建构论”语文观,不是像“工具论”语文观那样,只是把语言看作“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是把语言看作是人类心智世界的建构物、创造物。“建构论”语文观对语言的功能有着更为全面、完整的认识,认为语言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传达信息(含“工具论”所说的“交际”功能)、认识世界、表现心灵这三个功能。持着“建构论”语文观,我认为,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用语言建构、创造意义,进而发展健全心智世界的能力,获得用语言来传达信息、认识世界、表现心灵的能力。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对具有建构性、创造性的语言的学习,发展学生个人心智的一种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创造性的人。
我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要想健康发展,必得离开“工具论”这条坑洼小路,走到“建构论”这条康庄大道上来。
记 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您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已经有30余年,这当中心态有什么变化?当下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朱自强:不论是此前还是今后的人生,儿童文学是命运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因为在学术研究、翻译和创作这三个领域从事着儿童文学事业,我不断实现着自我价值,有效地以儿童文学为方法,解决着自身的问题,思考着人类的根本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我所言说的儿童文学,对于我而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此前如此,今后亦如此。
如果说心态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加重视儿童文学的实践性了。对儿童文学学科的性质,我提出了两大属性,即学术上的跨学科性和实践上的应用性。今天,儿童文学越来越成为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我相信,儿童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一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本人,今后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就是要做视野广阔、根基深厚的有格局的学者,就是争取成为立足于肥沃而广袤的儿童文学土地上的教育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