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等喜欢借古希腊的神话题材,解释现代世界的荒诞与黑暗;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这样的当今作家,则善于在他国文明以及个人记忆中挖掘普通人生活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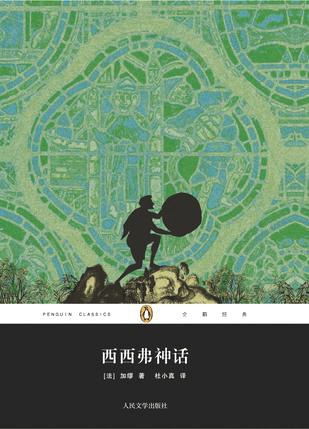
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等喜欢借古希腊的神话题材,解释现代世界的荒诞与黑暗;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这样的当今作家,则善于在他国文明以及个人记忆中挖掘普通人生活的真谛。

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等喜欢借古希腊的神话题材,解释现代世界的荒诞与黑暗;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这样的当今作家,则善于在他国文明以及个人记忆中挖掘普通人生活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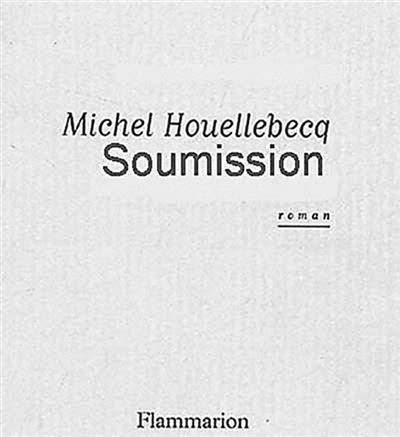
《臣服》(法语:Soumission,或译《投降》)是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在2015年1月出版的小说,以法国在2022年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为背景。该书的法文版初版印刷15万册,出版后迅即登上法国亚马逊畅销榜首位。《臣服》的敏感题材使得它未出版已在法国引起话题,有人批评维勒贝克的“极右惊吓故事”煽动伊斯兰恐惧症。2015年1月7日发生《查理周刊》总部枪击案后,维勒贝克停止为自己的新小说宣传。

《2084》 作者:(阿尔及利亚) 布阿莱姆·桑萨尔 译者:余中先 版本:海天出版社 2017年1月
“反乌托邦”小说流行
由现代人生存危机感引发
《2084》出版后,法国舆论基本一片叫好。这当然与彼时彼刻的形势有关。小说是2015年秋季出版的,11月时,巴黎等地接二连三地遭受了系列恐怖袭击,让人们对未来有所忧虑,有所反思。
正面的评价,可列数《快报》的观点:“寓言,政论,小说,以一种幻影般的文笔描绘出并无历史指涉的一种独裁统治,《2084》足以诱惑读者”;《电视万花筒》的记者米歇尔·阿贝斯卡认为:“寓言是强有力的,幽默是带破坏力的,话语是冷冰冰的。《2084》确实非同一般,作者提出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危险始终存在。”
至于相对温和的评价,则有《观察家》:“作为一部寓言小说,《2084》的教训令人痛苦,使得叙事变得抽象,妨碍读者对主人公的命运产生兴趣。文本本身则带来一种渎圣的快感”。而比较否定的评价,当数《巴黎竞赛画报》了:“再过二十年,当法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洪流再度泛滥时,人们会问,当初如何就盲从了一部如此拖沓的惊悚小说。”
就在《2084》出版前,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畅销小说《臣服》出版于2015年1月7日,当天恰逢巴黎《查理周刊》遭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袭击。作者本人受到死亡威胁,新作推介活动被迫停止。而这本小说同样有政治和宗教的大量隐喻,包括预言某宗教极端派政党赢得法国大选,其虚拟时空的设定也增加了故事可读性,为作者表达其政治和宗教立场提供了方便,而其“直击当代西方人的焦虑情绪”的严肃主题和无独有偶的出版日期,让小说本身大受关注。
纵观世界文坛,此类现象也比比皆是。2005年,法国的维勒贝克以人类克隆和以克隆技术为基础的社会邪教信仰为主题写出了《一座岛的可能性》,作品写某个小小的邪教组织是如何通过倡导盲信的宗教和恐怖的暴力手段控制了未来的人类。小说很受欢迎,批评界甚至预测它能获当年的文学大奖;2009年,日本的村上春树以当年“赤军连”学生运动以及奥姆真理教等社会事件为故事主线,虚构了《1Q84》,其主题俨然是对邪教组织和恐怖主义的深刻反思。
这些带有反乌托邦味道的小说,都赢得了读者的青睐,究其原因,与暴力恐怖、极端专政、宗教盲信、伪科学邪教给现代人带来的生存危机感有很深的关联。读者对未来忧心忡忡,需要从这类文字中得到启迪,或某种洗礼,或某种升华。
《2084》的意义
总有一个人在探求世界的可能性
说到法国乃至西方的文学传统,借古讽今或借未来而喻当下,是很多作家思考和涉及当代现实时常用的手法。拉封登的寓言诗借动物界的狮狼犬羊来代言社会各色人等;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勒萨日往往借用西班牙的故事来影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等喜欢借古希腊的神话题材,解释现代世界的荒诞与黑暗;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这样的当今作家,则善于在他国文明以及个人记忆中挖掘普通人生活的真谛。而近来种种“反乌托邦”小说,也自然而然地在未来世界中寻找思想的空间与虚构的可能,总之,在法语文学中,这种在“别处”寻找生活的写法,既与文学传统一脉相承,而每个时代每个作者又各有各的招数。
人类发展的每个时代,可能都有恶魔存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1948年启迪了奥威尔的《1984》,而今天的人对宗教极端狂热、宗教蒙昧主义、恐怖主义的深深忧虑,则启迪了《2084》的诞生。而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1992年的历史小说《金字塔》中体现的,也是人们头脑中对极端专制的古埃及法老、铁骑踏遍欧亚大陆的蒙古大汗等人面恶魔的类似的谴责。
无论是指向未来的反乌托邦小说,还是指向往昔的历史小说,强调的都是人要争取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反对绝对盲从。探究为什么,始终是这些注重人文关怀的作家的首要话题,也正是这一与人类未来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
在中国,阅读和谈论《2084》同样并非没有现实意义。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任何极端恐怖主义、极端专权信仰,都会有一定的小小市场,都会给人类带来大大的伤害,甚至毁灭性的打击。读者当然都不会愿意来到《2084》中的阿比斯坦国,在“彼佳眼”无处不在的监视下生活。那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地狱。
于是,“为什么?该怎么办?”的问题必须提出,必须思考。好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恐怕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想探求真理,这就是《1984》中的温斯顿,《2084》中的阿提。创造这样的人物,让他们引导我们一起去思索世界的种种可能性,这就是文学作品有别于其他劳动行为创造世界的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说,桑萨尔先生是在用文字向恐怖、暴力、极端专制挑战。
□余中先(法语翻译家,《2084》译者)
■ 延伸
《2084》与《1984》的互文性
一读到《2084》这个书名,第一反应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紧接着,又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1Q84》,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等。
应该说,桑萨尔的《2084》跟奥威尔的《1984》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2084》通过对《1984》形式结构的某种摹写,写出了作者对未来某个专制主义国家的描绘和思考。
《2084》与《1984》确实存在着内在联系,其互文性是明显的,可以说,《2084》是对《1984》的某种形式的致敬。
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小说《2084》中,直接就出现了“1984”的字样:当年,西恩疗养院矗立起来时,镌刻在要塞那宏伟大门半圆形拱顶上方石头上的一条碑铭,显示了数字“1984”,恰好“位于两个风化得面目全非神秘难解的符号之间”。
在《1984》中,我们经常读到并为之惊愕的一个句子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而在《2084》中,则是同样的警示在提醒公众:“彼佳眼在观察你们!”老大哥的原文为“Big Brother”,而彼佳眼的原文为“Bigaye”,两者何其相似。作者甚至还在《2084》中特地解释说:彼佳眼是一种俚语中的一个词,说的是类似“老大哥”“老家伙”“好同志”“大头领”的意思。
在《1984》作品的最后,奥威尔以大量篇幅“附录”了一篇“新语的原则”,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所谓“新语”的构成规则和使用特点,而在《2084》中,作者桑萨尔对阿比朗语的描述,也是不惜笔墨的,而且,也安排在故事叙述的最后面,即“尾声”之前。桑萨尔在书中强调:《噶布尔》之前的圣书是用一种很美、很丰富、很具暗示性的语言写的,它因更倾向于诗意化和雄辩术,而被阿比朗语所代替,阿比朗语的概念则得到了《1984》中“英社的新语的启迪”,它尤其致力于强调公众的“义务责任和严格的服从”。而这语言,完全“有能力在说话人心中消灭意志与好奇”。
《2084》与《1984》的互文性还明显地体现在一些词汇的选择与运用上。例如纳迪尔这种电子墙报(电屏),再如,小说最后,作者借研究20世纪古老文明专家陀兹之口,道出了阿比斯坦思想路线的三原则:“死亡即生命”“谎言即真相”“逻辑即荒诞”。这分明就是对《1984》中“英社”政治制度创建三原则“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影射和发挥。而无所不在又始终不露面的神主尤拉,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老大哥”。(节选自《2084》译后记)
反乌托邦文学
与乌托邦相对,指充满丑恶与不幸之地。这类小说通常叙述一种表面充满和平、本质却虚荣空洞的社会。在反乌托邦的社会,人类丧失自由、物质浪费蔓延、道德沦丧、阶级制度横行。代表作有英国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和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