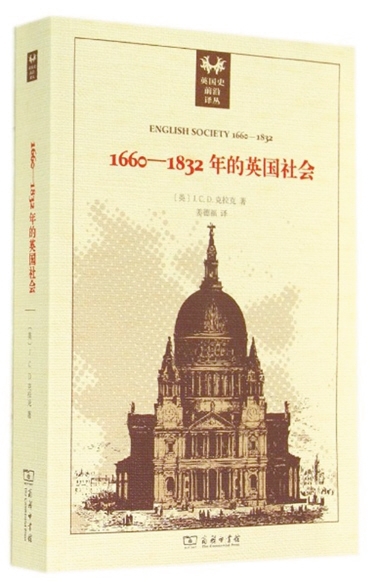 《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 作者:J.C.D.克拉克著,姜德福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4年8月 一声低低的叹息从那一年将收成全部捧出的田头传来, 干草垛立在田头阴沉沉地对着太阳, 那声音低吟:“完了啊,来吧,蜜蜂以及飞离了三叶草,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拉迪亚德·吉卜林,《长长的小径》 壹 “值得漫长回忆的18世纪” 英国诗人吉卜林用这么一首诗来哀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的衰落。十八九世纪的英帝国确实拥有着许多的荣誉,相较于欧洲大陆的绝对主义政体,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成为保证自由的优良政体得到同时期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考察与论述。政治上的稳定性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同时,也由于这样的稳定性,成功地避免了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一样的剧烈动荡。在法国,随着三级会议的召开,各式各样的政治理论与理念,君主立宪、共和、无套裤党人的专政,轮番上台表演,无数政治家的鲜血也成为了浇灌着这块政治试验田的肥水。相比之下,任何一种新奇的政治观念与理想都很难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吸引足够的看客。并且在皮特的领导下,成功地抵抗了革命的法国。这些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如果说,英帝国是一个夏天,那么18世纪的英国就是这个夏天的正午了。 克拉克的著作《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主要描写的就是这个夏天的正午所发生的故事。克拉克把英国的18世纪称为“漫长的18世纪”,其实在他心目中更毋宁是“值得漫长回忆的18世纪”。 这本书名为《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乍看之下很可能会以为是一本流行的“社会史”著作。通常所理解,社会与政治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反思能力的,而政治却具有这种主动性,改革者、革命者、保守派们在不断地斗争中,将自身的理智,公众的意见以及时代的潮流都统统融贯在一起。因此,“社会史”与“政治史”相应地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18世纪英国宗教观念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的变迁。因此,作者就赋予了“社会史”不同寻常的含义。作者认为,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之前,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史”都具有更广阔的内涵。“‘社会史’在18世纪和20世纪不可能是同样的一回事。”(P.9) 在主旨上,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强调延续性、集体意识和人的神圣性的著作”(p.2),“是一部表现中间立场的著作”(p.24)。换言之,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18世纪英国的社会共识、政治共识如何实现并稳固地持续下去(到1832年?)。 作者认为,在社会共识、政治共识凝聚的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作者看来,18世纪的英国是建立在新教为基础的“新教体制”。事实也确实如此,18世纪英国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稳固性的特征是以宗教为基础,更加准确地说是以英国国教安立甘宗为基础的政治与社会体系。这一稳固的体系是在“光荣革命”这一时刻取得的。“光荣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宗教、政治寡头的一次巨大妥协,而传统的国教以及悠久的王权成为此类妥协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宗教上的这种主导性颇容易让人联想起现时代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各种政治秩序。 贰 缺陷:“小英格兰”主义 作者把这本书限定于英格兰,这是该书最大的缺陷之一,并且不免被人指责带有“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主义的缺陷。事实上, 在18世纪英国新教体制的形成过程中,苏格兰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点也正如作者所言,对于英国民族性的形成,“更重要的时刻是1603年的王位合并。相反,除了自由贸易和爱丁堡议会被纳入威斯敏斯特议会外,1707年的条约没有触动任何东西。”且不论是否正如作者所言,1603年的王室合并的意义确实远大于1707年,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苏格兰不列颠宗教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凝聚过程中所起到过的重要作用。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成为詹姆斯一世确实带来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两国更加稳固的联合,对于英国民族特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斯图亚特王朝一同到来的还有绝对王权的理念,这对于议会主权的政治共识是一大冲击。内战的爆发是这一冲突的政治表达。而随后苏格兰长老会的介入则更加有可能颠覆英格兰议会主权这一哥特传统,甚至颠覆新教尤其是英格兰国教。不过,不论是议会的胜利还是克伦威尔在沃尔赛斯特对长老会的大捷,这一切都发生在1660年之前,即在《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论述范围之外。不过,这并不能成为忽视苏格兰,忽略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议会联合的充足理由。相反,任何一本涉及18世纪英国政治与宗教共识的著作都不应忽视“苏格兰问题”的解决。 然而,这是一部关于延续性的著作,同时这也是一部关于统治核心区的著作,它试图为人们呈现出18、19世纪繁盛的英帝国内部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奥秘。这是本书的主旨。因此,这本书没有集中处理的问题无疑是延续性之外的断裂。一个社会的稳定无疑依赖于多数人意见的统一,然而,一旦社会绝大部分人都慵懒地屈从于一种意见,并且更严重的是体制对思想自由与言论的自由表达进行严酷的压制,那么,这个稳定的体制除了稳定本身之外一无是处。它缺乏自由,更有可能背离真理。用约翰·莫雷的话来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人们懒散地顺应形势,默认将错就错,卑鄙地精于算计而不顾真相,为了暂时的利益背弃普遍原理,进行邪恶的妥协,损害永久的利益”。因此,对于社会、政治的运动与发展来说,偏见、乃至暂时性的错误有时候往往比毫无原则的所谓共识更有价值。对于,人性的光辉更加如此。社会因共识而稳定,因异端而前进。 叁 核心区历史叙事中的边疆史缺失 相对于核心地区的历史而言,边疆史往往更加恢弘,更具有戏剧效应。在18、19世纪的英帝国中,这种断裂集中体现在1776年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并不仅仅表现为它宣布十三个殖民地在政治秩序上不再隶属于英国这一秩序,更主要的是,它在政治思想与理念上造成了断裂。傲慢的“议会主权”在美洲殖民地再也行不通了,从此北美开始脱离殖民地的地位,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叙事与政制表达。断裂性的缺失看来是本书又一最令人遗憾之处。不过,读者可以在克拉克的另外一本著作《自由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Liberty)中找到关于这种断裂的论述,弥补这本书由于主题所限而带来的遗憾。 关于这次断裂的描述是18世纪英帝国史中最为宏伟的一部边疆史。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次断裂所造成的宏伟边疆史真正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开启了新天地。然而,正如美国电影《利益风暴》(Margin Call)投行老大最后所说的那样:“1637年、1797年、1819年、1837年、1857年、1884年、1901年、1907年、1929年、1937年、1974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0年、还有这次,不管我们叫它什么,一样的缘故,一次又一次,我们挡都挡不住,我们还想阻止它,控制它,甚至放慢它,我们的本性一丁点都没变,我们仅仅是随机应变,如果对了就赚一大笔,如果错了就被晾到一边,这个世界上过去会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比例的赢家和输家,得意洋洋者和垂头丧气者,撑的撑死,饿的饿死,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许前所未有的多,但是那个比例,原封未动。”现在所发生的,在过去的多少个世纪前都已经发生过了。而这才是断裂之外真正的延续性,不论在股票投机的经济领域还是在选票争夺的政治领域,也不论它处于哪种社会形态下,处于哪种政治制度与政治理论之中,同样比例的输家和赢家,历来如此,从无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克拉克“小英格兰”的傲慢也正是这种延续性的一个写照,尽管18、19世纪英帝国的余晖早已散尽。 然而,瑕不掩瑜,《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仍然是一本充满洞见,并值得相关研究学者以及一般读者参考、阅读的著作,尤其是在处理宗教与稳定的政治体制之间关系时有着独到的见解,足以为读者理解英国“漫长的18世纪”提供有益的指导。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