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鲁迅的文化遗产
无论你承认与否,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一个特异而丰富的存在。南京求学时受进化论影响,立志科学救国;留学日本时弃医从文,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为无产阶级革命呐喊助威,逐渐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他以文艺为武器,深入解剖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他把国家独立、民族振兴、民众觉醒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性格,但有时也敏感多疑、孤独忧郁;他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生死,珍惜生命,也不畏惧死亡。
纵观鲁迅的一生,其创作和译介丰富,他用文字影响了一代代读者。毛泽东同志说过“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引用鲁迅的论述。
在鲁迅留给这个世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有一部译作是十分被他看重的,那就是直到他病重之时依然坚持翻译的《死魂灵》。

鲁迅晚年多写“杂文”,小说创作很少,几乎没有大作品,因此招来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他不搞创作,特别是不写长篇小说,却写杂文或翻译些佶屈聱牙的苏联文艺理论,是浪费才能。他本人则认为杂文贴近社会,批评人生,能立即起到作用,自有其价值。至于翻译,他也不赞成“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的说法,而主张尽可能多地翻译外国作品,给中国的创作者提供丰富营养。哪怕译得不好,也比没有翻译强。
其实,鲁迅晚年在创作和翻译上均想有所作为。他至少有两个中长篇小说写作计划,一个是红军战斗题材。红军将领陈赓在上海养病期间曾拜访鲁迅,向他介绍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情况,鲁迅询问了很多细节,还收藏了陈赓随手画的地形图。他初步设想参照苏联小说《铁流》,写一部反映红军战斗情景和苏区生活的中篇小说。但因为素材不充分,加之不熟悉军事生活等原因,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另一个是一部叙述中国近现代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是1936年上半年鲁迅与冯雪峰谈话中透露的。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几次谈到的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代),可以说是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他说:‘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而且关于前两代,我不写,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他已经考虑到结构,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小!’……也谈到长篇小说的形式问题,说:‘可以打破过去的成例的,即可以一边叙述一边议论,自由说话’”。可惜,当年秋天,鲁迅病逝,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
至于翻译,鲁迅在去世前一年终于下定决心,“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这就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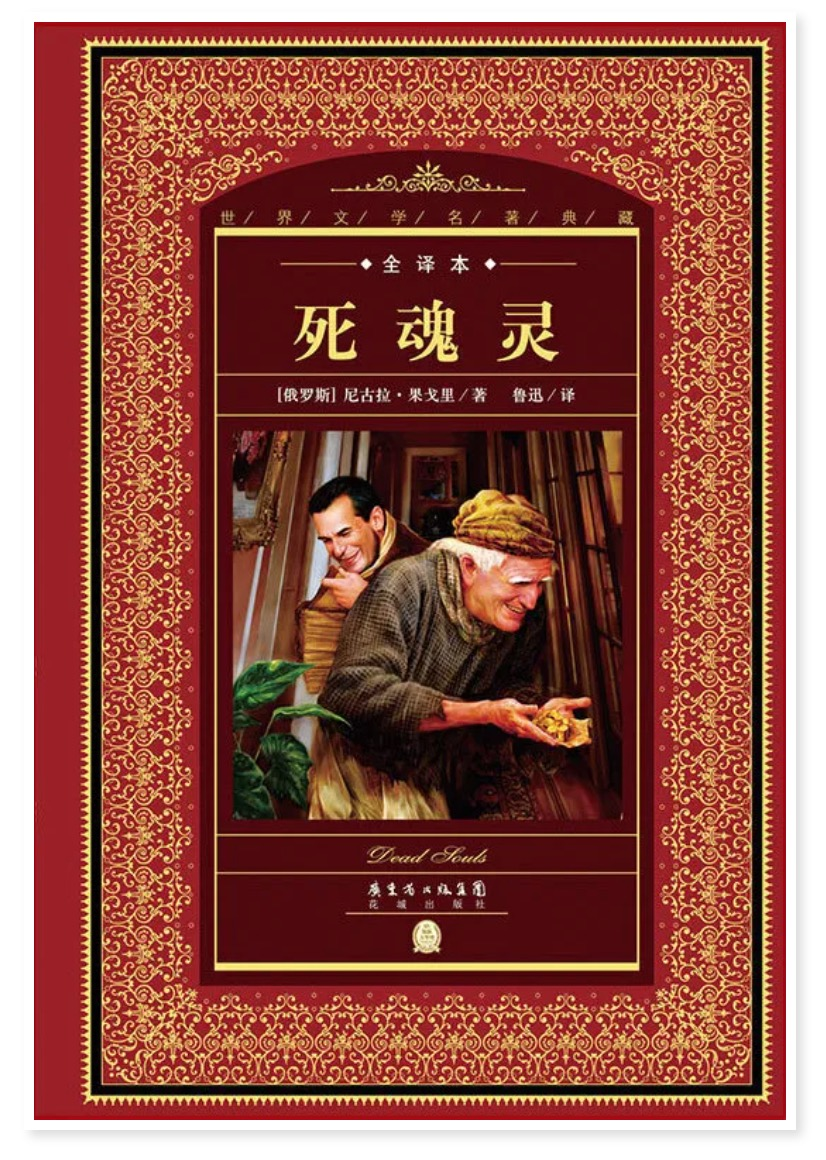
鲁迅为什么选择翻译《死魂灵》?表面上看,是他自己想翻译世界名著的愿望,又恰遇朋友的邀请或出版商的安排。但究其根本,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鲁迅年轻时候喜欢俄国文学。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俄国文学正风行日本,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大量被翻译成日文,德文译本也不少。鲁迅第一次提到果戈理,就满怀热情,高度赞扬:“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W.Shakespeare),即加勒尔所赞扬崇拜者也。”他在杂志上看到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果戈理小说《狂人日记》,很喜欢,特地收起来,放进自己的剪报夹。这篇小说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巨大。十年后,他写了同名小说,登上文坛,成为新文学的代表。假如鲁迅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中所受到的外国作家的影响,在一长串名单中,果戈理应该排在靠前的位置。
假如鲁迅懂俄文,他或许早就开始翻译果戈理了。1929年6月21日他在一封信中说:“耿济之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懂俄文,但我看他的译文,有时也颇疑心他所据的是英译本。即使所据的是原文,也未必就好,我曾将Gogol的《巡按使》和德译本对比,发见不少错误,且有删节。”他如此关注果戈理著作的翻译,是因为他自己也有翻译的计划,具体地说,是联合通俄文的孟十还翻译《果戈理选集》。孟十还翻译俄文书的水平,鲁迅是了解的。
1935年2月15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了“译《死魂灵》一段”,是他翻译《死魂灵》的开始。他与出版方约定:先在《译文》杂志上刊登,随后收入郑振铎所编《世界文库》丛书。
鲁迅接受翻译《死魂灵》的工作,意味着,他与孟十还的编译计划成形了。他们计划中的《果戈理选集》共6卷,一年内出完。
《死魂灵》是蜚声世界的名著,其时中国已经有译本。鲁迅翻译前,找来中译本阅读,感到水平不高,因而坚定了重译的决心:“昨天看见辛垦书店的《郭果尔短篇小说集》内,有其第二章,是从英文重译的,可是一塌胡涂。”他将这个译本同德文本做了比较,发现很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地方又都是这个译本不好,鲁迅推断这位译者是“对于英文也并不十分通达的”。他购买了日译本《死魂灵》,研读后评论道:“上田进的译本并不坏,但常有和德译本不同之处,细想起来,好像他错的居多,翻译真也不易。看《申报》上所登的广告,批评家侍桁先生在论从日文重译之不可靠了,这是真的。但我曾经为他校对过从日本文译出的东西,错处也不少,可见直接译亦往往不可靠了。”这又坚定了他从德文转译的决心。
不过,复译、转译,均非易事。《死魂灵》写法虽然平铺直叙,但行文含义丰富,用鲁迅的话说,是“到处是刺”,而且果戈理的讽刺“千锤百炼”,如果不能译出原作的锋头,就索然无味。19世纪各种物件的名目,使鲁迅大伤脑筋,弄得他“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昏头昏脑,后悔自己太小看这部著作了。
鲁迅翻译《死魂灵》的艰苦远不止这些。《死魂灵》要按期连载,需要赶工。鲁迅同时还编辑《译文》,既要翻译其他作品供给杂志,还要处理编辑事务,兼顾多面,分身乏术。更大的问题还在身体。他给朋友写信诉苦说:“《死魂灵》第三次稿,前天才交的,近来没有气力多译。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并停止抽烟;有几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为了种种缘故,一时也做不到。”
在翻译《死魂灵》期间,《译文》停刊,鲁迅同书店之间产生了矛盾。有小报造谣说,郑振铎同鲁迅不睦,腰斩了《死魂灵》;也有人说鲁迅与书店反目,中止了翻译,闹得沸沸扬扬。鲁迅又不得不分心来辟谣。
鲁迅就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夹攻下坚持译事的。译完第四章,他写信给黄源诉苦道:“《死魂灵》第四章,今天总算译完了,也到了第一部全部的四分之一,但如果专译这样的东西,大约真是要‘死’的。”1935年7月27日,他写信给萧军说:“我此刻才译完了本月应该交稿的《死魂灵》,弄得满身痱子,但第一部已经去了三分之二了。有些事情,逼逼也好,否则,我也许未必去翻译它的。”
鲁迅的韧性和毅力最终胜利了。1935年9月底,鲁迅完成了《死魂灵》第一部的翻译。
接下来,鲁迅译序言,编附录,尽量为读者提供更多参考资料。例如《果戈理怎样工作》一文,他看后觉得有用,就敦请朋友翻译:“我看过日译本,倘能译到中国来,对于文学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不过从日文翻译,大约未必译得好。现在先生既然得到原文,我的希望是给他们彻底的修改一下,虽然牺牲太大,然而功德无量,读者也许不觉得,但上帝一定加以保佑。”
《死魂灵》先出版了平装本,继而出版布面本。1935年11月16日,文化生活书店的吴朗西给鲁迅送来五本《死魂灵》布面装订样书。
鲁迅对这部倾注巨大心力的译作很满意。在给一位来信索要他的著译目录的读者的回信中,他写道:“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
他感谢同他一起策划翻译果戈理作品集的孟十还。他在一封信中说:“从三郎太太口头,知道您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忍释’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特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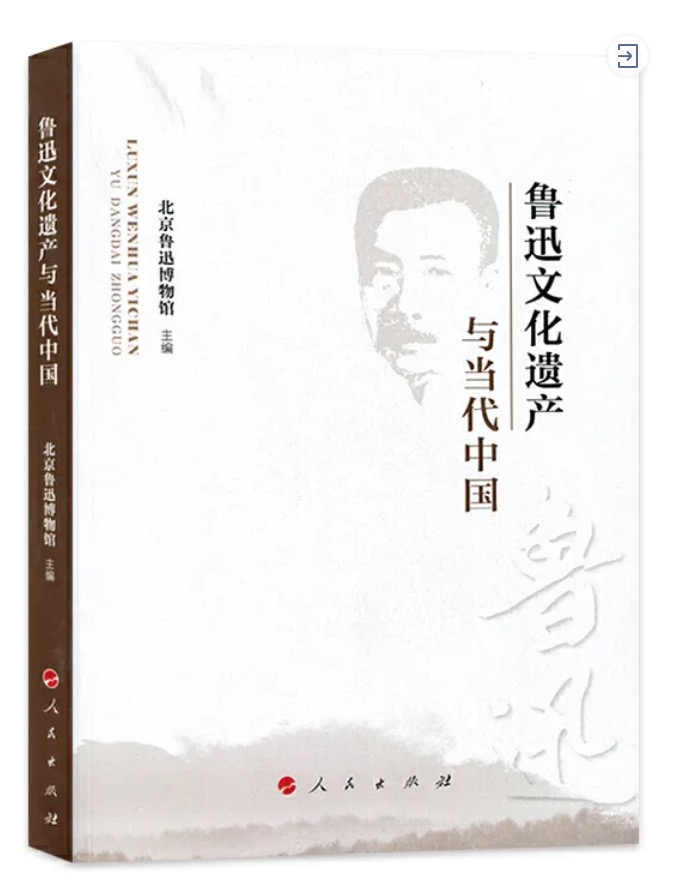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