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主义的话题似乎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在欧美,由好莱坞的MeToo运动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打破沉默者”;在日本,纪录片《日本之耻》的影响,为伊藤诗织赢来了时隔四年的艰难胜诉;在中国,不时出现的有关生育难题、职场骚扰、家庭暴力等具体事件,也常常引发社会范围内对女性现实处境的广泛热议。成为女人的焦虑与作为女人的挣扎,是几乎所有女性穷极一生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而在文学的世界中,为什么写作与怎么写出自己的声音,更是让一代代女作家备受困扰的难题。2019年,在中国当代文学新作中,几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聚焦女性成长,似乎与当下的社会热点形成了某种呼应。但是,与全球范围内女性意识的又一次觉醒相比,我们的文学书写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映照出的是当代中国女性的命运,而对这些人物的想象与塑造,也进一步透露出女作家对自身性别的思考,以及我们的文学书写与现实生活之间所存在的距离。 一 付秀莹的小说《他乡》(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中,呈现了一个由农村到城市的知识女性所遭遇的婚姻、情感、事业等种种波折,也映衬出了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以及内心图景。小说主人公翟小梨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女性,尽管她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教育,生活在北京这样现代化的城市,甚至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女强人”,但是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依赖那些能够对她施以保护的男人,她对一段“夫荣妻贵”关系的渴望,更体现出她对于女性可以成为甚至应该成为男性附庸这一角色的某种认可。  付秀莹《他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 这或许与翟小梨的成长环境有关。在小说中,每当翟小梨失意沮丧时,总会念叨起“在我们芳村”,“这要是在芳村”,“芳村有句话”……“芳村”对于小说家付秀莹来说,是她笔下“邮票大的故乡”,从早期的《爱情四处流转》《那雪》等中短篇小说,到上一部长篇《陌上》,付秀莹用文字搭建起一个以传统伦理价值为根基的乡土世界。乡土社会的风俗、伦常、人际关系等,都让付秀莹津津乐道,而现代性对传统乡村结构、伦理的侵扰,也不断成为她所青睐的书写对象。 按照费孝通的观点,在乡土中国,“婚姻不是件私事”,而是一种以生育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是人类种族延续的保障,父母双系抚育则是其基本方式①。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男性对于一个家庭的责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在婚姻关系中,翟小梨时刻渴望的,正是以芳村为代表的乡土传统中对丈夫、对这个一家之“主”的要求与期待;她感到不满的,恰恰是丈夫章幼通及其家庭未曾履行的、乡土传统中视为理所当然的“责任”,而这“责任”,反而是溢出了以个体独立、两性平等为基础的现代婚姻观念的,甚至更暗示着另一种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他乡》看似聚焦翟小梨在他乡北京的生活,但其精神实质指向的却是故乡芳村;小说看起来描写的是城市人的城市生活,但是内在的价值观却明显是属于传统乡土文化的。 戴锦华在谈及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变迁时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作为秦香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和花木兰——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②。小说《他乡》中,翟小梨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她看起来是现代都市里的花木兰,但实际上,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是甚至渴望一直能做个秦香莲般的弱女子。翟小梨既自卑又自傲,一个农村出身的大专生,自考、考研,留在北京,最后成了女作家,可以说是标准的凤凰涅槃故事。“我,一个芳村来的女人,一个外来者,尽管渺小,卑微,不足道,然而,我终究是汇入了这座城市的早高峰的人潮中了”③,这话看起来卑微,却隐含着一种骄傲。芳村,以及芳村所代表的价值观,既是翟小梨融入现代都市的绊脚石,又是她的精神药膏。在社会公共场域中,翟小梨不得不扮演一个现代文明培育出的新女性,但是,她对婚姻、对人生、对社会的评判标准,甚至她的整个价值观都是在芳村形成的,精神深处的翟小梨,始终是那个来自芳村的小女人。 在任何一段男女关系中,翟小梨都是“被观看”的客体,不管是章幼通眼中的“一只稚嫩的小母鸡”“一头漂亮的小母牛”,还是管淑人床上那“疯狂的妖娆的小兽”,“小女人”是作者对翟小梨的定位,也是翟小梨对自己的定位。“小”,于女性,仿佛是一种美德,因为小,所以娇弱,所以需要被保护,也因此容易被掌控。翟小梨当然清楚这一点,她甚至有点认同这一逻辑,即使这一逻辑背后暗藏着的是强大的男权话语。“在老管面前,我几乎是曲意逢迎,有那么一点讨好和谄媚的意思。不,就是讨好和谄媚。我用尽了一个女人的柔情和蜜意。在老管面前,我卑微,屈尊,下贱。我简直都不认识自己了。”④在一个优越的男人面前,翟小梨甘愿伏低做“小”,也甘愿领受这种姿态所带来的好处。女性当然可以弱小,就如同男性也同样拥有哭泣的权利一样。但是,正如同老管几次三番所暗示的那样,“你一点都不傻”,这样清醒而自知的“讨好、谄媚”,对于翟小梨这样的知识女性而言,到底是现实生活中难以为外人道的生存手段,还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对女性主体性的放弃? 翟小梨的命运,像极了林白在《北去来辞》中塑造的女主人公海红的命运,或许也代表着现实中许多知识女性的命运。她们都因一场婚姻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在全新的环境中,女性身上特有的韧性和耐性支撑着她们急速成长。她们的丈夫起初都是妻子的依靠,却多少因为“不识时务”的性格而逐渐脱离了时代,婚姻的齿轮因此开始松动。在经历了几段婚外情、几次逃跑的冲动之后,两位女主人公都选择了回到自己那平庸的丈夫身边。然而不同的是,《北去来辞》中的海红在一次次的试错与漂泊之后终于发现,原来那曾经被视为监牢与镣铐的一切,才是自己最眷恋、最依赖的地方。只有回到丈夫史道良的身边,她才能感到真正的安稳。二十年后,海红早已变成了另一个史道良,而当她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她才真正完成了与道良的和解,与她所憎恶的童年记忆和解,最终也完成了与现实的和解。而《他乡》中的翟小梨显然是不甘的,与其说她是在十八年后重新爱上了自己的丈夫章幼通,不如说,她是看清了自己心中所幻想与期待的那个理想爱人的崩塌,管淑人、郑大官人,不管是只言片语的柔情还是海誓山盟的承诺,不过都是一时虚幻的爱的憧憬。又一次,在现实面前,翟小梨领受了“芳村女人”的命运,“生活在向我使眼色。我不能视而不见”,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精神挣扎之后,翟小梨终于与命运握手言和,与其说这是她的成长与和解,不如说,这是现实女性的妥协与屈服。 二 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中塑造了两个女人,“好”女人甄宝珠和“坏”女人罗锦衣。这两个人物的命运,都与《他乡》中的翟小梨具有某种相似性,她们都是城市化进程中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农村女性,而她们各不相同的人生,恰好显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成长的不同面向。甄宝珠和罗锦衣这两个来自北舞渡的乡村少女,曾经共享了彼此高中毕业前的人生时光,两人同样怀抱着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去的愿望,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各自实现了愿望,最终历尽千帆,又在故乡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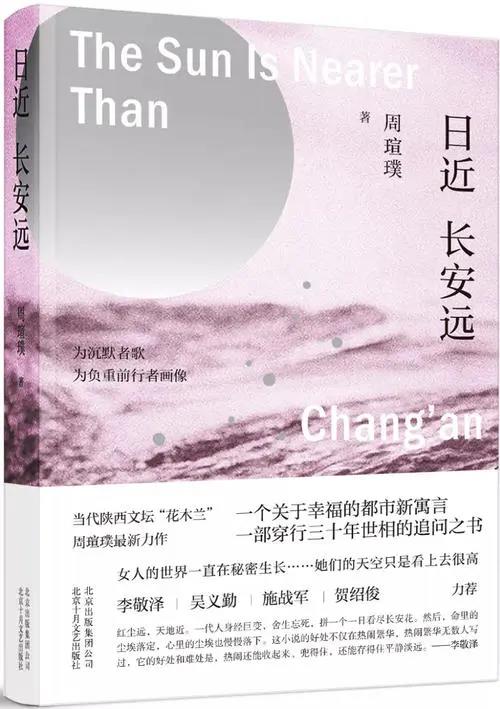 周瑄璞《日近长安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 少女时代两人曾偶遇一位老妇人,她无意间说出的话竟一语成谶:“人的命,天注定,不信不中。”命运之手在这两个出身相似的女性身上,显示出不同的力道。小说中的罗锦衣从小信念坚定、行事果敢,从二十多岁的“一身好肉皮儿”到中年迟暮,她一路身体开道,从北舞渡到西安,不仅一步步站稳了脚跟,甚至一度成了大权在握的副局长。作为一个过早经历了太多男人的、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女性,如果说罗锦衣还有什么欲望,或许就只剩下权力。然而恰如布尔迪厄的观点所称,“男性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是色情化的统治;女性的欲望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或者,严格来讲,是对统治的色情化的认可”⑤。罗锦衣无师自通般地深谙这一法则。她不惜一切代价,全身心地服膺于男权社会的种种法则,终于一步步登上了这套法则的权利顶端。从教育专干孟建设到省城的付良才处长,再到退了休还依然纠缠不清的程局长,罗锦衣不断地满足着一个个男人,内心非但没有挣扎,甚至是费尽心机地为自己争取一个献身的机会。终于,在她的权利顶峰时期,罗锦衣几乎完成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超越,她可以像当年那些男人要求她的那样,再去要求小健以及如他这样的年轻男人。但命运的可悲之处恰在这里,当年轻的小健们如同当年年轻的罗锦衣一样,热情而克制地奉献着自己时,罗锦衣反而失去了欲望,两性的、权利的欲望,在罗锦衣这样的女性个体生命中,最后都成了一场虚空。 在罗锦衣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显然投注了复杂的感情,正如后记中说的,“本是想批判这个人,把罗写成一个欲望强烈,同时又缺点心眼的人,不能让她有好的下场。但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一点被她吸引、感动了,她身上那种强劲生命力和强烈渴望,让人不得不佩服”⑥。小说中罗锦衣对权力与美好生活的渴望来源于自己童年的贫苦,以及强烈的摆脱过去的愿望,这简单而质朴的动机为罗锦衣此后的种种行为赋予了合理性。在生活中,她体贴亲友、心疼孩子,几乎成了自己和丈夫两家人的救世主,小说最后,经历了职场的大起大落之后,罗锦衣终于也过上了平静安稳的日子。某种程度上,通过剥夺罗锦衣作为一个女性的基本生育权,罗锦衣的“罪”也随之得以赦免——罗锦衣有“罪”吗?换言之,将身体当作资本的女性生存法则,究竟是不是存在问题?身体解放是中西百年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项基本成果与标志,身体的解放,意味着女性拥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它的最终指向应当是女性的精神解放。小说中的罗锦衣看似是身体解放运动的受益者,但于她而言,对自己身体的使用,即使看起来是那么自发自愿,最终指向的却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交易规则。这样的目的决定了,罗锦衣的欲望从来就不属于自己,而永远只能是一种被动的委身。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在这套由男性制定、男性主导的规则中,罗锦衣如鱼得水,她通过服从并熟练运用这套规则而成了游戏的赢家,甚至成为这一规则的制定者。如果说,女性身体解放的意义只是像罗锦衣这样,更便利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来满足男性,甚至以此向男性献媚,那么,身体解放对于女性自身而言,到底是难得的进步,还是另一种更为隐秘的负担? 小说中的甄宝珠是作为罗锦衣的另一种人生而出现的。与罗锦衣相比,甄宝珠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乡村女性。她与丈夫尹秋生摆地摊、开饭馆、收停车费,在日复一日琐碎而卑微的劳动中逐渐积累了财富,实现了在老家盖房子这个朴素的愿望。然而好景不长,尹秋生的发财梦破灭,连带着的是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不久后,尹秋生生病辞世,甄宝珠最终落得人财两空。小说中两个出身相似的女人,因为不同的人生选择,迎来了迥然不同的命运。甄宝珠作为女人的命运,始终牢牢系挂在自己丈夫尹秋生身上,她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全都由尹秋生做主,她的人生,向来都是她与尹秋生两个人的人生。丈夫辞世之后,甄宝珠的生命只好转而系挂到儿女身上。小说中,被寄予了世俗幸福的甄宝珠实际上一生都在随波逐流,从一种依附转向另一种依附,却从来没有成为她自己。 或许有人说,这就是所谓“现实”。在生活中那些晦暗而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罗锦衣与甄宝珠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在这本书的代后记中,作者与编辑的对话也传达了这一观点:“你想没想过底层的人怎么上来?比如一个乡镇的人想到省城去过体面的生活。这个愿望并不过分。可她没有任何资源,只有她的身体。”⑦所谓的底层“现实”真的就是这样吗?我不确定。但是,即便果真如此,我们依然需要追问,难道作家的职责就只是“真实”地描摹这样的现实吗?鲁迅先生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曾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⑧。一个作家,如果只能与“现实”共沉沦,那么他最多只能看到“藏在底下的罪恶”,但真正优秀的作家,应该具有穿透眼前“现实”和表面“真实”的能力,他必须比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得更高,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洞悉更深层的秘密,从而发现“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 三 与《日近长安远》中泥沙俱下的女性生存现实不同,蒋韵的小说始终致力于发现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完美女性形象。新作《你好,安娜》(花城出版社,2019)塑造了素心、三美、安娜以及子美、丽莎等多个女性形象。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几位女性彼此成就、同时又有意无意地相互伤害,在不无纠葛的人生道路中,完成了各自的精神成长与蜕变。  蒋韵《你好,安娜》 花城出版社,2019年 理解和谈论蒋韵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其实并不容易,小说中的安娜因为担心“死得难看”而拒绝手术,宁愿“病成一幅画”;素心为了夺回彭的笔记本,甘受陌生人的凌辱;安娜甚至因为笔记本的丢失,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现实逻辑中让人难以理解的情节,在蒋韵独特的美学体系中又似乎合情合理。这或许与作者的叙事策略有关,小说尽可能地模糊了价值判断,也搁置了伦理责难,转而追求一种至真至纯的美学境界。在蒋韵的美学体系中,灵魂的高贵圣洁与伴随着受难的自我救赎是其核心追求,这种精神追求超越了一切、笼罩着一切,当然也笼罩着她笔下的女性人物。 强烈的宗教意识也进一步加深了作品的美学追求。小说的上篇《天国的葡萄园》和下篇《玛娜》,其命名都源自《圣经》故事。在基督教的价值体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是男性的思想、肋骨和创造才能的衍生物。与此同时,女性生而具有“原罪”,夏娃以及她所代表的女性,她们引诱男性堕落、邪恶,因而世世代代受到惩罚。《圣经·新约》中对于女性的基本规训有如“女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中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驯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提摩太前书》),等等。基督教所崇拜的最重要的女性——圣母玛利亚——正是作为耶稣的母亲,作为一个牺牲者、救赎者而存在并具有意义的。在西方,自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女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他们认为,“尽管我们处于一个理性化的时代,早已抛弃了对它的字面上的信仰,但在感情上我们对它笃信如初。这一有关女性是人类苦难、知识和罪孽的根源的神话,直到今天还在左右着我们的性态度,因为它是西方男权制传统最重大的理论根据”⑨。在小说《你好,安娜》中,除了彭的姑姑、素心的“教母”,作者并未将其他主人公塑造成为基督教徒,但是,“圣母”般沉静的、甘愿付出与牺牲的,背负着不同的原罪而不断自我惩罚的特质,几乎体现在小说中每一个女性人物身上。 尤其是素心,小说写到她为了保护彭的笔记本而被陌生人侵犯,“那一夜,我把它,这封面上沾染了我初血的本子,藏在衣服里,紧紧抱在胸前,贴着我被弄脏的皮肤,挨着我原本如花蕾般清香的乳房。我抱着它,如同发疟疾一般,发着抖,一会儿被烈焰灼烧,一会儿沉入冰窟。它们俩,这高级的、羊皮面的本子,和我的身体,都脏了。如今,它们般配了。它们都让我厌恶和恨。可我也只有它了,我一无所有地抱着它,就像一头母狼抱着它刚刚出生的幼崽。对,就在这个耻辱的夜晚,我生了它”⑩。素心知道,笔记本是彭的至爱之物,因此,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对彭有着无限价值的笔记本面前,素心选择了献出自己,希望通过这种受难为自己所爱之人付出,或许更是希望借此在爱情的战争中打败安娜,与自己所爱之人完成某种“般配”。而正是这一隐秘的心理,让素心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因为不甘心将笔记本拱手让人,素心欺骗了安娜,以为笔记本已经遗失的安娜选择了死亡。安娜之死,让素心背上了无以复加的心灵之罪,她此后余生孑然一身、与朋友们断绝联系,用笔名“安娜”进行写作,无疑都是在试图改写自己的人生,在自我谴责、在偿还与救赎中努力洗清自己的罪恶。 安娜之死与素心之罪,在文学史的范畴中,几乎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想象。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早已发现,文学叙事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多被塑造为“天使”的化身,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提到的“永恒女性”,历经了从忏悔的妓女转变为天使般处女的过程。而完成这一形象的塑造,需要的是女性主动的自我放弃与牺牲:“无论是变成艺术表现的对象,还是一位圣人,她都需要面临对自我的放弃——放弃她个人的舒适、她个人的欲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是天使般的美貌女子最为重要的行为,也正是由于这些行为,这种牺牲,她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天国。因为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就不仅仅需要高贵的举止,甚至需要个人的死亡。” ⑪在《你好,安娜》中,素心和安娜这两位“天使般的美貌女子”,在面对自己所爱的男性以及那本写满了他与前任爱人的笔记本时,都选择了自我放弃与牺牲——安娜“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天国”,素心献出了少女的贞洁与在自责中度过的后半生。而作为女性,或者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她们的身体感受、精神痛楚甚至是生命本身,在这份想象中的爱情与虚幻的爱人面前,竟是如此微不足道。 对“完美女性”形象的反驳和打破,是女性主义写作的重要起点,更是女性发现自我、构建自我的基础。在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中,同样是写几位女性之间既珍贵又复杂的感情,同样是具有某种道德“原罪”的人物,女主人公尹小跳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女人,她有着真实的缺陷与不安,她的善良与邪恶、欲望与绝望、骄傲与卑微,都是每个个体生命时刻面对着的灵与肉的隐秘挣扎。而安娜、素心更像是从故事里,或者从画中走出来的女人,美则美矣,却最终只能是仅供观赏的艺术品。在小说中,安娜的姐姐丽莎几乎就是打碎这艺术品的顽童之手。年轻时的丽莎拥有惊人美貌,却因为舞蹈演员的梦想遭母亲反对而吞药自戕,此后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损害。之后在雁北山区插队,跟村里的羊倌结婚生子。知青返城大潮中,丽莎与丈夫离婚,带着孩子回到城市,在一家制药厂做工人。三年后工厂破产,丽莎只身来到北京,四处打工维持生计。最后,因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丽莎回到故乡,余生都在陪伴母亲的时光中度过。一个原本满怀着浪漫主义幻想的文艺青年,在接二连三的命运的重击下,一点点沉入现实的泥淖,丽莎一度也是沉沦的、自暴自弃的,但是,生存的需要让她从泥土中艰难地挣扎出来,岁月的洗礼,让丽莎成了与少女时期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她肥胖、衰老,甚至有些粗俗。但她的真实、勇敢、坚韧,最终让自己收获了丰饶而安稳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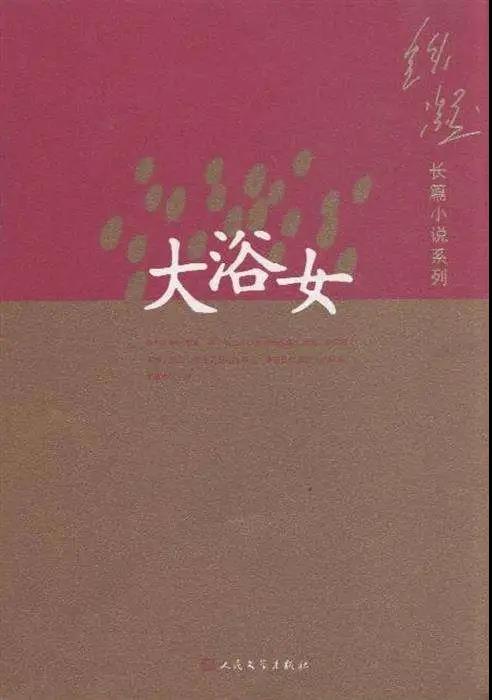 铁凝《大浴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在整个小说中,我更偏爱的不是唯美主义的安娜,也不是用余生去赎罪的素心,而是这个几乎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丽莎。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反而看到一种真实的、粗粝而强大的女性力量。小说中的丽莎也曾是“美”的追随者,但生活的磨砺让她逐渐从这场虚妄的梦中醒来,丽莎的人生仿佛彻底分裂为两个自我:一个朝向过去,是对未来、对人生充满了浪漫幻想的美好少女;另一个则生长在当下,艰难而不懈地应对生命中接踵而来的挫折,逐渐成为一个平凡甚至平庸的中年妇女。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与分裂中,丽莎的人生恰恰显示出可贵的韧性和力量。她时刻反抗那些外在于自己的想象和期待,她怨恨母亲对自己梦想的扼杀,憎恶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的家人,她的爱和恨都是如此简单明快、直截了当,她用一生完成了与母亲、与生活,更是与真实的、不完美的自我和解,而这或许才是生活的真相。 四 作为女性书写自我独特性的方式之一,“身体写作”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旗帜鲜明地主张“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她的自我”,“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最重要的路径即是发现和运用自己的身体,“她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⑫。女性主义者认为,文明社会的历史(history)是由男性书写的“his-story”(他的故事),历史上的女性被剥夺了书写的权利,因而文学与历史所记载呈现的都是男性话语,以及他们所构建的世界。正是基于对这一霸权的反驳,才有了简·奥斯汀的《劝导》,有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了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以及此后更多的女性主义书写。如果将女性写作,以及作为其中一种方式的身体写作放置在这样的历史通道中进行观察,其重要性与当时的迫切性不言自明,但与此同时,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正如其反对者所称,女性主义写作过于强调性别差异,以至于忽视了个体差异。“女性美学也具有严重的弱点。正如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尖锐指出的那样,女性美学强调女性生理经验的重要性非常危险地接近性别歧视的本质论。……女性文体或称为女性写作仅仅描述了妇女写作中的先锋派形式,许多女性主义者感到被这种规定的文体排斥在外。” ⑬女性主义与身体写作的主张,缘起于反对性别歧视、追求两性平等,而不是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敌视与拒绝,或是在反抗一种话语霸权的过程中滋长另一种话语霸权。将男性作家以及不同类型的女性写作排斥在外,从而走向狭隘激进的小路。 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一代女作家,其作品中对女性身体的探索,有意无意地暗合了身体写作的主张。此后,随着社会思潮的更迭,新一代女作家大多避开这一面向,而70后的盛可以,多年来却始终延续着这一写作路径。《北妹》中的乳房、《福地》中的子宫,都在不同层面上表达了盛可以对于女性身体秘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女性命运的思考。新作《息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中依旧包含这样的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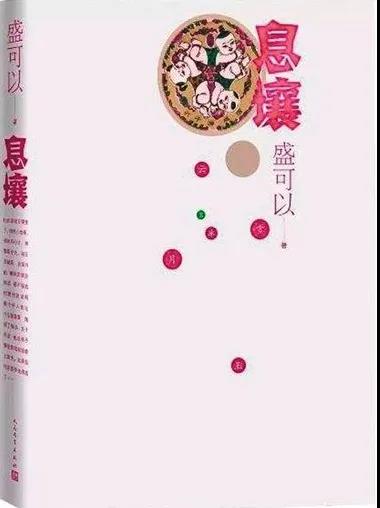 盛可以《息壤》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小说《息壤》通过初家几代女性不同的生命轨迹,尤其是面对生育问题时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折射出现实女性的种种宿命。母亲吴爱香生育六子,壮年丧偶,此后余生都在与欲望、与自己体内那个金属环状物作斗争;大姐初云挣扎一生,最终也没能离开无能的丈夫;初雪三十三岁被迫堕胎,随即丧失生育能力;初玉坚守了半生的信念瞬间瓦解,“从害怕生育到生育勇士”;初冰取环手术发生意外,不得已切除子宫;唯有初月,除了因生育而大出血的一次事故,基本实现了大多数女人所渴求的幸福。更晚一辈的初秀十六岁意外怀孕、意外流产……从急需生育到规避生育、从拒绝生育到渴望生育,初家几代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全方位地、全身心地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子宫的故事。 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小说中的初玉这个人物。盛可以的小说中通常有两种女性:一种是底层女性,她们在生活中备受磨折,却始终具有野性的、蓬勃的生命力;另一种是知识女性,她们对女性身份有充分自觉,甚至具有一定女权主义的反叛精神。小说《息壤》中,初云、初冰、初月是前一种女性的代表,而初雪与初玉则是后一种女性的代表。与底层女性将生育作为女性的天职,甚至希望用生育来圆满一场爱与婚姻的想法相反,妇产科医生初玉一度对此不屑一顾、深恶痛绝。在面对大姐四十岁又想要准备怀孕时,在面对侄女意外怀孕后的问题时,她的立场坚定决绝:“像你这种爱一个人就给他生娃 就给他做饭的旧思想要不得了。照你这么说,难道天下女人都应该学厨艺?如果爱就等于生娃,那不想生娃,不能生娃的女人就不懂爱,没资格爱吗? 这是什么逻辑!” ⑭“你自己才多大,十六岁就生孩子,这是旧社会。像条野母狗一样怀孕生子,哪里有做母亲的尊严?她自己什么也不懂,根本不懂生命,不懂生活,她根本没想过这些!这种事根本用不着考虑,没有什么选择,我建议赶紧去医院。” ⑮因为见过太多女性在生育过程中遭受的痛苦,初玉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始终怀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甚至清醒理智到有点不近人情的地步。 然而,真正耐人寻味的,并不是初玉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宣言,而是这些宣言、这种不容置疑在她此后生命中的一点点松动。初玉内心的松动也许是从与朱皓的感情出现危机时开始的。当朱皓对她表现出沉默并且不愿多做解释时,即使内心有万般疑虑,出于女性主义的倔强的自尊,初玉拒绝表达,“她看起来像西方女性一样独立坚强,她不能抛下这些优点做出一副柔弱的小鸟依人的样子胡搅蛮缠——虽然很多人一致认为女人在男人面前就应该弱小依赖,膨胀男人的自信与男根,不少人屡试不爽——她从未想过使用这种招数” ⑯。在这个时候,女性主义对于初玉来说,不仅不再是自我解放的利器,反而成了一道沉重的枷锁,它用另一种方式阻碍着初玉的言语、行动,更阻碍着她成为她自己。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初玉那曾经坚如磐石的信念开始动摇。 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暗示的,女性生而具有绵延生命与自我成长的能力。“息壤”一词语出《山海经》:“红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红水,不侍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鱼渊。”据郭璞《山海经注》的解释,“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盛可以以此隐喻女性“子宫携带者”这一天然的生理身份。小说最后,初玉成为母亲,她像所有的孕妇一样,平静安然地等待腹中生命的降临。曾经的女权主义者,最终领受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最基本的命运,生育对于她来说既是恩赐,也是惩罚,但她却甘愿在这痛苦的惩罚中享受甜蜜。我不知道作家是否希望借此人物表达对女性主义的反思,或是表现女性主义的现实困境。但在我看来,初玉的命运不但不预示着女性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女性主义的目的并不是否定任何一种女性生活的方式,而是让女性真正主导、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既有生育的权利,也有拒绝生育的权利,前提是她自己清醒自知并拥有最终的选择权。拒绝生育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目的,就像否定与拒绝另一种写作,并不应该是女性主义写作的目的一样。 小说中的初玉有一整套对生育的反思,但她最终没有陷入女性主义的偏见,而是自然地接受了自己作为母亲的命运。看起来,初玉几乎超越了狭隘的、独断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正如小说结尾所暗示的,“到她们这一代 子宫应该不再有什么负担”“那也讲不死火(说不准)⑰”,在漫长而遥不可期的未来,女性究竟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小说家无力给出答案,而当下的我们也并没有多少自信的资本。 结语 伍尔夫在谈论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写作时曾发现:“只需翻开那些已为人遗忘的旧时小说,听一听其中的语气,便知道作家正忙于应付批评。她时而挑衅,时而示弱,时而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时而又抗议,说她‘跟男人不相上下’。温顺、羞怯,还是怒气冲冲,如何对待批评,全要视她的性情而定。……这让我想到,所有这些女人写的小说,散落在伦敦的旧书店里,就像果园里的小苹果,长着疤痕。就是这心中的疤痕让它们腐朽。她为了迎合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⑱2019年,在翟小梨、甄宝珠、素心与初玉的时代,女性的现实处境早已不同于伍尔夫所指认的那个时刻,她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更不必再受到紧身衣的束缚。但是,在几位女作家所呈现出的文本世界中,男权中心的话语、宗教价值观的规训,甚至是极端的女性主义的立场,依旧不期然地浮现出来,覆盖、影响着作家自己的声音。伍尔夫所说的“心中的疤痕”,不仅改变了19世纪女作家的价值观和书写方式,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左右着今天女作家的说话方式、书写态度,成为某种沉默却无所不在的强权力量。  萧红(1911-1942) 代表作 《呼兰河传》《生死场》等 在父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文化价值体系中,女性的问题始终被认为是少数族群的话题。尽管几百年来,中西女性在不断地自我反抗过程中,收获了难能可贵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进步,但是,呼唤女性退出职场、回归家庭,对高知女性的污名化想象,以及倡导所谓“女德”的声音等,依旧不期然出现,甚至还能引起女性群体内部的共鸣。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在描写娘娘庙里的塑像时有一段精彩的发现:“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就是好欺负的,告诉人快来欺负她们吧!”“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的,神鬼齐一。怪不得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至是招打的缘由。”⑲身为女性,我不大确定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喊出那句著名的宣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塑造“女人”的不仅是女权主义者所声讨的男性以及男权意识,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正是女性自己。或许不妨想想,我们到底是萧红所说的挨打以致温顺的娘娘,还是根本就是那个打人的人、塑像的人?(行超,《文艺报》社) 【注释】 ①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2008。 ②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5页。 ③④付秀莹:《他乡》,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344、284页。 ⑤[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26页。 ⑥⑦周瑄璞:《日近长安远》,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347、346页。 ⑧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