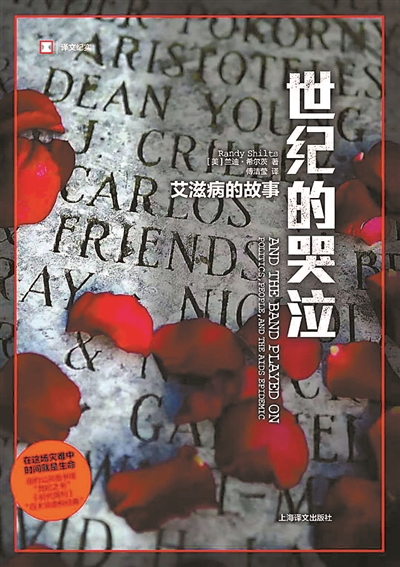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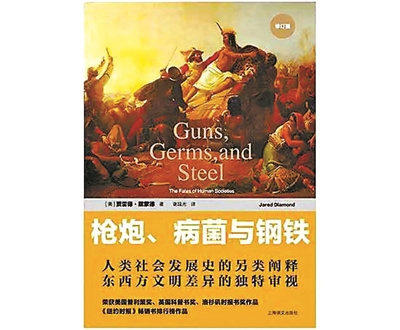 《世纪的哭泣》作者兰迪·希尔茨   受访人:步凯,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学院/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博士研究生在读。2013-2018年,供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疫情当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几本和疾病有关的书都受到了较高关注,《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血疫:埃博拉的故事》《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分析美国医疗体系的《美国病》。这几本都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纪实类作品,同时也是具体医疗研究领域内被认可的作品。 在没有那么确定病原体、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时候,人类社会对传染病如何反应?会出现哪些观点或情况?各方群体是怎么因为这种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传达自己声音的?《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情况,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在面对未知传染病时的记录。 今天我们的访谈将以《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作为起点,受访者步凯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当然,我们也希望将话题深入下去,不囿于某一具体的疾病。面对一种未知的传染病,及时的努力和长期的研究、科普、记录与书写同样必要。 全球范围内 疾病对个人健康 对社会的影响是相通的 北青报:《世纪的哭泣》英文原版1987年问世,三十多年之后中文版和中国读者见面,一些在疾控系统工作的专家对中文版出版表示非常惊喜。这种惊喜感源于什么呢?为什么这本书格外重要? 步凯:《世纪的哭泣》中文版能够出版,确实是一件非常让人惊喜的事。我记得得知上海译文社在做中译本的时候,我激动得连发两条朋友圈。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疾病对个人健康的影响、疾病对社会的影响是相通的,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只要受到艾滋病的影响,都有着相似的经历。所以,对于已经造成了数千万人感染和死亡的艾滋病来说,这本书既是对过去的反思、回顾,也是分享一种全人类共通的对艾滋病的经验。 目前,艾滋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了40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要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流行。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世界范围内仍然面临着药物可及性、商业逐利、边缘人群权益保护、艾滋病的歧视与污名化等很多问题、争议,其实是40年前争议的翻版,甚至如出一辙。即使书中的内容不能够告诉我们现在要如何做,至少能够告诉人们曾经经历的那些故事,并从中有所启示。 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1985年我国大陆地区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1989年云南省中缅边境吸毒人群局部流行,到1995年左右发生中原地区非法采供血人群流行。从目前的资料看,几十年来,我们开展了一场预防艾滋病扩散的工程。这些都是值得被记录的,因为从疾病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记录以及阐释分析并不是为了对某种策略、某个事件盖棺论定,而是为了从不同角度呈现出疾病、社会、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本书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记录写作这些历史事件的方法和样例。 与此同时,艾滋病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依然存在。艾滋病的流行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矛盾(比如歧视)、社会问题(比如边缘人群的权益)、公共政策争论(比如是否应该免费治疗、治疗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预防策略)、科研争议(比如对贺建奎事件)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很多问题其实是从艾滋病流行初期延续而来的,并不会因为有了治疗药物就割断了与过往的联系,所以这本书其实可以让我们追本溯源。 一本重要的疾病史作品 而且是当代史 北青报:《世纪的哭泣》是一本医学卫生纪实作品,能和读者分享一下您读后的感受吗? 步凯:《世纪的哭泣》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在内容和体量上都是如此。也许从图书出版业的角度来说,这样一本大厚书多少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程。近几年可能流行不厚但精装的小薄书,短平快,读者看着也不费力,码洋上也许还能有不错的业绩。因此翻译出版《世纪的哭泣》,出版方有文化和知识的担当。 内容上来看,《世纪的哭泣》记录了在艾滋病流行初期美国社会各方对这样一个新发致死性传染病的态度和观点,以及作者视角下的艾滋病流行过程。从病毒的角度来看,这种流行的过程可能非常简单,就是A传给BCD,BCD传给EFGH……但是任何疾病其实都有社会性,艾滋病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艾滋病早期的流行其实是一个病毒特征和社会应对两种因素互相建构的过程。 最早疾病暴发在男性同性恋群体之中,还大多是中产男性,后来发现还有其他几类人群高发,就是4个H开头的英文单词——同性恋、海地、海洛因和血友病。这些群体都是以往无法进入社会主流话语的群体,所以从这些群体中出现的可能广泛流行的致死性传染病所引起的社会冲突是巨大的。 这本书能够把读者带回到一种特定的情境,就是传染病暴发之初,在人们没有那么确定病原体、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时候,人类社会对传染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会出现哪些我们觉得“奇葩”的观点或情况?也能看到各方群体是怎么因为这种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传达自己声音的。 某种程度上,这和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很像,就是在面临没有被充分认识的传染病的时候,会有各种声音。人类社会在面对这种未知的时候,从历史上到现在,反应其实都是很类似的。 现在我们说艾滋病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个很好预防的疾病,病毒的传播效率并不高。但是当时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日常接触不会传播”,其实是在几十年和病毒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这是绕不过去的必经之路。我们有时候喜欢说科技的发展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这种疾病,也对,也不对。很多时候疾病与人的关系,只能在疾病真的对人类社会有所影响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 再一个感受就是,这其实是一本重要的疾病史作品,而且是当代史。传统意义上书写历史会和事发时间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本书不同。本书作者记录的是对当代事件的书写,从1981年艾滋病出现到1987年,这几年间美国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和反应过程。但作者的工作还不仅于此,这一作品其实促使人们发现并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的艾滋病迅速流行了,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应对措施滞后了,其中原因可能包括政府划拨的经费不足、公共卫生机构立场不够坚定、同性恋问题的敏感性、研究机构研究动力不足、同性恋群体把艾滋病作为政治筹码等等。尽管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但这些问题其实对现今社会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医学每一点进展或者弯路 背后都是被疾病纠缠折磨的众多病人 北青报:面对传染病,科普的工作很重要。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作品在科普方面的价值? 步凯:这样一本书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是一本纪实性作品,它同时也是一本科普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看作是一部公共卫生与医学史的学术作品。它从一个角度呈现了美国艾滋病流行早期的事件,它也告诉我们现在的预防策略,比如安全性行为、献血员检测、治疗药物的知识,是如何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并形成共识的。它积累了公共卫生领域应对新发传染病的经验,它记录了这一注定载入人类历史史册的重大传染病,最初与人打交道时的重要史实。 对很多研究艾滋病史的学者来说,这本书其实是艾滋病史研究的起点。2017年,美国历史学刊专门组织了一次艾滋病疾病史的研讨会,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本书。从这本书开始,艾滋病史领域出现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叫做“零号病人”。书中的陈述是这位名叫杜加斯的“零号病人”,是最早将艾滋病带入美国的,又因为他与多人发生过同性间的性行为,导致疫情在美国广泛传播。书中对“零号病人”着墨颇多,并建构了美国社会对于“零号病人”的刻板影响。 事实上也有一些历史研究是对这本书的讨论和批判,但这本书仍然可以被作为一种艾滋病的历史书写起点存在。 还要指出的是,这种记录其实是对过去的人和事件的怀念或者缅怀。即便我们现在取得了一些艾滋病预防控制的成绩,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走过的弯路。医学的每一点进展或者弯路,背后可能都是被疾病纠缠折磨的众多病人,甚至是大量的死亡。我们在看到医学技术发展进步的同时,应该对此怀有敬意。 北青报:传染病也引起了很多对特定人群污名化的争议。 步凯:是的。从科学上看,这其实是一种人为的分类手段,也可能算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建构,就是找到被感染群体的共性,把这种群体特征呈现出来。这是人们了解一种传染病的认知方式。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是控制传染病的三个核心要素。但在面对新发传染病时,这三个要素是倒推的,人们只能先看到被感染的人群,再倒推可能的传播途径和传染源。但是这种认知方式并不是要对某些群体污名化。 污名化是人类面临未知威胁时候的常用策略,梅毒流行时欧洲国家之间互相污名,所以梅毒有了很多别名,比如高卢病、法国病、那不勒斯病、西班牙病;艾滋病出现的时候有人提出远离同性恋群体……这种污名化是人类面对新发传染病的常态,但是这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有百害无一利。 很多时候 人类就是在茫然无知情况下 与传染病共存 北青报:尽管这本书的关注重点是艾滋病,从这本书当中读者能获得哪些关于传染病的基本常识? 步凯:首先,传染病依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健康威胁。人类历史上,传染病一直是造成人类死亡的最重要因素,也在很多时候影响了人类进程,有学者认为甚至决定了人类史的发展。《瘟疫与人》《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些作品其实都或多或少透露着这样的思想。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人类的疾病谱从传染病向慢性病转变了。确实,慢性病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了,但能不能真的称得上“转变”,也未可知。有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和慢性病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转变”。比如说肝炎有慢性肝炎,艾滋病也被认为是一种慢性传染病。 医学技术的发展能够控制传染病的病情发展,但是还不能治愈,也不能把病原清除,而且这种依靠药物维持的慢性传染病依然会给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人类通过科学研究发明抗生素,发明疫苗,发明药物,都是很晚近的事情,不到200年。但是很多细菌、病毒其实已经在自然界中存在了相当久远的时间,而且变化多端。所以不能说慢性病多了,传染病就不重要了,这种认识是很危险的。 全书的开篇其实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叙述的。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人的发现是在1981年,但是考虑到艾滋病发病之前存在着8年左右的潜伏期,最初的感染应该是在70年代。不过,艾滋病病毒的确切出现时间没有人说得清楚。有研究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有研究追溯得更早,比如意大利学者有研究,在19世纪的医学记录中,就发现过与艾滋病发病症状很相似的病案记录。这些都是推测,我们目前对艾滋病的真正起源依然没有确定。很多时候,人类就是在这种茫然无知的情况下与传染病共存的,埃博拉也是如此。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自然界还有那么多未知,人类对传染病的反应总是有些滞后的,这无可厚非。关键是我们在认识到一种新的传染病已经出现的时候,如何预判并确定所采取的政策。这种决策压力是很大的,人类历史上的教训和经验也很多。 进而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控制传染病来说,绝不仅仅是科学认知的问题,比如《世纪的哭泣》中就提到,有明显证据证明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的时候,要不要做血库筛查检测?在同性恋群体中广泛传播的时候,要不要强制关闭同性恋群体的活动场所?这些问题都不是仅靠科学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复杂社会情境、激烈矛盾冲突中 平衡各方利益做出选择 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处境 北青报:医学专业的研究者会从哪些标准来评价一本面向大众的医学读物呢? 步凯:《世纪的哭泣》一书重要的特征和成就,就在于作者尽其所能地搜集了各个群体的观点资料以及事件。总统、政府部门(疾控中心、食药监局)、商业机构(生物制品厂商、药厂、保险公司、雇主)、非政府组织(各种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协会、同性恋团体、异性恋群体、血友病群体)、研究机构等等,各个方面的观点与声音均呈现在了这样一本书中,这种呈现是全景式的,必然横跨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多重领域,这是很难得的。 因此,这样的作品告诉人们,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其实是在复杂的社会情境甚至是激励的矛盾冲突中,平衡了各方的利益而做出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处境。 北青报:本书作者是《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兰迪·希尔茨,从1983年开始着手调查,采访医疗界和同性恋社区获取各种资料,4年后完稿。在写作过程当中他接受了HIV检测,但坚决要求医生在写作完成后才能告知结果,并在交稿的时间点得知自己是HIV病毒携带者。 在您看来,书写医学、疾病的纪实作品,作者是否有医学背景是衡量作品的重要标准吗?就文本而言,有医学经验和没有医学经验的作品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步凯:我个人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体验。有过从医经历的作者可以写出很好的医学纪实作品,患者其实也可以写出好的医学纪实作品,中国俗话讲“久病成医”。虽然作者的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但是有着共同的对疾病的体验。 兰迪·希尔茨虽然并没有医学背景,但他是当时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群体的一员,这种体验对于呈现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国人避讳谈及疾病和死亡 健康观、疾病观、生死观教育比较缺乏 北青报:在写法上,面向大众的医学非虚构作品通常会有很多文学性的修饰。在您看来,在医疗卫生题材的非虚构写作上,文学性和事实性是否是矛盾的?会不会彼此伤害? 步凯:我个人认为并不矛盾。无论任何写作手法,都是帮助读者理解作品中的信息和内容。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理解纪实之实。 当然其中比较有争议的是所谓的隐喻问题。比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曾经明确反对将疾病问题隐喻化,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疾病的隐喻无处不在,为疾病赋予意义与价值的过程无所不在,桑塔格希望为疾病去复杂化的尝试违背了疾病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事实。也就是说,一些比喻手法能够帮助读者更形象地了解书中的叙事,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那仅仅是一种比喻。 北青报:我们也看到,《世纪的哭泣》一书在1993年被HBO改编成电影。您如何看待这类作品的改编? 步凯:这种改编恰恰说明了书中内容的丰富性,叙事中充满了矛盾冲突,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疾病预防的角度看,这样的改编大有裨益。 北青报:西方非虚构的写法,好像很喜欢将个体的故事上升为公共经验的叙事机制。您如何评价这样的做法,特别是在卫生医疗题材的作品里使用这种方法? 步凯:个体的叙事如果不上升到公共经验的叙事,就成日记了。而如果只陈述公共经验,则更像是社会调查或是公共卫生统计。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能提供某一个面向,所有人的个体化叙事拼接起来,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故事。于研究方法来讲,可能更像是个案研究;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其实是一种公众史学。医疗卫生题材作品,其实是一种亲历者叙事或者患者叙事。 我个人觉得《世纪的哭泣》是一本将个体叙事和公共经验结合得很好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并不是告诉我们作者的观点和体验,而是告诉我们艾滋病流行初期的那些故事,能够带读者回首来时路,重新经历艾滋病流行初期,人们的恐惧、彷徨、无助、争论、希望,这些其实是一种共享的公共体验。 北青报:能否再推荐几本关于医疗卫生的纪实作品? 步凯:《逼近的瘟疫》《违童之愿》。个人觉得国内的作品还是偏少,也许是国人比较避讳谈及疾病和死亡吧。健康观、疾病观、生死观的教育都比较缺乏,但是又受到了大量“唯科学主义”的教育,是医患矛盾突出的重要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