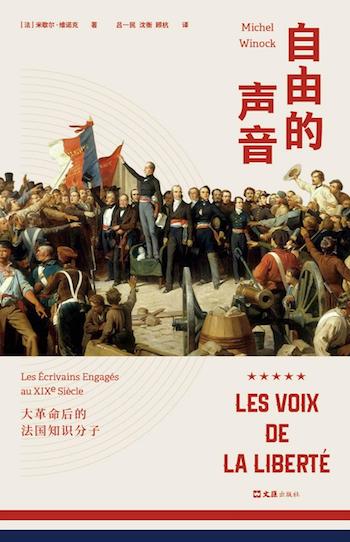 《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法]米歇尔·维诺克著,吕一民、沈衡、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776页,108.00元 虽然早已入秋,但是南方仍然酷热难熬;时而刮起的暴雨过后,在地面更激起蒸腾的热浪。前几天听说有年轻人在纸片上潦草地抄了一句诗,竟然是古罗马抒情诗人贺拉斯的:“照亮你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 赞美它带来的恩惠,与意外的时间。”据说是抄诗者出门前留下的,在珍惜和感恩之后,门外的夜与生命的无常都无法使他畏惧不前。此时此景,十六世纪的法国文豪蒙田早已说得很清楚:“谁学习了死亡,谁也学习了不被奴役。”说得很深刻,这就是诗歌与哲学对灾难宿命论的回答。这还令我想起最近看到一本书的书名,耶鲁大学教授马丁·黑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的《今生:为何死亡让我们自由》(This Life: Why Mortality Makes Us Free),这似乎也是对蒙田的话和那位青年抄诗人的一种诠释。 当面对一个城邦的生与死的时候,历史学家会思考更多的问题,那些问题也更令人动容。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Miletus)的居民无法忍受波斯人专制统治的奴役,为了自由而发动起义。公元前494年,起义被波斯人血腥镇压。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说,米利都城失陷之后大部分男子被屠杀,妇女儿童被掠卖为奴隶,神殿与圣堂被劫掠、焚毁。这个曾经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学派的城邦从此丧失了她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二等城邦。接着,希罗多德还谈了两件关于米利都人的事。 一件事是,当叙巴里斯人被克罗同人掳杀时,全体米利都人不分老幼都剃光了他们的头以表示哀悼;但是在米利都悲剧发生后,叙巴里斯人却没有任何表示。希罗多德因此认为叙巴里斯人没有对米利都人给予公正的回报。所谓“公正的回报”,我理解不仅仅是指一种同情和哀悼,同时更是基于正义的立场对反抗邪恶的声援,这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立场与原则。在米利都城邦陷落的那个晚上,如果来点穿越,或许你会期待看到整个希腊世界都翻飞着“今夜我们都是米利都人”的群发微信。一个为自由而抗争的城邦陷落了,除了雅典人以外,没有任何声援与同情,希罗多德为此而痛心。 另外一件事是,两年后在雅典上演了诗人普律尼科司创作的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全场观众无不失声痛哭。但意料不到的是,希罗多德接着说:“他们由于普律尼科司使他们想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灾祸而课了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出这出戏。”(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41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97年第六次印刷)为什么?观众被深深打动以致全场痛哭,不正是说明创作和演出都极为成功吗?希罗多德的叙述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古希腊悲剧的教授曼德尔松认为普律尼科司过早将历史改写成戏剧,米利都城陷落两年后雅典人还沉浸在对被屠杀同胞的哀思之中,尚无法以审美欣赏的心情去观看这幕悲剧,因此要罚款和禁演。其实,真正导致作者被罚的原因是过于煽情,古希腊人认为好的悲剧应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而不是简单的发泄悲情;真正好的戏剧应该使人思索人生与命运的问题,而不是使人哭个昏天黑地。据说在欧洲语言中,“戏剧”与“理论”这两个概念有着相同的词源,都有“全神贯注地观看”的意思,观看是为了思考。雅典人要告诉我们的是,城邦的理性与价值观才是最值得我们思考与认同的。 还是要回到米利都人的起义和反抗镇压。希罗多德在书中记载了伊奥尼亚人的将领狄奥尼修斯说的一番话:“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于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而且是逃亡的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决定关头了。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忍受困苦,你们当前是会尝到苦头的,但是你们却能战胜你们的敌人而取得自由。”(同上,406页)古代米利都人为什么被称为“爱奥尼亚的精华”?除了哲学以外,还有在城邦抗争中的政治学与伦理学,“自由的城邦”是其中不可剥夺的原则。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是自由的,城市也是自治的,就像那句著名的德国谚语所说的:“城市的空气使人变得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据说这句谚语来自当时的一项习惯法:只要农奴逃到城市里居住超过一百零一天,他就是自由的,即使他的主人也不能再抓他回去。马克思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还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都是曾经来自德国的声音,关于自由的声音。 从古代城邦到中世纪城市,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到十九世纪的法国知识界,关于自由的声音仍然值得我们聆听与思考。近日重读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原书名: Les Voix de la Liberté: Les Écrivains Engages au XIXe Siècle;吕一民、沈衡、 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对十九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关于自由的思想有了更深的体会。该书中译本第一版的书名是《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多年以前读过。此译本对该书的简介写得非常好:“血雨腥风的历史平台上,知识分子如何捍卫自由之原则?桎梏横行的年代里,怎样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以动荡不安的十九世纪的法国作为解读的背景,通过描述维克多·雨果、乔治·桑、马尔所克等活跃于各个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坚持不懈的斗争历程,彰显出法国专制体制下捍卫表达自由原则的艰难轨迹。风起云涌的斗争氛围、针锋相对的笔墨论战和悲欢离合的生活际遇交织成一幅既有生活质感又充满睿智思想内涵的历史画卷。”再看看书名近似的另一本关于美国的书——《自由的声音:影响美国的17个演讲(英汉对照)》(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该中译本的简介是:“收录了两百多年来美国人民不断追求自由的17篇以自由为主题的演讲,演讲者包括了帕特里克·亨利……在内的各界杰出人士。在演讲中,他们向美国民众乃至全世界人民陈述了自由的可贵和不断追求自由、维护自由的希望与决心。即使遇到再多的艰难险阻,自由的声音永远都会高高响起、永远悦耳嘹亮!”同样很简洁和通俗易懂。 目前这个新版本的译文看起来基本上与旧版译本相同,只是有个别字词作了修订。关于这个新版本的书名尤其是副标题与旧版本的差异,有评论者提出的解释是:“其标题可直译为‘自由的声音:十九世纪介入(公共生活)的文人。’……中译的副标题为‘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相当恰切的: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有关自由的论辩,都是在大革命遗产的影响之下、在拿破仑对自由十五年的压抑之后展开的。”我同意此解释中的观点,更认为旧译中的“大观”实在不好,但是与原文相比较,去掉了“介入”这个对该书内容而言很重要的概念,却是一种并非轻微的损失。说到底,还是对书名的翻译空间与自由度的理解与把握问题。 新版本的封底有一段话:“大革命之后,统治法国数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迎来的却是法国近现代最动荡不安的世纪。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轮番登场之际,知识分子选择发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脑。这些人中有明哲保身的赌徒贡斯当、戴着镣铐跳舞的基佐、预见民主弊端的托克维尔、身着男装的女作家乔治·桑、一度反对共和的‘法兰西灵魂’雨果……许多人白天还在为政府效力,晚上就被迫流亡他乡。……尽管政治立场相去甚远,但他们均共享对自由的热爱,而正是这份对自由的坚持使19世纪末的法国毫无疑问地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这也是对该书内容的精准而又有某种深度的简介。 正如该书作者在“导言”所讲,他要写的不是一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或思想史。“这本书选定的历史是由文人、作家与写作者……为了自由,与当局和其他为反动权威或乌托邦主义权威效劳的文人斗争的历史。这并不是一种文学史:本书的内容与政治相关,这亦说明某种选择始终会有争议。”(第7页)另一方面,该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我们希望能让这些男男女女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仅仅写一部他们的思想史。而且,结合他们的财产、生活方式、爱情、庸俗的抱负、虚荣、弱点,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可以理解。”(第9页)这当然是偏向感性的和重视历史语境的一种理解思想史的方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也会产生某种阅读上的障碍:关于自由这个主题的政治思想的发展逻辑、对立阵营的观点交锋、思想与历史事件关系的深度分析等等都被溶入到个人的行为、心思及其与他人的复杂关系等微观叙事中去,读者仿佛是要在一部嘈杂、喧闹的多声部乐曲之中辨认“自由的声音”的主旋律。读者似乎容易迷失于其中,或者望而生畏而徘徊在思想江流的岸边。其实,即便是生活在1805年至1859年的法国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也称当时的局势为迷宫,其中充满了微细的变故、幼稚的念头、不足称道的激情、各种个人观点和自相矛盾的方案,许多公众人物的一生都在其中耗尽(见其《回忆录》第一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似乎是为了消弭这种阅读困难,作者的“导言”提供了俯瞰全局的角度,也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作者的价值立场与对本书主旨的说明。 1789年大革命未能使自由获得制度性的基础(后来的所有大革命有哪些不是如此?),拿破仑虽然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但他实际上是以对自由的践踏而践踏了大革命,在这里维诺克说了一句足以让人心惊的话:“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第1页)但是,在波拿巴主义压制下的法国,自由派仍然幸存。他们没有首领、没有组织、一般说来不是专职政治家,他们只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同上)当然,也有某些文人选择颂扬服从权力、教条,维护传统秩序。复辟之后的波旁王朝开始的时候在宪政的约束下还允许人民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没有几年就变得向专制倒退。自由派文人与王朝斗争的焦点是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最终导致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在艺术表现上有我们所熟悉的德拉克洛瓦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还有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的高达五十二米的七月革命青铜纪念柱顶端的“自由之神”雕像,一个展翅奔驰的自由神。在接下来的七月王朝时期,自由的呼声仍然存在,但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呼吁,围绕着自由而发生的思想论争变得更为复杂和激烈。1848年的革命带来短暂的自由与平等的幻觉,新的帝国开始的时候曾试图以人民的名义埋葬自由,但是迫于民族运动的变化而转向自由化。然而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其后的巴黎公社使形势变得在自由与专制之间进退两难。直到1870年代末,重新建立的共和制才使自由得以相对稳定地确立。1885年6月1日雨果的葬礼是“自由的声音”最后压轴的一幕,也是本书的终点,象征着自由的实现。如果我们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察眼光看待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政治趋势,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现一种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而发生的反复对立,也就是贵族的复辟与自由原则顽强抗争,而所有动荡的核心都是离不开自由与专制的抉择。 在本书中最受关注的浪漫主义作家是维克多·雨果,分别有四章谈论他。第六章题为“维克多·雨果:向左转的浪漫主义”,细致地分梳了君主主义和基督教的浪漫主义与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的区别,细致地分析了雨果的浪漫主义从右向左转的过程。我们或许最感兴趣的是思考艺术自由是如何与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同步的,然后目睹着“维克多·雨果成为共和派”(第二十三章),感受着“《悲惨世界》的冲击”(第二十七章),最后全书的结尾同样还是“维克多·雨果:至高荣誉”。雨果的一生不仅因其文学创作而不朽,同时也因为他永远致力于自由的事业而不朽。今天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悲惨世界》《九三年》的时候,我想着的首先是政治与自由,其次才是文学。作者在“导言”中说,“雨果似乎可以安息:这位年迈的斗士已被奉为‘共和国之父’”(第7页)。值得思考的是:雨果手中没有枪,只有笔;雨果毕生为自由而呐喊——我想维诺克要强调的是,只能从共和国与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的意义上理解究竟何谓“共和国之父”。 “这些男人、女人、作家、哲学家、政论作者或讽刺歌谣作者曾三次直奔广场,参与事件并试图对事件施加影响。由此,划分情节的三大交叉口依次是‘百日’(1815年)、‘二月革命’(1848)和‘凶年’(1870-1971)。19世纪的这三大政治危机也是非同寻常的集体时刻。作家、文人、艺术家在这期间,在议会的讲坛或市政厅这些巴黎长久的革命圣殿的窗台上起了积极和中心作用。”(第9页)这是多么形象和多么激动人心的描述!作者在“导言”最后说,十九世纪的思想成果——他指的是关于自由的思想——是我们不可剥夺的遗产;而全书的结尾是:“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19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然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尤其要感激它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691页)我时常感到,无论文学还是政治思想,十九世纪这份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今天,我们没有资格嘲笑崇高,更不会在如何实现自由的问题上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