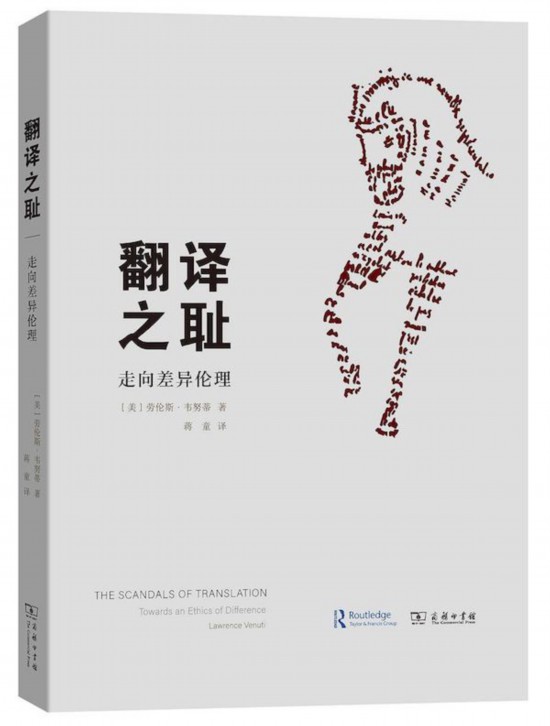 《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美]劳伦斯•韦努蒂著,蒋童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出版,322页,38.00元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蒋童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是一部具有鲜明特征的专著: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中带有鲜明的情感特征和强烈的学术发展诉求,在这里可以引用“译者前言”中的一段话——“在韦努蒂为翻译及翻译学科鸣不平的声音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韦努蒂在诚恳地期许一个没有翻译之耻、没有翻译悲情的乌托邦,他渴望一种可以让翻译稳定栖身的价值,一种属于翻译与译者自身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翻译文化。”这也的确是我在阅读该书的时候强烈感受到的。 该书“引言”开头就说“翻译的诸多耻辱(scandals)与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相关”,并认为这种耻辱出现在翻译所处的学术研究、批评以及争论的边缘境遇之中,非常明确地点出了该书的核心论题。接着就是,“翻译常被鄙视为一种写作形式(a form of writing),遭到版权法的排挤,为学术界所贬低,被出版社、政府以及宗教组织所盘剥利用。笔者认为,翻译之所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部分原因是翻译敢于质疑当前的主流文化价值并挑战学术机构的权威”。(1页)因此,“本著作的目的首先是通过质询与使其边缘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揭示翻译之耻”。(2页)在这里,揭露、质疑、控诉和雪耻的色彩已经鲜明呈现,而其起点则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翻译研究本身。它的关键问题是把自己局限在语言学的领域中,而忽视了与社会价值观、当代文化和人文学科的关系,远离了当代发展中的重要论争。但是顺带要说的是,我想这可能是到90年代末为止作者所看的研究状况,而且这种状况可能更多发生在关于翻译的纯理论探讨领域中,在今天的翻译史研究中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景观。举个例子。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翻译史研究》(自2011年始,每年出版一辑)体现出研究角度的跨学科、问题意识的多元化与扎根历史阐释场域的穿透力等学术品格,早已远远超出了翻译实践与策略、文本描述与对比解读等语言学的层面。从翻译的文本到出版机构,从译本的接受、传播到产生社会影响的历史情境,所有一切与翻译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无一不是翻译研究所必须关注的对象。关键的研究发展趋势是,在传统的文本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深切地关注词语的翻译与传播在历史实践中的复杂性,以敏锐的问题意识使翻译研究与各种门类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当然,韦努蒂的这部著作和他之前的《译者隐身:一部翻译史》也都作出了同样的努力与贡献,这也正是他对于当时的翻译研究现状提出尖锐批评的基础。 既然核心论题是“翻译之耻”,作者从文本的著者身份、版权、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学、哲学、畅销书和全球化等多维角度揭示和论述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的遭遇和承受的耻辱,目的是要重新确立翻译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重新评估翻译行为对于社会文化乃至历史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生产与法律地位这双重层面上重新建立翻译的权威性价值与意义。第四章“文化身份的形成”在全书中的重要性比较突出,所讨论的是异域文本通过翻译而产生的归化、铭刻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如何操控翻译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环节,以及如何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影响。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以古典学学者琼斯、日本小说的美国译者福勒和《圣经》的翻译等具体个案研究作为例证,说明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形成的复杂关系,最后提出和阐释了化同伦理和差异伦理这两种翻译伦理。其中,韦努蒂关于翻译与种族主义以及与本土政治权威的关系的两段论述特别值得重视。关于前者,他说翻译有可能对特定种族、民族以及群体表现出尊重或蔑视,从而塑造出不同的刻板形象;既可能显示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也可以显示出对种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爱国主义的仇恨。关于后者。他认为“翻译塑造身份的力量,总能让文化与政治机构陷入困局,原因就在于它能揭露出所处社会权威的不稳固性。再现真相不是建基于权威文本与机构管理的一致价值观,而是建基于使文本得以翻译、出版以及接受的偶然性”。(106—107页)顺带要说的是,在这章的开头有一个阅读理解上的疑问:“这一痕迹铭刻的过程,操控着翻译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这首先体现在选译哪些异域文本,因而总不选译与本土利益相适应的那些异域文本与文学。”(105页)从意思上看 “总不选译与本土利益相适应的……”似乎有误,而下文说“这样以来,异域文学通常被重写,以符合本土文学中当下的风格与主题”也能说明这一点。作为研究翻译的著作,我感到该译本还是时有阅读并不那么顺畅的地方。 第七章“畅销书”研究的主题是翻译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所处的困难处境,指出畅销的译著更需要迎合当下本土的文化期待,才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进而更重要的是,出版商会期待畅销书译作能加强读者已经持有的价值观念,因此“在生产译作的本土文化与该译作要再现的异域文化这两者间,畅销译著更有助于揭示的是前者而非后者的状况。”(193页)在本章中韦努蒂以很长的篇幅论述了意大利著名作家乔万尼•瓜雷斯基(Giovanni Guareschi,1908—1968)的作品被翻译到美国并成为畅销书的过程,以阐明时代意识形态和大众通俗审美观对翻译和畅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瓜雷斯基的小说以幽默与讽刺为最大特色,在20世纪50年代十分流行。惭愧的是我的孤陋寡闻,在此之前竟然不知道这位意大利作家。韦努蒂对他和其作品及译作的概括性介绍是:“他的小说笔锋犀利,富于讽刺。他最受欢迎的几部作品的主要人物唐•卡米罗(Don Camillo),是意大利北部村庄的一位牧师,卡米罗和共产主义镇长佩彭内(Peppone)时有意识形态的饶有趣味的小冲突,并总能获胜。瓜雷斯基的作品翻译于冷战时期(即西方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阵营间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他的全球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反复出现的反共产主义主题。然而,译本为了争取畅销书的地位,不得不迎合当时的多种文化期待,迎合不同本土读者群,迎合不同于在意大利本土获得的期待。”(197页)接着,他详细论述了瓜雷斯基的作品在美国的翻译引进与畅销过程,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瓜雷斯基译作在美国的畅销与当时蔓延全国的“红色恐慌”有最紧密的联系,“无疑,瓜雷斯基的反共立场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198页)但是美国读者更愿意接受的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卡米罗“对共产主义镇长幽默胜利空想式的安慰”,他让读者关注的是他的勇气、力量、信念和幽默,给读者带来的是胜利的信心;而对于他的对手,有一位评论员这样写道:“在他的书中,共产党人尽管咆哮,但并非恶魔。在大话的背后,他们仍然是充满激情的意大利人,其初恋情人仍是教堂。”另一位评论者说,“村里的共产主义镇长,卡米罗最主要的对手,也一样是人,与似乎随处可见的恶魔般的政治漫画人物大相径庭。”(205页)也有评论认为卡米罗与共产主义镇长之间的争论带有“意大利人性情中歌剧性的本质”,意识形态的锋利边缘总是显得模糊不清。(201页)这两个人的形象与处在红色恐慌中的美国大众对他们的接受颇有意思,似乎可以说明一种相对柔化的“文化冷战”在大众文化中的真实存在。 二、在米卡罗这个形象中体现的个人主义精神、男性理想形象和父权家庭模式非常迎合当时美国阅读大众的文化期待,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学想象。“美国读者将瓜雷斯基看作是一个证实了在男性异性恋的权力与反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关联的作家。”(202页)不仅是他的作品,而且是他本人的形象所传达给美国读者的印象。“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结构,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性别、阶级与国家认同,这是美国接受瓜雷斯基作品的特点。”(204页)这是翻译的接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论题,韦努蒂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三、在瓜雷斯基作品的翻译、传播过程中,出版商、编辑、译者所起的作用极其重要,这一过程极为复杂。令我有点惊讶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的删减、章节的调整与重组、词语翻译中的选择(有意选择美式英语和口语表达法等)、语言风格的改变乃至对原著中的意大利风土事物的改变,其变化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合大众的阅读与审美趣味,它们的畅销就是这种改造的成功证明。就这样,读者甚至感觉不到读的是译作而不是原作,“该译本最非凡的是,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将美国本土行为规范及意识形态铭刻进译作的过程是无形的。……美国读者阅读翻译时,要在译作中找到英语的方言,找到他们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以及任何想象中能够用于自身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228页)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洋为中用”,或者说是翻译生产中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在最后一章,韦努蒂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的观点:在“全球化”时代中,应该坚持文化的差异性发展,应该坚持在翻译中突出异域文本的异质性,“只有这些差异才能提供把异域文化的异质性铭刻进翻译的方式”。(293页)这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该书副标题的最后回应:走出“翻译之耻”的道路就是“走向差异伦理”。 从韦努蒂的“翻译之耻”很自然会想到我们自己的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虽然角度和状况都有不同,但也有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词语的翻译看到“归化”中的翻译与政治。 简•莫里斯《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方军、吕静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中译本有一个译名的问题值得注意。这本《世界》从珠峰开始谈起,“珠穆朗玛峰1953年”,问题是,在英文原著中真的是写着Chomo Lungma(这一写法出自C.K. Howard-Bury,转引自林超)而不是Everest吗?1855年,在英国人主持下的印度测量局对该峰进行测量,并以该局前任局长埃佛勒斯(S.G.Everest)的姓氏命名此峰。1952年,中国政府将埃佛勒斯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关于这段命名公案,我国地理学家林超先生在1958年撰写的《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一文(收入《林超地理学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予以详细论述。文中提到,“到现在,除了苏联和另外几个国家已改用珠穆朗玛外,其他各国,还大都沿用挨佛勒斯的名称”。因此在1953年的莫里斯似乎不可能用Chomo Lungma这一写法。手头没有原书,只好存疑。如果原文是Everest,中译本译为“珠穆朗玛峰”,我认为有问题。在翻译的忠实原则面前,要解决“政治正确”的问题并不困难,在这里加个译注就可以解决。其实,我在1999年进入珠峰地区的时候,在《通行证》上“攀登山峰”栏里注明的仍是Everest,当时我想可能这是因为这类证件主要是发给外国登山者的缘故。这是对的。 在翻译外国著作中的“技术处理”,在删除、改变名称等手法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忠实还原。如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特别注明该译本所依据的巴黎版“恢复了检查机关删节以前的原稿原貌,并经作者亲自校正”。1975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全三册)的中文版“出版说明”一方面花了不少篇幅批判该书的反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另一方面则说没有对原书正文做任何“技术处理”。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翻译政治中的“差异伦理”的具体例证,可以说明差异性与归化原则的合理并存? 韦努蒂在他的著作中似乎没有论述的一个问题是原著在异域的被禁与在他国的翻译出版,这是20世纪的翻译与政治关系中的重要论题。由于原著作者所在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常常会出现原著在自己的国家被禁而其译本却在其他国家出版的情况。例如,《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全书于1973年至1975年在法国出版,在中国大陆,群众出版社于1982年12月以“内部发行”名义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译者在出版前言中申明“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同时也说明译文没有作任何删减。但在苏联国内,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出版禁令要到了1989年才解除。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苏联的。尼•伊•布哈林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冤而死,苏共到1988年正式为布哈林平反、恢复党籍,但是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就已经有了一批关于布哈林的译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肯•科茨《布哈林案件》(王德树译,人民出版社, 1981年)、斯蒂芬•F. 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 (1888-1938)》(徐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苏绍智等主编《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在翻译的耻辱与悲情的背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自豪与光荣。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