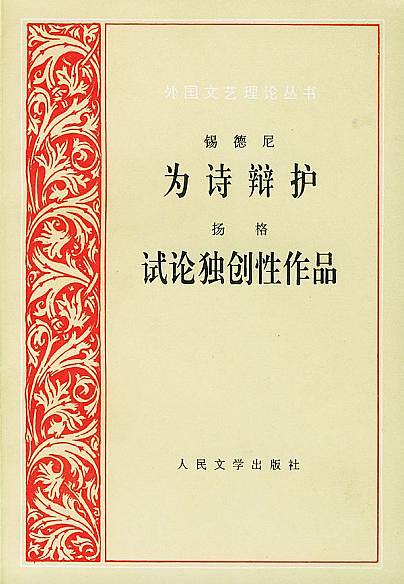 学养型批评是我提出的一个词。两年前杨正润教授邀我给他主编的《现代传记研究》写篇文章,因为我不专门研究传记,拖了年余方成稿,而且仍旧是在我研究的18世纪英国文学范围里做了篇文章,评介塞缪尔·约翰逊的《诗人评传》,题目是《略谈学养型评传——以约翰逊〈诗人评传〉为例》。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提到学养型批评这一概念,而约翰逊则是最典型的学养型批评代表。 其实,回顾英美文学批评,我们不难看到,从启蒙时期一直到19世纪初,主要的文人和学者都是学养型批评家。以英国为例,上起16世纪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的《诗辩》,下至T.S.艾略特对玄学诗人的评价,都不属于二战后兴起的,由各种理论引领的批评。学养型批评家大多是饱学之士,他们评论和发表看法从不拘于某一种理论,他们满腹经纶,熟知从古代到19世纪的文学、哲学和美学理论。而且在评论文学作品时,更是非常善于阐释和细读文本。此外,他们的英文非常漂亮,读他们的文章和著作是件很享受的事情。比如约翰逊把琼生(Ben Jonson)誉为技巧型诗人(poet of art),把他的戏剧比成仔细安排规划的精致的花园,而把莎士比亚誉为天然的诗人(poet of nature),他的戏剧被比做大森林。不像琼生的小花园,森林里有杂草,但有参天的松柏和各样植物,是那么宏大、丰富。这种概括性的评价十分准确、到位和生动,从此传为了对莎翁的定位性质的评论。不仅如此,“精致的花园”和“参天的森林”这样的比喻之后又与伯克(Edmund Burke)和沙夫茨伯里(3rd Earl of Shaftsbury)等18世纪文人提出的“秀美”(the beautiful)和壮美(the sublime)对应,形成一种传世至今的美学概念。又比如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上发表了18篇评论弥尔顿《失乐园》的文章,还有一组12篇谈“想象愉悦”(The Pleasures of Imagination)的文艺理论文章,基本都是出自他自己的学识和体会。一直到阿诺德 (Matthew Arnold)、卡莱尔(Thomas Carlyle)、罗斯金(John Ruskin)、梯利亚德(E. M. W. Tillyard) 等等学者都是约翰逊的传人。最近我被梁工教授要求给他的期刊写篇文章,我最后写了弥尔顿的《失乐园》,其中选用了燕卜孙(William Empson)评《失乐园》的话,是一句典型的学养批评的评论。他说:“我认为它(《失乐园》)可怕但很了不起……就像卡夫卡的小说……而且我不大相信任何一位批评家能宣称自己没有类似的感觉。”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作为文学作品《失乐园》非常了不起,弥尔顿是伟大的,创作了那样丰富、宏大的史诗。但如果对照形而上的上帝(即神学的上帝)来细读,这部史诗就可怕了,因为大量的文本例子展示了《失乐园》的上帝可能被读作与弥尔顿写上帝的意图相反的一个不仁慈、玩弄权术、把天使和人类通通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坏上帝。这类评论很好看、有趣,常常是真知灼见,当然学养型批评也很个性化,甚至情绪化,就像艾略特全面否定弥尔顿和《失乐园》虽然有他自己的诗学理论,但因他不喜欢宏大叙事就打偏了靶子。这是学养批评的弱点。 然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在文学、文化理论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西方掀起了以理论为框架的批评热潮。一时间学养批评显得没了水平,大家都一哄而上地比谁的理论高,实际上文本已退居相对不重要的地位。当然,多元化理论批评激活了许多已经沉埋很久的文学文本,让我们更深刻、更透彻地认识了作家和作品。比如18世纪书信体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被喜爱菲尔丁、狄更斯小说的文学主流意见贬低后,几乎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多元文化和文学批评激活了他的小说,揭示了书信体小说重在心理刻画的特点和它独特的“写至即刻”(writing-to-the-moment)的戏剧性,并从叙事理论、文体特色、女性主义、复调与狂欢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评论和分析他的作品,最终给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伊恩·沃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将他与菲尔丁并列为英国现代小说的两大源头。在我国也有理论做得很不错的学者,比如做叙事理论的申丹教授。因此理论批评的功劳也是不应磨灭的。而且理论框架批评也是以学养为基础的,现当代西方绝大多数走理论批评路子的学者学养都极佳,而且不会像学养批评那样个人化和情绪化。 但这种批评带来的问题也很多。比如美国贝伊勒大学知名教授大卫·杰弗里在讨论圣经的文学阐释时曾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一些后现代理论名流们介入圣经文学批评的目的。比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同别人合著的《结构分析和圣经阐释:解读文集》(Structural Analysis and Biblical Exegesis:Interpretational Essays),其主要兴趣是用圣经阐释来宣传结构主义理论消解边界的功能,是用圣经文本来试刀,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和万能。这是许多理论批评家共有的问题,他们的兴趣和目的不在文本。然而,因为那些西方理论家们都有扎实的文本基础和细读本领,所以一般都没有丢掉文本来空谈。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韦恩·布斯(Wayne Booth)谈小说修辞,伊恩·沃特谈小说兴起,都是通过细读多部小说来提出他们的理论的。布斯对奥斯丁(Jane Austen)《艾玛》的分析就特别精彩,让学界信服地认识到那是奥斯丁最好的一部小说。 另外,理论框架批评看似高深,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比细读文本得出自己的见解来得容易。首先有了理论词语壮胆,文学批评反而变得有据可依。一位美国教授曾对我说,理论框架引领文学批评后,反而使批评容易了。先前的学养批评让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不敢介入,因为读的书不够,学养没有,也没法说出有见识的意见。而有了理论做框架后,不用读百卷书,只要会摆弄某些理论词语,尽管还没吃透理论,他们也觉得自己有了侃侃而谈的底气。因此在我国,特别是研究生论文中,大部分是找几个文本例子与某一个理论对号入座,用理论去贴文本,最后成为两张皮论文,还往往吹牛说发展了某某理论。此外,语言好也是学界对批评的要求,但理论批评的行文一般谈不上优美,读起来很累。在美国我的老师就批评过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英文不够好。而不赶时髦,较保守的教授就会当场尖锐地批评用理论套文本的做法。比如我为了自己即将到来的答辩去见习了一个美国博士生答辩,他用巴赫金理论分析美国早期政论性散文,但由于理论和文本结合生硬,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老教授当场就批评他的论文“愚蠢”。 到了中国,理论套文本的问题就更多了,当然这主要出现在研究生中,比如用弗洛伊德理论读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的戏剧,用女性神学读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简爱》等等。结果是理论没弄透彻,文本分析又做不到层层深入,因此往往就很肤浅地先按一知半解的理论把人物或表现分类,再像投信箱那样把作品的人物或描述按类别梳理一遍,过程中理论和文本阐述还不断重复,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也有少数胡说八道的,比如用弗洛伊德读乔叟的《特罗伊斯和克丽西德》(Troilus and Criseyde),居然读出克丽西德和给她和特洛伊斯拉关系的叔叔还有一腿!我认为不以文本为主,用一个理论套文本的做法实际上把文本扁平化了,也把作家简单化了。比如托尔斯泰,他远远不是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可以把控的,而莱辛(Doris Lessing)在北大做讲座之后与学生交流时就公开生气地否认她是女性主义者,因为她的作品比一个主义丰富得多。 这种理论批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大词语套简单内容,比如当前最时髦的空间理论。这两年弗洛伊德冷清了,很多论文都争着用空间叙事理论。我不反对,也觉得空间叙事很有意思。但它就是一种非时间顺序的叙述,比如意识流叙述,或不按照线性时间叙述来讲故事,故意让人物一会在街上,一会在火车上,把看到的和想到的都写出来,甚至心里的想法和脑子里的活动都可以算作空间叙事。虽然我们可以并欢迎使用这个理论来深化文学批评,加深叙事理论的哲理,但走火入魔也不必要,更不可绕进去就不能自拔并唯它独尊。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不搞理论,因此说的多半都是班门弄斧,为了强调我的观点就有可能简单化地评论一个复杂得多的理论。当然,除了上述两类批评,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批评,比如诗学批评、考据批评、评介性批评等等。这些类型的论文实际也都很有认识价值。刘建军教授前不久在上海交大的一次论坛上谈到他正在做的拜占庭文学翻译与文学史书写的社科项目,我觉得就特别好。 我国近年来强调论文必须具备理论框架的后果是置教师于尴尬和无奈的处境。教师们(我也在内)经常被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学生养成吹牛的风气,长期下去就破坏了我们的学风,而且会培养出一批学术不扎实、做人不老实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接班人。我要再次声明,我今天提出学养型批评,并不是要否定理论驾驭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我的目的仍然是强调好好读书,因为学养是一切批评方式的基础、起点和落点。不论是理论书还是文学作品,我们都要细读,读懂、读透,并且读书时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不要像目前大多数的博士论文那样,做哪个理论就俯首帖耳;做哪个作家,尤其是获外国的文学奖项,如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这类奖项的作家,就把他们吹捧上天,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思辨和看法。这样的文学批评,不论是强调文本,还是强调理论,都不是好的批评,也不会有真正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