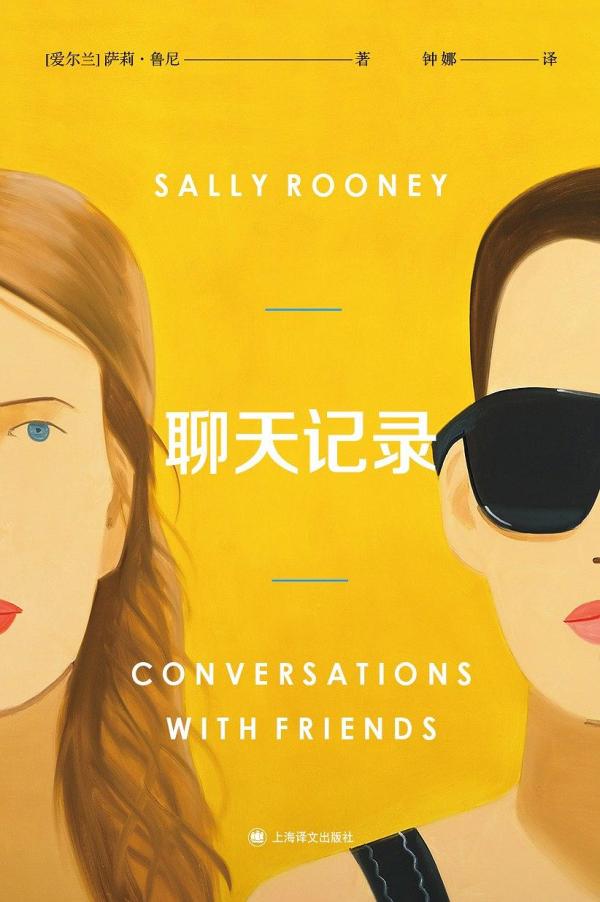 《聊天记录》 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首部作品《聊天记录》,回溯了大学时弗朗西丝在2012年夏天到同年圣诞期间的经历。这年她21岁,业余时间在都柏林酒吧表演说唱诗。故事开始时,她和表演搭档兼前女友博比以接受采访为契机,结识了记者梅丽莎和她的演员丈夫尼克。闲聊时,弗朗西丝注意到了梅丽莎的装备: “梅丽莎用的是一款大块头的专业相机,她在专用相机包里装了很多种镜头。” 只有对镜头迷恋的人,才会第一眼看到它,并精准地对它进行描述。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萨莉的许多句子都具备这种荷兰静物油画的质感,所有出现在笔下的事物都不是出于偶然,它们统统经过了作者严苛的筛选、漫长的雕琢,最后以朴素到让人误以为简单的方式,把观者和被观看者的欲望、虚荣、哀伤、绝望全部呈现在你眼前。 《纽约客》撰稿人劳伦·科林斯在书评中引用了《聊天记录》里一个转瞬即过的短句,说一个聚会上“全是音乐和戴长项链的人”,劳伦·科林斯说,“这句话会让你再也不想戴长项链了”。事实上,读完整本书后,你会发现书里遍地都是这样的看似漫不经心、不着痕迹的小句子,它们就像小小的轻量级拳击手,那么精瘦,出拳却如此有力,被击中时你才意识到它的体格已在作者纯熟的思考中锻炼到极致,没有一丝多余的骨肉。 《聊天记录》里,弗朗西丝不停地照镜子。和博比谈恋爱了,照镜子;登台表演前,照镜子;和母亲发生争执了,照镜子;孤独自弃时,照镜子。镜子,这面明亮的小小的湖泊,映照出弗朗西丝的容貌(“我的脸平淡无奇,但我超级瘦,瘦得看起来很有性格”),也映照出她的内心(“我在镜前凝视了一会儿自己,感觉心中的厌恶越来越强烈”)。 凝视自己的目的不是、或不仅仅是对自我的迷恋,而是对自我在他人眼中的外在形象进行把握。正是这种态度赋予了《聊天记录》数字时代的质感。写下这篇文章的这天,推特正在庆祝它的十三岁生日。过去十数年里推特、脸书、QQ空间、微信朋友圈合力孕育出一种潜意识,一种强烈的“被注视感”。当梅丽莎发来成片时,弗朗西丝在手机上将高清照片放大到只看得见像素颗粒。然后她把照片缩回原样,打量自己的脸,“假装自己是头一回看见它的陌生网民”。对社交媒体原住民来说,“陌生网民”是她潜意识的一部分,一面背景墙,或一种白色噪音。 弗朗西丝自己何尝没有构成别人的背景墙和白色噪音。初识梅丽莎的演员丈夫尼克时,她已经在网上搜到过他没穿衬衫的照片,他“正从游泳池里上来,或在一档老早就被取消掉的电视节目上冲澡”。当她开始和尼克偷情后,博比曾发给她尼克幼年时作为“神童”参加的电视节目。于是,在网络和摄像技术的帮助下,一件在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弗朗西丝看见了十岁的尼克,他“很瘦,像竹节虫”,困扰时东张西望,仿佛在寻找他的父母。 信息就是力量。就像橙色封面所暗示的,《聊天记录》记录了年轻人对成人世界发起的一次进攻。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羡慕成年人的成就、豪宅、甚至婚姻,而成年人则咬牙切齿地捍卫自己用青春和纯真换来的一切。弗朗西丝可以借互联网之力窥探尼克的隐私,从而洞察他的脆弱;梅丽莎可以采用更传统的方式,挑拨弗朗西丝和博比之间的感情。掌握更多秘密的人拥有主动权,无论是去伤害还是去爱。和尼克分手后,弗朗西丝在网上看到一枚他和梅丽莎早年的视频,为朋友们表演一首英文老歌: “我从没听过尼克唱歌,他的声音很美。梅丽莎的也是。他们表演的方式也很好,尼克假装不情愿,梅丽莎试图挽留他。这很适合他们。他们显然是为朋友们排练的。从这个视频,任谁都能看出他们有多爱彼此。如果我之前看过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心想,大概什么都不会发生。大概我会料想到结果。” 萨利·鲁尼喜欢用“can”这个词。不完全统计,她在首部小说《聊天记录》里用了356次“could”(“can”的过去式),在第二部小说《正常人》里用了253次。“Can”经常伴随一个戏剧性瞬间出现,和see、hear、feel搭配,表示一种能力。她的人物从不仅仅看见、听见、感觉到,他们还感知到自己感知的过程。他们和世界似乎总是隔着一层玻璃,他们站在明亮的房间里往外看去:看见世界的同时,也看见自我在玻璃上的倒影。 比如弗朗西丝在剧院第一次看见尼克表演时: “我能看出他在试图跟我对视,如果我回应了他会给我一个类似抱歉的神情。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强烈了,像裸露灯泡的亮光,我没法去想。观众继续鼓掌,我能感觉到尼克注视着我们下台。” 去掉“能”字,情节不会发生改变,但整个瞬间的戏剧重心会悄悄发生位移,部分回流到表演者尼克身上。“能”字为弗朗西丝灼烧的自我意识添了把火,硬生生造出一束光(“裸露灯泡的亮光”),打在自己身上。哪怕真正站在舞台上的是尼克,在弗朗西丝的叙述流中,观众似乎在为她鼓掌。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萨莉·鲁尼,那么你要小心。她的问题、她的态度、她的视角,一旦吸收就很难忘掉。你无法撤销她对你施加的影响。某种程度上,鲁尼的小说像今天的手机,前置镜头像素紧追后置镜头。然而不同的是,她的小说世界里,前置镜头没有美颜功能。你如果想要凝视自己,就必须接受自己的全部——自卑、虚荣、丑陋,甚至平庸。 比如,意识到自己爱上尼克后,弗朗西丝开始对他和他妻子梅丽莎逐渐修复的感情产生嫉妒。她在交友软件上结识了一个男人,并和他发生了一夜情。那周末见尼克时,她将此事向尼克坦白,后来两人发生了争执。 “你他妈结婚了,我说。 没错,谢谢你。简直帮大忙了。我猜就因为我结婚了你就可以想怎么对我就怎么对我。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试图扮演受害者。 我没有,他说。但我认为如果你对自己足够诚实,你就会为我是已婚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你可以随便发泄,而我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我不习惯被他这样攻击,觉得有点害怕。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独立到别人的观点与我无关。现在我害怕尼克是对的:我将自己从批评中孤立出来,于是我可以随便胡来,并且保持我的正义感。” 在另一个场合,弗朗西丝得知自己被诊断出子宫内膜异位症,在回家的车上她以一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目光审视着自我: “我有种感觉:我生命中某样东西结束了,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或者是个普通人。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会充满平庸的生理上的疼痛,这没什么特别的。痛苦并不会让我特别,假装不痛苦也不会让我特别。谈论它,甚至书写它也不会将它变成某种有用的东西。什么也不会。我感谢母亲送我到车站,然后走下了车。” 全球化的今天,经济把所有故事捆绑在一起。1995年至2007年,爱尔兰经济腾飞,增长率四倍于欧洲平均值。而2008年起,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爱尔兰经济直转急下,2010年财政赤字高达国家经济总量32%,不得不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援助申请, 到2011年底,爱尔兰失业率更是高达15%,这是小说中弗朗西丝的故事开始的半年前。 资本飓风带来的破坏在生活中留下可见的遗迹,在其中长大的年轻人开始拥抱马克思主义。鲁尼的第二本小说《正常人》里,还是高中生的主人公玛丽安娜和康奈尔曾在开发完成后无人居住的“鬼宅”约会。康奈尔来自工人阶级,母亲是清洁工。他高中时便阅读马克思所著《共产党宣言》,后来考入名校圣三一学院,和“造成金融危机”的人的儿子们做同学。鲁尼精准地描绘了某一类年轻人:他们出身并不显赫,通过教育完成社会升级,然而收入没有跟上脚步。于是他们的道德感和他们的欲望之间裂出一道鸿沟,它越来越宽。 一方面,弗朗西丝迷恋于尼克的高档衣着:隐隐带点褶皱质地的棉麻衬衫、领尖带纽扣的牛津衬衫、蓝色丝绸衬里的灰色羊绒大衣;一方面,在《聊天记录》的开篇,她便宣称自己不想找工作,即使找,她的工资也不会高于全球人均年收入(16,100美元)。理想很崇高,但根基很脆弱。弗拉尼丝的生活费由她父亲支付,她免费借住在亲戚在市中心的房子里,她在文学经纪公司的实习工资几乎为零。聪明如她,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不食人间烟火毫无知觉。她不止一次描述过母亲的手: “她的手又大又蜡黄,一点都不像我的。它们充满了我缺少的实际性,我的手在它里头像件需要修的东西。” “她跟我道别时我抓着她的手,她的掌面又大又暖,就像某样能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 这是轻盈在渴慕沉重。然而轻盈不知道该如何获得重量——《聊天记录》的后半段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当常年酗酒的父亲打来电话、神秘失踪后,当尼克回到梅丽莎身边,当博比靠近又远离,当疾病来袭,当银行账户只剩下取不出的零头,当大雨倾盆——“在危机关头,我们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决定,我们究竟要爱谁”——弗朗西丝不得不消灭拦在自己和世界之间的那道玻璃,踩着玻璃渣出去。 有意思的是,鲁尼最后选择让无神论者的弗朗西丝在教堂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二次洗礼。“曾有人做出了我此刻坐着的长椅,”弗朗西丝心想。她的目光抚摸过面前每一样东西: “曾有人打磨木头,给它上清漆。曾有人把它搬进教堂。曾有人给地板铺砖,有人安装窗户。每一块砖都是人的手垒好的,每一扇门上安装的铰链,每一条外面的路,每一盏路灯的灯泡,都需要人的劳作。” 通过教育习得的知识统统归零,世界是新的,需要重估一切的价值。至此,一个人再次成为她自己。  萨莉·鲁尼 Jonny Davies 摄 今年4月,为了能见萨莉一面,我来到纽约SOHO区的McNally Jackson书店。进门是两个卖明信片的旋转支架,右边收银台前整齐码着她的第二本小说《正常人》。灯光明亮,有咖啡的香味。我来早了,活动还没开始,工作人员在调试投影仪,座谈区尽头拉上隔离带,后面站满了等待的人。 究竟是谁在读萨莉·鲁尼?美国Interview网站采访了多家纽约书店。曼哈顿书店Book Culture说是曼哈顿的中上层阶级;西村书店Book Book说是NYU的学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布鲁克林地标书店Greenlight说是“白人女性,尤其是年轻白人女性。当然了,很多不同的人也在买——中年男人,带着小孩的妈妈们。” 我看向四周:穿撞色衬衣、大圆眼镜的棕发女孩,利落短发间露出黑色耳钉的金发女人,穿皮夹克、戴很多配饰的中年夫妇。很多人穿皮夹克,很多人穿牛仔服,我也穿着牛仔服。McNally Jackson是弗朗西丝和博比也会喜欢的书店,我们是可能出现在《聊天记录》里的人,甚至可能是萨莉会带着讽刺口吻描摹的人——那些“戴长项链”的家伙们。在访谈里,她不止一次表达过对作家这个职业的怀疑。作家不应被明星化,她说,真正值得采访的是护士,是巴士司机。然而我怀疑,如果此时天花板掉下来,可能会砸中五个市场营销、三个编辑、十个想当作家的人,却不太可能有护士和司机。 萨莉会为此烦恼吗?获得她警惕和怀疑的人群的追捧,会不会是一种讽刺?阅读她过去几年接受的采访时,她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小小的任务,那就是诚实地书写我知道的那种生活。” 我们需要《聊天记录》,因为和弗朗西丝一样,戴长项链的人们需要先看清自己的模样,再进行改变。萨莉当然也会继续发生蜕变,毕竟生活最伟大,而萨莉正年轻。 (本文作者系《聊天记录》中文版译者)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