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雍措散文集《凹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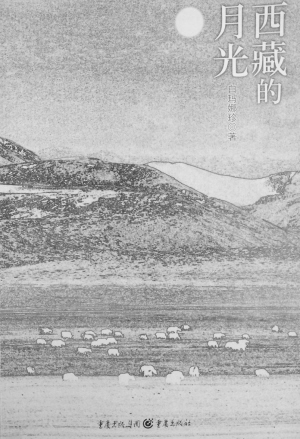 白玛娜珍散文集《西藏的月光》  梅卓散文集《走马安多》 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出走”和“回归”故乡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常态,与之相随的是对故乡的守望与追忆成为故乡书写的常见情感模式。当代藏族女性散文中的故乡书写亦是如此。由不同文化场域穿梭带来的文明思考,在她们笔下表现为原乡依恋与现实文明的冲突。 在当代都市文明裹挟下,当代藏族女性散文以横向视野展示从日常生活到建筑、服饰,从宗教历史到教育制度;再以纵深视野,从历史到当下,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书写了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故乡。她们笔下的故乡既是生养作者的地理版图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带有浓厚民族文化记忆的精神原乡。其故乡叙事既有个体小我的人性张扬,也有浓郁的区域意识,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是其故乡书写的基石与内核。 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栖居地 当代文学作品中,对藏区书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将藏区作为世外桃源、人间天堂。在当代藏族女性散文中,藏区故乡是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栖居之地。 四川康定女作家雍措笔下的“凹村”是超越区域局限的世外桃源。这从她文章的题目便可看出,如《风过凹村》《又是一年樱桃红》《植被茂盛的地方》《梦里的雪》《让灵魂去放牧蓝天》《多雨的季节》《静处,想起一阵风》《思念像风中的叶子》等。这些富有诗意的意象填满作者关于凹村的童年记忆。 意象之美是雍措故乡书写特点之一。美好的乡村邻里关系,温馨的亲情以及清新的风、漫山遍野的郁郁葱葱……这些充满人性关怀的意向,塑造了当代版的“湘西世界”。作者详细回忆了童年记忆中的美好快乐,再现鲁迅“朝花夕拾”式的情景。 美好的人伦情怀是故乡记忆的情感触发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故乡记忆的轴心。邻里乡亲的和睦关系与家人的温情,显示出深厚的人情美、人性美,让故乡呈现出传统古典美学意蕴。雍措的笔下塑造了传统意义上伟岸、坚强的父亲形象与善良温柔的母亲形象,以此重回古典意义的“家”,重回传统叙事。 对父辈感情的叙述是历史建构的主要内容。在《凹村》中,父母一代美丽的爱情承载了雍措对故乡的美好记忆;在《遗像里的爱情》中,父母坚贞的爱情没有因生命消逝而褪色;在《漫过岁月的绿·指头花》中,阿爷与阿奶饱受包办婚姻之痛,当阿爷遇上了自己的真爱时,他抛弃了阿奶与刚出生的女儿,阿奶没有被破裂的婚姻摧毁,反而以顽强的生命力挺了过来。 当代社会在走向现代文明、逐步西化的过程中,传统节日渐渐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雍措的“凹村”叙事复活了人们对往昔岁月的美好记忆。她在《听年》中,从“腊月”“年花花”“抢头水”“过年谣”“年疙瘩”“新衣裳”等细节中,追忆了村子里乡邻们聚拢一起杀猪迎新年、穿上漂亮新衣过年的传统习俗,再现了新年热闹快活的场景。 千年农耕文明积淀了静态乡村文明的审美意识,从陶渊明到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书写了静谧隽永的乡村之美。雍措对故乡的叙述,在时间隧道中以诗意化的方式回望故乡,其价值意义在于:笔下的故乡在立足区域的同时又超越了区域,具有古老中国乡村文明的共性。 浪漫的历史与身份建构 从雍措家长里短的温馨日常生活叙事,到白玛娜珍穿透岁月的历史叙事,故乡书写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直抵藏文化核心。白玛娜珍的故乡书写因此而增添了历史沧桑之感。 浪漫历史建构是白玛娜珍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在她的笔下,红尘诱惑是魔鬼,会让爱情“生锈”。在她的《拉萨的活路》中,拉萨红尘不仅腐蚀了僧人洛桑与曲珍的美好爱情,也摧毁了洛桑。在《爱是一双出发的箭》中,一对相爱的恋人为相守而抛弃一切,漫长的出走岁月,人生信仰安抚了他们流浪的身心,也让爱情常驻。在《唯一》中,痴情的男子出家为僧,整整20年独自一人居住天葬台的山脚下,只为在亡妻消逝的地方守候。在白玛娜珍笔下,美好的爱情如陈酿的老酒日益芬芳浓烈。 与白玛娜珍浪漫的叙事不同,梅卓的叙事带着历史的厚重沧桑,穿透时光而来。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中定位自我身份,是梅卓故乡书写的主要特征。她的《走马安多》以游历的方式呈现了安多丰富的人文地理风貌,从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文化自信。 梅卓的故乡书写是典型的学者型散文,注重文化地理内涵的开掘。梅卓游览九寨沟时,面对美丽山水,她关注的是山水之外的文化、历史。她的文笔穿梭于不同时空——介绍藏族聚居区历史中曾有的卡约文化、古格王朝等多种文化,为藏区神性色彩另添传奇。与此同时,她也关注普通藏民的日常生活,从婚丧嫁娶到日常穿着服饰,挖掘深藏于其间的历史传承。如《在青海·在茫拉河上游》里,她写了兰本加一家从早到晚的日常劳作,制作奶茶、挤牛奶、清点羊群、剪羊毛、迎客宰羊、制作酥油、炒青稞……这些日常劳作显示出温馨的亲情、友情,写出了普通藏民的苦与乐。 梅卓的故乡书写,挖掘了藏区文脉传承,细数当下藏民的日常生活点滴,在纵横之间,构建具有厚重历史的当代美丽藏乡。梅卓的自我身份认同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中得以建立。如同光影相随,因为对于历史的沉迷以及因当代生态环境破坏而对现代文明的抵制,也构成梅卓自我身份认同与现代性认同之间的一道鸿沟。 对传统与生态文明的坚守 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化,城市文明的欲望膨胀吞噬着乡村文明的淳朴静穆,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和对乡村文明的守望成为当代文学的主题之一。藏区因为地理位置关系,生态与人文环境得以相对较好地保存,因而藏区成为当代人心中的理想桃园。 白玛娜珍经常穿梭于现代都市文明与偏远的藏区牧场之间,她将现代与传统的博弈放置在较为开阔的空间与深远的历史。一是对当代文明的思考。在《百灵鸟,我们的爱……》中,她指出整个地球生态恶化导致拉萨的日益燥热,作为世界最后一方净土的拉萨尚且如此,人们已无处可逃。二是对历史文化的梳理考量。在《等待荒冢开花,等待你》中,她将当代生态环境破坏的缘由追溯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长达几个世纪的残酷争战中。在人力弱小时期,适度的开垦是人类生存的有效方式之一,但当人力逐渐变得强大,开垦已经造成生态环境失衡。三是对不同形态文明的再比较。历史上,农耕文明几乎一直以来都优越于游牧文明,但到了当代,面对失衡的地球环境,对游牧文明的缅怀成为生态保护者的情感共性。面对现实问题,白玛娜珍用一幅美丽的画卷,表达了对传统的缅怀,显示出作家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情感倾斜。 当下,地球生态环境遭到极度破坏。与之相对,藏族聚居区悠远的游牧文明成为工业文明的有力参照物,并因为那洁净的空气、淳朴的民风和虔诚的信仰而取得优势性地位,那里成为当代人“梦想的天堂”和“永恒的精神家园”。梁炯·朗萨在散文集《恢弘千年茶马古道》中,为世人提供一份遥远的历史想象,讲述了千年茶马古道上一个个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她用天路、香巴拉乡城和圣地稻城亚丁等建构了一个让当代人向往的家园。 藏区故乡书写与当代乡土文学中的故乡书写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以莫言、刘震云等为代表,他们笔下的故乡主要是被批判、质疑的所在。在工业文明袭击下,内地乡村文明总体呈式微状态,故乡留不住人们离开的脚步。与之相对,虽然藏族聚居区不可避免地会承受来自现代文明的震荡,但是藏区故乡因为原生态的高山、湖泊、草场和浓烈的情怀,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 当代藏族女性散文表现出的现代性认同,受生态破坏和人文伦理道德失衡等因素影响,几乎集体性地选择了对历史的回望。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就民族地区而言,处理好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建设区域文明、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藏族女性作家或唯美浪漫、或蕴含厚重历史内涵的故乡记忆,与当代文坛“撕裂”的故乡记忆形成了故乡书写的参差对照,体现了当代中国多层次、多结构的文化生态。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