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故事”是九久读书人公众号新开辟的栏目,与读者分享不止于书的作家日常,每周二更新。本栏目包含九久原创、媒体优质好文分享,主题不限,望借文引路,伴读者进入更为开阔的作品世界。 本期“作家故事”介绍的是王安忆。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在《我所认识的王安忆》中说:“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形象来描述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条斜行线,斜率在过程中会有变化,向上却是不变。”今天,我们就来阅读张新颖教授的这篇文章。 王安忆和我是两代人。1993年,她送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中篇小说集《神圣祭坛》。我读简短到一页半的自序,忽然强烈自省,年纪轻,对有些问题特别敏感,而对另外一些问题则可能完全没有体会。这本书里的作品,之前我都读过,特别喜欢《神圣祭坛》和《叔叔的故事》。这样的作品与写作者“深处最哀痛最要害的经验”相连,满溢着迫切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对我这一类沉溺于“精神生活”的青年人——后来才明白,那个年纪,除了所谓的“精神生活”,也没有别的了——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我说的特别敏感之处。而当王安忆将注意力放到别人的经验上,特别是写市民世俗生活,她和她的个人经验拉开了距离,她的作品也就和我拉开了距离。这个集子里最早的一篇为《逐鹿中街》。1989年我写过一篇短评,题目叫《庸常的算计和爱情追逐》,虽然是称道作品“不同于常人眼光的洞见和不动声色的表述”,但事实上,并不懂这世俗人生中的庄严。譬如我用的词“庸常”“算计”“追逐”,和王安忆在这篇自序里的说法对比一下,就知道差异多么分明:“《逐鹿中街》,我要表达市民的人生理想和为之付出的奋勇战斗,以及在此战斗中的变态”——1989年我大学毕业,22岁,还待在校园里继续学业和“精神生活”,能看出“变态”,却不能从“庸常的算计”里看出“人生理想”和“奋勇战斗”,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吧。  2018年王安忆连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蒋迪雯 摄) 1996年,《长恨歌》出版,把她作品中不断增扩的世俗人生故事推上了一个高点。她赠书,在我名字后面加上“小友”两个字。这两个字本身也写得小小的——这个称呼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两代人。我之所以要强调“代”的不同,是因为从我个人经验来说,我们最直接的学习对象就是上一代,他们是“文革”后的新生群体。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下一代成长到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走在前面的人,他们就成了我们年轻的老师。 2004年春季,王安忆调入复旦中文系,我们成了同事。她最初讲课,是在我开的一门课程里,共讲了3次。我印象至深,她每次走上讲台,都先从包里拿出厚厚一叠卡片,然后按已经理好的顺序一张张讲下来。卡片,当它们出现在王安忆手里时,我一愣。 我也曾做过卡片,但早已不再做,连图书馆的卡片箱都废除了,连中文系资料室几十年累积的卡片资料也都不知道扔到了哪里。此时,不期然地,卡片现身于她的课堂。卡片之外,我想她还有详细的备课笔记。几年之后她能完整地整理出讲稿,就是靠笔记和卡片的详细。这3次课的讲稿分别是《小说的异质性》《经验性写作》和《虚构》,与此后五六年间的讲稿汇集起来,就是《小说课堂》这本书。在这本书之前,她还有一部小说讲稿叫《心灵世界》,再版时又叫《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在复旦站了一个学期讲台,讲的就是这个。手握粉笔,遇到关键处,转身写黑板。王安忆喜欢讲课,但不喜欢演讲——喜欢作为一个专业教师讲课,不喜欢被当成一个名作家演讲——这之间的差别,其实比通常以为的还要大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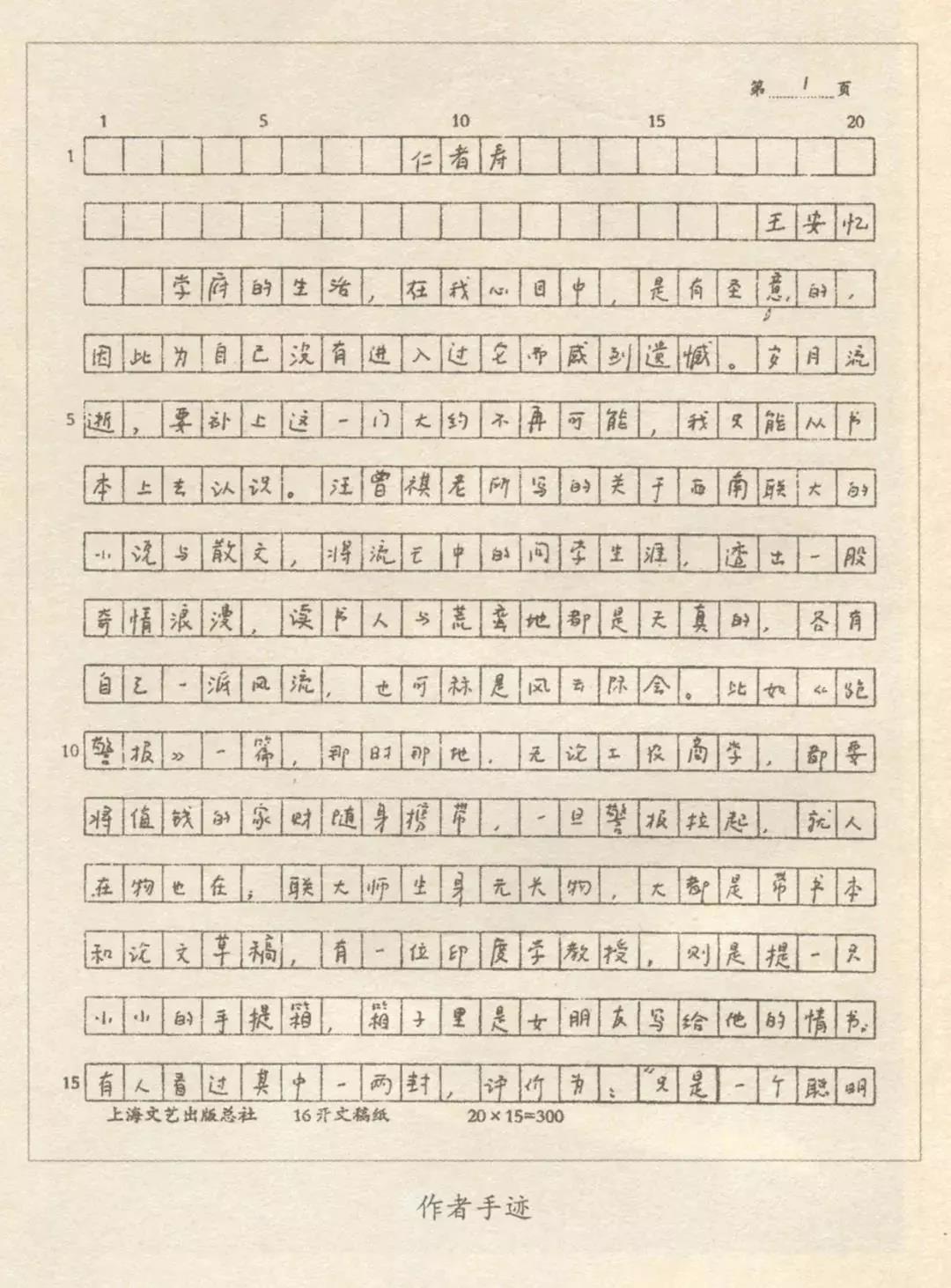 2004年12月下旬到2005年1月末,我和王安忆做了次漫长的对话,陈婧录音,后来整理出版为《谈话录》。我们谈了六次,五次是在王安忆定西路的家,一次在复旦文科楼的教研室。次与次之间有意隔几天到一个星期,做点准备。每次围绕一个主题,约两三个小时。谈完后,由于一直忙乱,等到2006年秋冬,我到芝加哥大学,每周除了讲两门课没有别的事,才在空闲中整理出来。书的出版,更迟至2008年。我一向就不是一个好的对话者,因为话太少。不过这一次,我本来就定下来自己少说,请王安忆多说,我多听。王安忆几次提议我应该多说一些,似乎效果不大。从头到尾整个谈话过程,我都感到愉快而轻松,因为重量多由王安忆承担。她认真、诚恳、坦率,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没有一点花哨。我接触过的作家能说会道的不少,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不得不培养出针对不同对象与场合的说话策略和技巧,时间久了,运用自如,连他们自己都忘了这些策略和技巧的存在,而这些东西已悄然内置成他们说话的语法。我与王安忆谈话所感受到的愉快,来自于没有策略和技巧的语言,我无须去分辨其中什么样的成分占比多少。这份对当年“小友”的信任,也是她对自己的忠实。没有互相的信任,没有对自己的忠实,还谈什么话。 转瞬间,王安忆到复旦已经12年。她的创作更是几近40年——有了这样的时间长度,文学道路这类的说法,才更有意义吧。与王安忆一同上路的人,不算少,走到今天还在走的人,已经不多。长路本身,就是考验。  王安忆部分作品 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形象来描述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条斜行线,斜率在过程中会有变化,向上却是不变。这条斜行线的起点并不太高,可是它一直往上走,日月年岁推移,它所到达的点不觉间就越来越高。而所有当时的高点都只是它经过的点,它不迷恋这暂时的高点,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斜率往上走。它会走到多高?我们无从推测。我想,这条斜行线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不是从事后,而是在事先,不论是读者还是作家本人都很难想象, 从《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或《雨,沙沙沙》起始,会走到《小鲍庄》和“三恋”,走到《爱向虚空茫然中》。即使站在为她赢得更多读者的《长恨歌》那个点上展望,也没法预见《天香》,更不可能预见《匿名》——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保持着近40年的斜率,才绵延至现在的暂时的位置。 为什么王安忆的创作历程会是一条向上的斜行线呢?这个问题虽然不会有完满的答案,但我还是要试着给出我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应该是答案的一部分。 我想到的是一个特别常用,常用到已经很难唤起感受力的词,学习。古人说,学而不已,其实很难。一个人如果终生都是学习者,终生保持学习的能力,那真是了不起的事情。王安忆迄今都是一个学习者。我有时不免惊讶,她的学习欲望和学习能力如何能够一直旺盛不衰。 学习肇始于不足和欠缺。王安忆第一部长篇叫《69届初中生》。她自己就是69届初中生,16岁去安徽插队,所受学校教育不足,知识系统有欠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经历来说,虽然有知青生活经历,但算不上特别波折。 回到上海后做过几年编辑,即进入职业写作状态。要说人生经验,同代作家中丰厚复杂的大有人在,比起来也是不足和欠缺。这两个方面,王安忆都有相当自觉的意识。 经验的相对平淡,反倒促成王安忆对经验的精细分析和深度挖掘。她懂得珍惜,不会浪费,不会草率地处理。经验对她的写作来说是一个出发点,而不是目的地。除此之外,她更另辟新路,思考和实践不依赖于自身经验的文学写作。考虑到中国当代创作中并不少见对经验的过度依赖,肆意挥霍,或为经验所束缚——经验把一些作家的想象力局限于经验本身,王安忆这种文学上的实践和思考即显出特别的价值,这里不论。 王安忆为读者签名 回到教育的欠缺。2012年,在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王安忆发言说:“我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是我终生遗憾,也因此对学府生活心向往之,可说是个教育信仰者。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在大学门外完成教养的范例, 事实上,倘若我能在学府中度过学习的日子,我会比现在做得更好。”这个想法,此前她多次表达过。 不足和欠缺本身是具有限制性的,但意识到它,而且意识达到一定的强度,有可能反转出破除限制的能量。王安忆的解决方法不是避重就轻,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最朴素、最老实地去学习。这个方法短期不能奏效,也没有捷径可走,就是得踏踏实实、一点一滴积累。所以就成为一个长期的方法,日积之不足,月积之不足,年积之仍不足,那么年复一年,总会有可观的收获。同时,与时日俱移,逐渐也就内化为习惯,内化为需要。 如果说王安忆早先是对自己客观存在的不足和欠缺产生自觉意识而努力去补偿性地学习,那么到后来,她甚至常常是主动地“制造”、主动地暴露自己的不足和欠缺,由此而“再生产”出继续学习的欲望和能力。比如《纪实和虚构》的写作。一个优秀的作家经过较长时期的实践,总有办法把写作控制在自己驾轻就熟的范围内,写出较为完满的作品。但当不满足于轻车熟路,想要扩大写作实践的范围时,就要吃重,就要冒险,就可能露出弱点,显出欠缺。王安忆时不时会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把斜行线的斜率调到很大。但走过去之后,就是迈过了一道坎,上了一个台阶。在跨60岁的年龄段,王安忆完成长篇《匿名》,与以前写个人经验、写人情世故、写市井现实、写城市身世的作品有更大不同。她说写这部小说是因为不满足于以前那样的写作。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不像以前那样有把握和胜算。写好之后更是困惑,以后要写什么呢?使我满足的写作是什么呢? 不满足,没有把握,困惑,发问,这些从写作开始到结束之后的感受,不也正是学习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学习和写作是两回事,可是你看,写作在这里就变成了学习。《匿名》不正是对知识、对世界、对文明、对人怀着强烈的好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询,大胆地刨根问底,小心翼翼地尝试求解? 学习,这个词太平淡了,说一个人是学习者,通常就比不上说一个人是天才有魅惑力。而创作,我们强调它不同于普通的工作,因此也就常常突出天分、才华、灵感、启示等的非凡作用。有的作家喜欢讲类似于神灵附体的极端体验,不明就里的人崇拜神秘性。当然,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也不必否认。我不会无视王安忆独特的天分和才华,我想她一定也偶尔经历过灵感和启示降临的特殊时刻,但是这几样,没有一样能够支撑任何一位作家走30年、40年的写作上坡路。一个学习者,则能以持续的学习不断开发出的能量充实自己,走得更长更远。 从对不足和欠缺的补偿性学习,到努力把学习所得吸收和融化于写作,再到把写作变为一种特殊方式的学习,我觉得,在绵延的时间中,王安忆把学习的精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她写作的斜行线也层层上出。这条长长的上出的斜行线,是学习对学习者的回馈,也是学习者向学习的致敬。 转载自《红蔓》杂志2019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