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美学意味着一种感性的分配。康德的去功利的审美判断,以理解力与感受力之间等级关系的中立化确立了审美维度的核心,即以一种审美分离为前提的平等的“歧见”,由此带来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此乃“美学的政治”。存在两种试图取消审美的政治潜力的伦理模式:其一是以“习性”为基准的社会学批判,其二是以“崇高”为中心的绝对他者原则。“政治的美学”则表现为“民主”政治乃一种“仿佛”的操作,是任何人之共同权力的平等展演。柏拉图式的共识性的“仿佛”导致了以社会分化为前提的伦理秩序的循环,德里达式的异质性的“到来的民主”则排除了人民主体的歧见力量。总之,为了强调美学的政治和政治的美学,一种蕴含了知识的美学的思考方式和话语实践势在必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2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关键词:感性的分配; 美学的政治; 政治的美学; 知识的美学; 伦理; 歧见 作者简介: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法国哲学家,当代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译者谢卓婷,女,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该如何理解这个标题的语段结构?显然,它并非声称政治或知识必须具有审美维度,或者说它们必须基于感觉、感知和感性。它甚至也不是表明政治和知识应以感性为其根据,或感性自身即具有政治性。美学所指涉的并非感性,而是某种情态(modality),某种感性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虽然该术语从未被用作实词,但至少在其原初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架构了该美学空间的文本来理解它。当然,我指的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我将其当作建构了意义更为宽泛的美学概念的主导线索。现在我只想从该文本中抽取三个基本要素,它们构成了我所说的感性的分配。首先,是被给予的事物(something given),即由感觉所提供的形式——例如,在康德书中的第二节所描述的一座宫殿的形式;其次,对该形式的理解并不只是感觉问题,而是感觉自身的双重化。(对事物的)理解调动了康德所说的诸能力(faculties)之间的关系,即,提供给予物的能力与用给予物产出某物的能力之间的一定关系。这两种能力的希腊语为同一个词:感性(aesthesis)。这就是感觉的能力,一种既能感知给予物又能对其加以理解的能力。 康德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理解一种被给予的感觉。其中两种规定了一定的等级秩序。在第一种方式中,赋予意义的能力支配了传达感觉的能力。为支配被给予的感觉,理解力需要想象力的协助,此乃知识的秩序。这种秩序定义了这样一种关于宫殿的观念:宫殿被视作施加于空间和原材料之上的某种观念的结果,它体现于建筑师的设计蓝图中。该蓝图自身也符合建筑的目的;第二种理解方式则相反,感性能力对知识能力发号施令,此乃欲望的法则。此法则将宫殿视作骄傲、嫉妒或鄙弃的对象;第三种看待宫殿的方式则既不将其理解为知识的对象,也不将之当作欲望的对象。此种方式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力支配另外一种能力;“要么……要么……”(the either/or)的原则不再管用。两种能力和谐一致,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观者可能会认为这座宫殿的壮观是彻底无用的,他也可以将宫殿的壮丽浮华与穷人的悲惨境地对立,或与为了低廉的薪水而建造此物的工人的汗水对立,但此已远非重点。此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感性分配的特殊性,它摆脱了高级能力与低级能力之间的等级关系,即,以一种积极的(positive) “既不……也不……”(neither/nor)的方式而得以摆脱。 我们可以总结三点。首先,感性分配意味着对被给予物的一定配置(configuration);其次,对被给予物的这种配置会引起感觉(sense)与意义(sense)之间的一定关系。此种关系可以是连接的(conjunctive)或是断离的(disjunctive)。当它遵循不同能力之间一定的从属秩序,或遵守既定规则展开游戏时,此种关系就是连接的;当不同能力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支配规则时就是断离的;第三,连接或断离其实也还是一个等级问题:即,要么是不同能力之间可能被倒转的等级;要么就是无等级。在无等级下仍存在一种能力,其独特的力量正是源于对等级关系的拒绝,而对不同能力之间等级关系的拒绝所涉及的是社会等级的中立化(neutralization)。这在《判断力批判》的第二节中通过宫殿的例子就已表明。在后来的第六十节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强调,康德将之归于一种审美的共通感( sensus communis),一种在不同原则与层级之间达成和谐的能力。几年之后,席勒(Schiller)也在对作为形式冲动与感性冲动之间对立的中立化之审美经验的政治阐释中清晰表达了这一点。通过将两种能力之间的游戏转化成两种冲动之间的张力,席勒提醒了康德的读者至为关键的东西。在成为协力促成判断的能力之前,理解力(understanding)与感受力(sensibility)指定了灵魂的不同部分:较好的部分,即主导的部分,这是有权力予以尺度的知性(intelligence);另外则是从属或难以驾驭的感性部分,它只懂得感性的震惊和欲望的刺激。正如柏拉图所强调的,对个体灵魂的划分就是对集体灵魂的划分,这同样也是城邦中一种阶级划分:有注定要作为支配者的知性与制定尺度的阶级,也有感性、欲望和无限性的阶级,他们注定要反抗其所必须服从的知性秩序;而第三个术语——审美经验,则是对此类划分的补充(supplementation)。它不能被视为一个部分,而是一种再分配活动,一种采取了中立形式的活动。 我所说的审美维度就是这样,它是对那些自身还不能被视为组成部分的部分进行的补充计算。这是另外一种感觉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既揭示了处于感性之核心的划分又对其加以中立化的一种补充。让我们称之为“歧见”(dissensus)吧。 歧见并非冲突,它是对感觉与意义之间常规关系的一种扰动。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种常规关系就是“好的”对“坏的”的支配。它是处于博弈(game)之中的两种既互补又对立的权力,以这样的方式,唯一可能的扰乱就是“坏的”反对“好的”之斗争——例如,民主的欲望阶层反叛贵族的知性阶层。这种情况不会产生歧见,也不存在对博弈的扰乱。只有对立面自身被中立化之际,歧见才得以发生。 这意味着,中立并不完全等同于和解(pacification)。相反,不同能力、灵魂的不同部分,或者群体不同阶层之间对立面的中立,是对一种剩余(excess)的展演(staging),是产生更为激进的看待冲突的方式的一个增补。但是,正如有两种思考冲突的方式(共识的方式和歧见的方式),思考歧见的本性以及共识与歧见之间关系的方式也有两种。这一点是决定性的,即,存在着两种阐释共识和歧见的方式,一种是伦理的方式,另一种是审美的方式。 伦理(ethical)必须在其最初的“习俗”(ethos)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习俗”在表示适合于某个居所的存在方式之前,首先所指的是“住所”(abode)。伦理法则首先以一个地点(location)为其基础的法则。一种伦理法则本身也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取决于你是考虑地点的内在决定性,还是其与外部的关系。我们先从内部讲起。内在法则也是双重的。伦理最初是将一种经验领域阐释为运用属于某一地域的全体人员所共同拥有的特性和能力的领域。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因为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的更为高级的摹仿(imitation)的能力,所以有了诗。所有人都能够摹仿并乐在其中。同样,因为人不仅具有与动物一样发出表达愉快或痛苦的声音的特质,也有用之以揭示和讨论何为有用,何为有害,并由此推断何为正义与不正义的逻各斯的特殊能力,于是便有了政治。 众所周知,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共同特质并非人皆有之。世上存在着一些并非完全是人类的人类,譬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奴隶就只能“感知”(aisthesis)语言(理解词语的被动能力),而并不能“拥有”(hexis)语言(陈述和讨论何为正义或非正义的主动能力)。更为一般的是,由嘴巴所发出的一系列声音是清晰表达的言说,还是仅仅只是关于愉快或痛苦的动物式表达,这往往颇具争议。以这样的方式,伦理的普遍性通常被伦理的区辩(discrimination)原则所双重化。共同位置其实包含在赋予不同存在方式以不同位置的地形学(topography)之中。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工作场所就是一个在那里工作起来则时不待我的地方,这也意味着,工匠没有时间去任何其他地方。既然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也就没有能力去理解组成一个共同体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他没有政治的理解力。这种关系也可以颠倒。就工匠无非只是一种关于需求和欲望的人而言,他们对共同尺度是毫无感觉的,因此除了生产欲望与消费对象的场所之外,他们无处可去。这是一种伦理的循环,它将为人们量身定做的某个位置、某种职业,以及某种天资才能,即,一种感性的装配(the sensory equipment),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伦理法则因此也是在感性阶层与智性阶层之间的一种分化法则。 简而言之,作为一种内部法则,伦理法则就是根据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将共同能力的分享与不同能力的分配结合起来的一种感性分配。 但是,伦理法则也可以确立为一种外部法则。在《政治学》(Politics)中,在对基本的人类共同体作出分析之后,而对政治的动物作出陈述之前,亚里士多德很简略地构想并驱逐了一个没有城邦(polis)的主体形象。这是一个低于或高于人类的生灵——也许是一个怪兽或者神——一个无拘无束的(azux)存在,它不与任何一种与其类似的生灵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必然是处于战争之中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所简单描绘的这个外部形象也可以倒转而为一种不可度量的或无可替代的形象。根据一种分配法则联系起来的所有可度量或可替代的事物,在此都必须冒着被律法取消的危险而接受其律法。众所周知,这样一个形象已在最近几十年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复活:他者(Other)的律法、他物(Thing)、崇高(sublime),不一而足。 这就是我所说的对于共识和歧见问题的伦理阐释,也是对共同事物与其补充物的伦理解释。审美维度却是对此的另一番阐释,这种阐释既取消了内部的分配法则,也取消了不可度量的外部法则。审美维度导致了对伦理合法性的废除,也就是,对三个术语的伦理互补性的一种拆解。这三个术语是:共同习俗的规则,非此即彼的组成部分的分配法则,以及外在于规则之外的怪兽的权力。 它也可以被描述为是对“相同”(the same)、“相异”(the different), 以及“他者”(the Other)的一种伦理分配。与此种分配相反,审美配置的一般形式可以描述为:不是他者,也不是不可测量性,而是对同与异的重新分配,是对“同”的划分与对“异”的消除。审美配置重新演绎了差异的关系,其方式是使之中立化,并使此中立化成为对超出共识性分配之冲突的展演。不能按照分配的共识原则来计算此种超溢,但是,也不能遵循某种不可测量的他者性原则。处于两种超溢之间的差异就是伦理的他律性(heteronomy)与审美的异质性(heterotopy)之间的差异。 让我试着以我曾说过的“美学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政治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politics),以及“知识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knowledge)来对此进行说明。在每一个这样的领域中,都可能将审美的方式从两种伦理方式的形式中区分开来。从我所说的“美学的政治”开始。它是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中,审美经验(作为对艺术实践及其接受的可见性与可理解性形式的重新配置)介入感性分配。为了理解,我们先回到起点,也就是,回到康德将美作为一种“既不……也不……”的表现的分析。审美判断的对象既不是知识的对象,也不是欲望的对象。在由席勒所作的政治转换中,这一“既不……也不……”的原则被阐释为对知识阶层与欲望阶层之间的伦理对立的消解。这样一种美学的政治遭到了两种伦理批判形式的质疑。一方面,是认为其无视习俗之社会法则的社会学批判。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作品代表了此类批判,他断言,不受任何利益支配的审美判断的立场无异于一种幻觉(illusion)或一种神秘化(mystification)。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审美判断只是那些能够将自身从社会法则中抽离(或那些相信他们能够抽离自身)的人的特权,这种社会法则就是,根据不同的社会阶层,其趣味判断与其习性,即,与环境加诸其上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吻合。对宫殿之形式美的无功利判断,实际上是为那些既非宫殿的主人也非其建造者而保留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判断,他们不用担心工作或者资本,通过采取一种普遍思想和无功利趣味的立场,他或者她沉迷于其中。因此,他们的例外无非是确认了这样的规则,据此,趣味判断事实上包含在社会判断之中,它是对社会决定的习性的一种转译。这样的判断也是神秘化的一部分,它隐藏了社会决定论的现实,并且有助于防止社会体系的受害者获取自身解放的知识。 弗朗索瓦·利奥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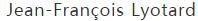 )提出了一种相反的伦理批判形式。利奥塔同样认为去功利的判断是一种哲学幻觉。他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逻辑怪物,试图将美的标准与艺术鉴赏之社会决定的公共性之间任何一致形式的丧失转换为古典的和谐关系。这种对一个失落的和谐世界的怪诞涂抹,隐藏了现代艺术的真实本质,不过,在康德的批判中也阐明了此点:现代艺术作品遵循着一种崇高法则。崇高法则就是一种不均衡的法则,一种在理解性与感受性之间任何共同尺度都荡然无存的法则。在第一个场景中,利奥塔将这种不均衡等同为感性问题的压倒性力量:一种声调或颜色,“皮肤或木块的纹理、香料的芬芳”之独特且无与伦比的特质。但是,在第二个场景中,他抹除了所有感觉的差异,“所有这些关系”,他说,“都是可以互换的。它们均可被命名为一个情感事件,一种精神尚未做好准备的动情性(passibility),它早已扰乱了精神,藉此,它所保留的只是一种模糊债务(debt)的情感——痛苦或者惊喜 。艺术的所有差异总计而为同一个事物:精神对某种不可驯服的感觉震惊事件的依赖。这样的感觉震惊反过来又表示为一种根本的奴役状态的标记,即精神对他者法则的无限债务。他者在此有可能是上帝的法令,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权力。在其他地方,我已经对这种以崇高代替审美中立化的伦理转向进行过分析,并且表明,这种假设可被认为是对康德崇高概念的彻底颠覆。我不想在此再作赘述。我想要集中讨论的是该操作的核心问题:利奥塔为了成全崇高的他律性,取消了美的异质性。其结果是,尽管它们来自全然不同的视角,这种操作与社会学批判的结果如出一辙。在这两种情形中,异质性的政治潜力都被归结为一种隐藏了服从之现实性的纯粹幻觉。 )提出了一种相反的伦理批判形式。利奥塔同样认为去功利的判断是一种哲学幻觉。他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逻辑怪物,试图将美的标准与艺术鉴赏之社会决定的公共性之间任何一致形式的丧失转换为古典的和谐关系。这种对一个失落的和谐世界的怪诞涂抹,隐藏了现代艺术的真实本质,不过,在康德的批判中也阐明了此点:现代艺术作品遵循着一种崇高法则。崇高法则就是一种不均衡的法则,一种在理解性与感受性之间任何共同尺度都荡然无存的法则。在第一个场景中,利奥塔将这种不均衡等同为感性问题的压倒性力量:一种声调或颜色,“皮肤或木块的纹理、香料的芬芳”之独特且无与伦比的特质。但是,在第二个场景中,他抹除了所有感觉的差异,“所有这些关系”,他说,“都是可以互换的。它们均可被命名为一个情感事件,一种精神尚未做好准备的动情性(passibility),它早已扰乱了精神,藉此,它所保留的只是一种模糊债务(debt)的情感——痛苦或者惊喜 。艺术的所有差异总计而为同一个事物:精神对某种不可驯服的感觉震惊事件的依赖。这样的感觉震惊反过来又表示为一种根本的奴役状态的标记,即精神对他者法则的无限债务。他者在此有可能是上帝的法令,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权力。在其他地方,我已经对这种以崇高代替审美中立化的伦理转向进行过分析,并且表明,这种假设可被认为是对康德崇高概念的彻底颠覆。我不想在此再作赘述。我想要集中讨论的是该操作的核心问题:利奥塔为了成全崇高的他律性,取消了美的异质性。其结果是,尽管它们来自全然不同的视角,这种操作与社会学批判的结果如出一辙。在这两种情形中,异质性的政治潜力都被归结为一种隐藏了服从之现实性的纯粹幻觉。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审美异质性的政治潜力。1848年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期间,工人报纸有过一个短暂的蓬勃期。其中一份名为《工人警钟报》(Le Tocsin des travailleur)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文中一个细木工(joiner)描绘了他的细木工同伴或在车间或在其正铺设地板的房间里工作的时光。他将之呈现为一种日记的形式。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它看起来更像是对《判断力批判》所作的某种个人化演绎,且与清楚表达了审美判断之无功利性的第二节尤为类似。康德以无须虑及社会用途与意义而去观看和欣赏的宫殿为例,证明了这种去功利性。这是细木工以自己的叙述方式对此作出的转译:“只要地板尚未铺完,他就喜欢这个房间的布置,相信自己是在家中。如果窗户是对着花园敞开的,或远远望去是一幅如画的风景,他便停下工作片刻,在想象中向着那片广袤风景滑翔,他比隔壁住宅的主人更好地享受着这一切。”这个文本似乎正是描画了布尔迪厄所描绘的那样一种审美幻觉。当细木工言及相信(belief)和想象(imagination),并且将这种愉悦与财产的现实性对比的时候,他自己就确认了这一点。但是,这篇文章在革命期间的工人报纸上出现并非偶然,在此,审美的相信与想象意味着的正是这样的事物:手的活动与凝视(gaze)活动的分离。透视主义(perspectival)的凝视,长期以来总是与统治权和权威勾连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凝视被重新挪用为一种扰乱身体与习俗之间的适当性的方式。这就是去功利性或者淡然(indifference)所带来的东西:对那种被认为一定要符合某一特定习性(明白工作将时不待我,以及其感知要与此种时间的匮乏相契合的工匠习性)的身体经验的拆解。不在意宫殿的真正归属是谁,不在意包含在宫殿之中的贵族的浮华与人民的汗水,这就是审美判断的条件。此种无知(ignorance)与那种隐瞒了财产之现实性的幻觉无关,而毋宁说,它就是建构一种新的感性世界的方式,这是在财产的世界和不平等的世界之中的平等世界。这样一种审美描述在革命期间的报纸上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正是这样一种对工人身体经验的拆解成为了工人政治发声的条件。 因此,审美的无知中立了伦理的分配。这种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社会学家分裂为简单的非此即彼,它要求你要么是无知的和服从的,要么是拥有知识的和自由的。这种二选一其实仍深陷于柏拉图的循环之中,即一种据此那些只适合于时不待我之工作的感性装配的人就没有能力获得社会机制的知识的伦理循环。打破此种循环的只有审美。它存在于感性装配与其必须为之服务的目的之间的断离之中。细木工在决定性的一点上与康德保持一致:审美经验的奇异性(singularity)是一种“仿佛”(as if)的奇异性。审美判断发挥作用的形式就仿佛宫殿不是一种(财产)拥有和支配的对象。细木工就像是拥有了那些远景一样在行动。这种“仿佛”并非幻觉。它是对感觉的重新分配,是对那些必定要根据高级或低级的能力,高等或低等的阶层而发挥作用的划分的一种再分配。就其本身而论,这也是对另外一种“仿佛”的回答:按照柏拉图的方式,城邦的伦理秩序必须被视作是上帝将金注入到那些注定是统治者的灵魂之中,而将铁加入到注定是劳作和被统治者的人的灵魂内。这也是一个关于“相信”的问题。很显然,柏拉图并不要求工匠们获得一种内在的确信,即相信神果真将铁加入了他们的灵魂而将金加入了统治者的灵魂,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便足够了。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像相信这是真的那样来运用其手臂、其眼睛及其头脑即足矣。他们这样做,更多的是使得这个有关适宜性的谎言与其自身条件之现实性两相契合。社会职业的伦理秩序最终以一种“仿佛”的模式出现。审美断裂则以另外一种“仿佛”打破了此种秩序。 这样一种简短的分析将我们带至我所说的“政治的美学”问题。在伦理视角与审美视角之间也一样是非此即彼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原因很简单:政治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法则或宪法,而是关于共同体的感性织构的配置问题,藉此,法则和宪法的问题才得以理解。(这些感性配置问题包括:)什么对象是共同的?什么主体被包含在共同体之中?哪些主体能够看到或说起共同的事物?什么论述和实践可被当作政治讨论与政治实践?等等。 我们想想我们世界上最普通的政治概念,也就是民主(democracy)的概念。对于民主,世上存在着一种共识性的伦理观点。这一观点将民主视作基于生命形式或由自由市场所决定的自由形式的治理体系。只要民主一直反对极权主义,这种在经济生活形式与制度体系,以及一整套价值体系之间看到的某种一致性观点就会备受青睐。不过我们知道,这种青睐在过去十年间已急剧下滑。一方面,政府和政治家们总在抱怨民主难以管制,民主受到了一个敌人的威胁,该敌人就是民主自身。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在抱怨民主是一种对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个体消费者的权力,一种不仅威胁着好的政府,同时也威胁着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和人类谱系的权力。我们无须在表面价值上展开争辩。重要的是,当他们通过对立民主的政府管理与民主的社会,从而激增了一种关于民主的共识性观点时,他们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处于民主之核心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也许并非一种不良政治体制的特征,而有可能恰是政治自身的特征。 换言之,当下对民主的批判所指向的是一种处于政治之核心的歧见。歧见不是一个角色与另一角色之间——在富人和穷人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而是说,它是对这种简单的关于支配与反叛的共识性博弈的一种增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增补?再一次地,它可以从审美的立场或伦理的立场来加以理解。 从审美的立场理解歧见,是从对权力分配的伦理法则作出中立化的角度来理解。正如我之前所提及的,伦理规则实际上是双重的;一些非此即彼的能力使得那种共同的特性被双重化了。根据这个原则,权力是某些有一定资格的人支配没有资格者的资格的运用。行使权力的人得以如此,因为他们是上帝,是牧师,是创始者的后裔,是最年长者,是最好的同类、最聪明者、最有道德者,等等。这就是我所说的起源(arkhe)的循环,或一种逻辑的循环,据此,权力的行使是在行使权力的能力中被预期了的,此种能力反过来又为权力的行使所证实。我曾声明,民主的增补是对此种逻辑的中立化,是对任何位置之去对称性(dissymmtry)的解除。这就是“人民(demos)的力量”这一概念的意涵。人民不是人口,它也不是多数或者低等阶级。它由那些没有特定的资格,没有隶属于其位置或职位的天资,也没有统治的潜力而只能被统治,或者没有被统治的理由而应该去统治的人们所组成。民主是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原则:统治者得以如此,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没有理由去解释为何某些人应该去统治其他人,除了一个事实:没有理由。这就是民主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权力与人民之间的一种断离式联结。悖论(paradox)就在于,民主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结果被证明是类似于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力之存在的唯一基础。在社会层面上运作着各种各样的伦理权力:在家庭、宗族、学校、车间,等等;父母支配孩子,长者支配幼者,富人支配穷人,教师支配学生,等等。但是,只要共同体是由这些权力的联结构成,只要它在整体上是根据一种或多种力量的联结而受支配,它就还不是政治的。为了使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成为政治的共同体,必须存在另一个原则,另一种权利,它是所有其他原则和权利的基础。但是,只有一个原则超越所有其他:即民主的原则与权利,或无资格者的资格。 这就是我对民主增补的理解:人民是对社会分化的集体的一种增补。它是一个由无资格者,以及在计数中不被计数为计量单位的人所组成的增补部分,我曾称之为“没有部分的部分”(the part of those without part)。它并不是指一群弱者,而是意味着任何人(anyone),人民的权力是任何人的权力。正是这样一种无限的可替代性原则或者漠视差异的原则,以及对任何一种去对称性的否定,可以作为共同体的基础。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就是因为它异质于社会之组成部分的计算。它是一个异端(heteron),但却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异端,因为其异质性相当于可替换性。其特定的差异就是对形成了社会秩序的差异或差异的多样性(它们意味着不平等性)的淡漠。民主的异质性意味着两种逻辑的断离式联结。通常被命名为政治的事物由两种对抗性逻辑组成。一方面,存在一些支配统治他人的人,因为他们是(或者他们扮演的角色是)长者、富人、智者等等,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支配那些没有地位和才能的人的资格;存在着各种以一定的位置与才能的分配为前提的统治模式与程序,这就是我所说的治安(police)规则。但是,另一方面,权力必须由另外一种权力所补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权力就是政治性的(political)。统治者的统治建立在这样一种最终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就是:没有理由说明为何他们应该是统治者。他们的权力就建立在其自身合法性的缺席之上。这就是人民的权力所意味着的:民主的增补就是使政治作为自身而存在。 我们可以从人民的存在模式中得出一些结论。一方面,人民的权力只是一种内在的差异,它对任何一种国家体制或权力实践既进行了合法化又进行了去合法化。就其本身而言,这也是一种不断消失的差异,它不停地被体制的寡头政治功能所取消。这就是为什么,在另一方面,这种权力必须被政治主体不断重演的原因所在。政治主体通过一种宣告(enunciation)的过程和扮演人民角色的展现(manifestation)而得以确立。扮演人民的角色意指为何?它意味着,通过把施加于特定群体的特定过错,与由治安分配(对任何人之能力的治安性否定)施加于任何人之上的过错联系起来,从而挑战部分、位置和能力的分配,这就是政治歧见。歧见是将两个世界——两种异质性逻辑——置于同一个舞台上,同一个世界中。这是一种不可通约性的可通约性(a commensurability of incommensurables)。这也意味着政治主体是以“仿佛”的模式而行动的,他俨然是人民那样行动,也就是说,是作为由不被计算为共同体之有资格部分所组成的整体而行动。这就是政治的审美维度:它是由那些仿佛是人民那样行动的主体(由任何人之不可计数的计数所组成)对一种歧见——一种感觉世界的冲突——所进行的展演。当一小群抗议者在“我们都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的旗帜下走向街头,就像他们曾在1989年的莱比锡城(Leipzig)所做的那样,他们知道,他们还不是人民,(但是)他们却创造了一种由尚未融入国家或尚未得到政府机关安置的人们所组成的开放集体。他们所扮演的是一个由没有特定的能力去统治或被统治的人所形成的不可计数的集体角色。 这就是我所说的对民主增补的一种审美理解,它也等同于一种政治的理解。我认为我们能将之与关于增补的伦理立作对照,这种立场可以用德里达的“到来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概念来加以概括。我的观察不应遭到曲解。我意识到,德里达也专注于一种民主概念的阐述,这种概念有可能打破作为富裕国家之支配方式与存在方式的民主的共识-伦理立场。我还意识到,德里达对新的民主概念的追寻,是其致力于反抗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压迫形式的诸多斗争的一部分。我承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所致力于的是民主的主要议题。然而,我仍然认为,“到来的民主”概念还不是一个政治命题,而是一个伦理命题。对于德里达而言,到来的民主不是一种使得政治得以可能的审美的增补,它是对政治的一种增补。因为德里达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人民的民主,其政治观念所欠缺的就是一种政治主体的观念,也就是政治能力的观念。原因很简单,某些事物是德里达不会为之背书的(endorse),即,关于中立化(或可替代性)的观念——对差异的淡然,或者在同者与他者之间的等值性观念。他一贯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关于“仿佛”的民主游戏。从这一点看来,只存在着某种二选一:要么是同者的法律,也就是自治性的法律;要么是他者的法律,即异质性的法律。 我所说的“同”的法律可由两个概念加以概括,德里达曾以此概括政治的共识立场的特征:主权(sovereignty)与兄弟情谊(brotherhood)。德里达无需讨论即认可了一个公认的观点,那就是,政治的实质是主权,这是一个源自神学谱系的概念。主权实际上可回溯到万能的上帝,上帝将主权授予了国王。相反,民主的人民则通过砍掉国王的头而轮流得到它。政治概念是一些几乎不可还俗的神学概念。按照此种立场,人民的概念不会具有任何特异性,它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主权的概念,一个与维持国家权力的主权逻辑保持同质性关系的自我决断的主体。所以,“到来的民主”的力量不是人民的力量。因此,受到怀疑的不仅是人民的形象,也包括政治主体的概念,以及那种将政治视为任何人之能力发挥的观念。正如他将政治的概念等同于主权的概念,德里达将政治主体的概念与兄弟情谊的概念也等同起来。从此点看来,在家庭式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破裂。正如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乃主权之父,政治主体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兄弟。即便是“公民”的概念——在过去的20年里,这是一个在法国政治话语中被使用且误用得太多的概念——在他的概念构想里都毫无意义。公民(Citizen)无非只是兄弟的另一个名称。我们不能不被德里达反对兄弟情谊或友爱的辩论所震撼,这其中甚至还包括着对平等(parity)的批判——仿佛一个平等的妇女,一个可替换的妇女,一个“可计数的”妇女依旧不过是一个兄弟,是一个主权家庭的成员。就像他所认为的,一个兄弟就是一个可被替换成另一个人的任何人,也就是一个具有可替换性特性的任何人。 因此,“到来的民主”不是那种由可替换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换言之,“到来的民主”能够与民族-国家的实践形成对立的,不是那种作为任何人之角色的政治主体的行动。它所致力于的是一个绝对的他者,一个永远不会与我们相同,也不能被替代的他者,或者,我们可以增加一点,是对一个不能展现他或她之他异性,不能展现他或她的包含(inclusion)与排除(exclusion)之间关系的他者。“到来的民主”是一种没有人民的民主。对于一个主体而言,它不具备发挥人民力量(kratos)的可能性。 这样一种民主暗示了另外一种“异质”(heteron)的状态:一种作为外部的、远方的、非对称的,以及无可替代的异端。为了应对他所说的“国际秩序”的(International Order )的“十大瘟疫”(ten plagues),德里达的“好客”(hospitality)概念暗示了比逾越民族-国家边界多得多的义务。好客(hospes)所要超越的,首当其冲的就是那种允许了互惠性和可替代性的边界。在这一点上,好客是人民的严格的对立面。好客的特征在于,在可能的或可计算的舞台,与无条件的、不可能的,或不可计算的舞台之间打开了一条不可协调的鸿沟。这里所排除的就是一种“仿佛”的审美表演(performance)。好客抹除了人民的异质性,因为他在政治和解的领域与无条件性领域之间,在法律的可计算与正义的不可计算之间拉开了一道根本的裂隙。这样的对立所取消的,正是那些扮演着尚不是人民的人民角色的表演。当示威者在街上说“这是公正的”或者“这是不公正的”的时候,他们的“是”(is)并非要对包含了其对象的决定性概念进行部署。这是两种正义、两个世界的冲突。这也正是政治歧见或异质性的意味所在。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正义被德里达所排除。在他看来,要么就是如同机器操作一般常规的、共识的应用;要么就是无条件的正义的法则。这就是“到来”(to come)所意味着的。伦理的“到来”和审美的“仿佛”相对立。它(“到来”)意味着,民主是不能被呈现的,即便是以人民的歧见形象,也就是说,以仿佛就是人民那样行动的主体形象。在此,不存在部分对整体的替换,也不存在展现着相同与相异之间的等价性的主体。人民的异位(heterotopy)被两种不可化约的异质性所代替:“到来”的时间异质性,以及“好客”(hospes)的空间异质性。这两种形式被联合而为“初来者”(first-comer)与“新到者”(newcomer)的形象。“好客”或“新到者”是不会走到同一性位置的他者,是其角色不能被其他人所扮演的他者。这种去对称性在《流氓》(Rogues)一书中得以清晰表达。当他将“任何人”当作是“到来的民主”的核心的时候,这个“任何人”与歧见主体是不一样的,歧见主体是那些肯定没有能力者之能力的人;德里达的“任何人”是一个关心的对象。德里达给予“初遇者”(first to happen by[le premier venu])这个借自让·保兰(Jean Paulhan)的术语以非常的意义。他说:“任何人,无论是谁,都处于‘谁’与‘什么’,活物、死尸和鬼魂的可渗透性的界限之间。”任何人因此正好成为了初来者的反面。这是一种具有绝对奇异性的形象,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所构想出来的那个低于或高于人类的生灵——低于人类的则是委托我们去关心(àrevoir)的动物、死尸,或者鬼魂;在这种意义上,他者,就是要求我们去回答他、她或者它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这就是责任(responsibility)的意义:对一个委托给我的他者的义务,对于他或者它,我必须予以回答。 但是,另一方面,他者是非互惠性地拥有凌驾于我之上的权力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譬如,在《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中,对面罩或头盔的效果分析就展现了这一点。鬼魂或者“他物”以一种取消了任何对称性的方式看着我们,我们却无法穿透它的凝视。德里达补充道,正是从面甲(visor)的功能,我们第一次接受了律法(law)——不是正义,而是律法。正义相当于我们的无知,相当于我们没有能力去检查其语词的真实:对于“一个说‘我是你父亲的鬼魂’的人,我们只能相信他的话。一种本质上对其秘密的盲目服从,服从于其本源的秘密:这是对禁令(injunction)的一种最初的服从。它将是全部他者的条件。”为了理解这一服从命题的至为关键之处,我们必须记住另外一个场景,即哈姆雷特与鬼魂之间的对质显然已经替换掉了的父与子之间的场景。现在,哈姆雷特正处于亚伯拉罕(Abraham)的位置上,而鬼魂则处于命令亚伯拉罕去杀其儿子的上帝的位置之上。正如德里达在《流氓》中所指出的,当我们强调异质性原则是处于此种关系之中心的时候,“这是一个……关于异质性、关于源自他者的律法,关于对他者(一个内在于我的他者,一个比我伟大而年长的他者)的责任与决断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借助于克尔凯廓尔(Kierkegaard),德里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时刻”(coup de theatre):命令亚伯拉罕去杀以撒(Isaac)的上帝确实是叫他服从他的命令。正如德里达在《赠与死亡》(Donner la mort)中所指出的,他说: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但是,他想要亚伯拉罕明白的是,你必须无条件地在背叛你的妻儿与背叛我之间作出选择,你没有理由选择我而不是萨拉(Sarah)和以撒。牺牲(Sacrifice)仅只是意味着选择,在绝对他者与家庭成员之间的选择,这无异于无论何时我进入到一种与任何他者之间的关系时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它强迫我为所有的他者而牺牲。“任何他者都是全然的他者”(Tout autre est tout autre[any other is wholly other]):这是一种对立面的同一公式,是绝对的不平等与绝对的平等之间的同一。任何人都能充当作为全然的他者之任意他者的角色。多亏了亚伯拉罕的上帝,任何人都得以扮演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角色。 于是,一种根本的异质性准则就与政治的平等准则旗鼓相当了;伦理性的任何人与政治性的任何人平起平坐。但是,只有通过对异质性伦理法则的自我否定或自我背叛,这一切才得以可能。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为了使得一种任何人的政治得以可能,整个伦理异质性的架构不得不进行自我取消(self-cancelled)。 正如前述,我不是说我的民主概念比德里达的更为恰当。我只是尽力概述了政治的审美理解与伦理理解之间的差异。德里达的“到来的民主”在此方面也许更有意义,因为它正是在其最难以辨别的界限上使得这两种方法的根本差别表现为最接近的近似关系。 为了强调美学的政治与政治的美学,必须启动某种话语,即一种蕴含了知识的美学话语。这一表述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它是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它充分赋予了由康德所构想出来的审美判断之显然是无伤大雅的定义,即审美判断意味着一定的无知这一定义以充分的意义。我们必须忽视宫殿的建造方式及其为了获得审美欣赏而追求的目的。正如前所述,这样的无知或者中止并非只是省略。事实上,它是对知识与无知的一种分配。对于一个细木工而言,对一座建筑的拥有及其目的的无知产生了两种知识类型之间的分离:其工作的专门技能与其所处环境(作为与那些对于远眺风景的愉悦毫不关心的人共享的环境)的社会意识之间的分离。它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念。这种信念并非作为知识之对立面的幻觉,而是两种知识之间的连接(articulation),是知识形式和与之相随的无知形式之间的平衡。正如柏拉图所声称的,连接或者平衡都必须被相信。知识的管理(economy)[14]必须以一个故事(story)作为前提。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幻觉或一个谎言(a lie),而是意味着知识就是以这样一种编排结构的操作作为前提。在此结构中,不同知识之间的连接才能得以相信;在此织构中,知识也才得以运作。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技术性的知识必须服从于一种目的论知识。然而不幸的是,这样一种为不同的知识与位置的分配提供了基础的科学,自身却没有可论证的基础。它必须被预设(presupposed),而为此之故,一个故事必须被叙述出来且要被人相信。知识需要故事,因为知识事实上总是双重的。再重复一遍,存在着两种处理这种必然性的方式:一种是伦理的方式,一种是审美的方式。 所有事情都围绕着“仿佛”的情形在转动。柏拉图以一种挑衅性的方式建构了它:伦理的必然性就是一种虚构。虚构并不是一种幻觉,它是为感觉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处地方(topos)、一个空间以及一种规则的操作。现代“人类”(human)以及社会科学拒绝这种挑衅。他们宣称,科学不承认虚构。但是,他们却想从中渔利;他们想要保持灵魂分配的地形学,这体现于注定是知道的人与注定只能为知识提供对象的人之间的区分形式中。我提到布尔迪厄早期的社会学,因为它是对推动现代知识的柏拉图主义加以拒绝或隐藏之最纯粹的形式。这种对审美幻觉的反对,并非某一个特定社会学家的观念。它是结构性的。美学意味着工人的眼睛可以从其双手分离,他的信念可以与其所处的环境脱节,而这正是社会学家如若要存在则须大加挞伐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种习俗必须被定义为一种习性;一个居所必须决定一种存在方式,而这转而又会决定一种思考方式。当然,并非只是社会学如此。譬如说,历史自身也有将存在和思考的模式建构为不同历史时期之表现的特定方式。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科(disciplines),或所谓学科思考的情形。就其效果而言,一个学科,首当其冲的其实并非对某个疆域的开发,也不是对一套适合于一定领域、一定对象类型的方法的界定。它最重要的,是将这个对象建构为一种思考的对象,是对一定的知识观念作出证明(demonstration)——换而言之,是知识与位置的分配之间和谐一致的观念,是两种知识形式和两种无知形式之间关系的一种校准。这是一种定义可思的观念,定义何为知识自身的对象能够思考和理解的方式。 学科通过切断语言和思想的共同结构来描画其疆界。因此,譬如说,它们在细木工的言辞和其句子意义之间,在其天然的物质性与其所表达的社会环境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他们致力于一场反对审美无知(它也意味着审美分离)的战斗。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投身于一场反对工人的自我战争的战斗。他们想要使构成社会的身体拥有专属于其位置和职业的习性(与其习性相一致的感知、感觉和思想)。要点就在于,这样一种一致性其实永远会受到干扰。无需主人(的指引),言词与话语在自由流通,将身体从其目的地转移开去。对于木匠及其兄弟们而言,这些词语可能是“人民”(people)、“自由”(liberty)或者“平等”(equality);对于其远处的姐妹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而言,它们则可以是“激情”(passion)、“幸福”(felicity)或者“沉醉”(ecstasy)。有一些景观是完全可以将凝视从其双手分离,并且将一名工人转换为一名审美家的。为了在身体状态和与之相呼应的感知与意义模式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学科思想必须不停地阻止这种内乱(hemorrhage)。它必须不停地追求战争,但却是将之作为一种安抚性的操作来追求。 因此,谈论一种知识的美学并不是一次走近感觉经验的机会,它是谈论沉默的战斗(silent battle),是对战争语境作出重新演示的时刻——这正是福柯所谓的“遥远的战斗的隆隆声”[16] (distant roar of the battle)。为了如此,知识的美学必须实践某种无知。为了在斗争中恢复其作为战斗武器的地位,它必须忽视学科的种种边界。譬如说,这正是我曾经将细木工的措辞从其常规语境,也就是,从其社会历史(它们往往将之视作是对工人身份的表达)中抽取出来时所做的。我所采取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径。这些只言片语不是描绘一种生活境况,而是对一种境况和与之相关的可见性形式及思考能力之间关系的再创造(reinvent) 。换言之,这样的叙述(récit)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是一个神话(myth);而它是一种反-柏拉图的神话,是对命运的一种反叙事。柏拉图的神话规定了在环境与思想之间的一种相互确认关系,而细木工的反神话却打破了这个循环。为了创造一种使得神话的此种神话关系可见、可思的文本和符号化的空间,我们必须启用一种“非学科”(indisciplinary)的思考形式。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没有界限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平等的空间,在这里,对细木工生活的叙述就进入到和能力与命运之组织分配的哲学叙述的对话之中。 这意味着哲学及其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实践——一种非学科的实践。传统而言,哲学已经被当作一种超级学科,它思考着社会科学的方法,或者为其提供基础。当然,这些科学也可能会反对哲学的这种地位,将之当作一种幻觉,因而冒充自己乃哲学幻觉之知识的真正拥有者。这其实是另外一种等级,另外一种将话语置于其位的方式。但是,还有一种更好的第三种方式(a third way)。它抓住了这样的时刻,在此,它颠覆了制定话语秩序的哲学的自负,成为以叙述的平等语言对秩序之任意性本质所作出的宣言。这就是我曾试图将细木工的叙述与柏拉图的神话结合在一起时所做的一切。 柏拉图神话的特异性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的:它将知识(savoir)的理性,倒转而为对故事 (conte)的一种纯粹任意性的坚持。当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向我们表明,一定的生活如何产生了表达这种生活的一定思想时,哲学家的神话却将此种必然性指认为一种任意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民而言,一个美丽的谎言同时也正是他们的生活现实。这样一种必然性(necessity)与偶然性(contingency)的同一——一种谎言的现实性——不能以将真实与幻觉作出区分的话语形式来加以理性化。它只能被叙述,也就是说,只能以中止了区分与话语等级的论述形式来表示。 在《裴德罗篇》(Phaedrus)中,柏拉图声称,我们必须在谈论真实性(vérité)之处来言说真实(vrai)。但是,也是在此处,柏拉图却求助于最根本的故事,即关于真理的平原,关于神圣驭手,关于在坠落的过程中,将某些人转化为灵魂中掺入了银子的人,而其他则成为运动员、工匠或诗人的故事。也就是说,事情全都颠倒了。当柏拉图最执拗地想要表明一种组织完好的环境的分配之时,他诉诸的却恰恰是对这种分配之最根本的否定:这是一种取消了话语等级及其所担保的各种等级的故事与共同语言的力量。基础的基础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审美问题(an aesthetic affair)。从此处我们能够想象一种指向故事的哲学实践,这种故事包含在每一种界定了一定习性如何产生一定的思考形式的方法之中。要点确实并不在于宣称学科乃错误的科学或其真实所为只是一种文学形式;也不是要从某些他者形象或外部立场来废除它们,这些他者形象或外部立场通常包括:实在界之创伤的揭示、事件的震惊效果、弥赛亚承诺的视域,等等。 要点既不在于倒转伦理共识内部的依存关系之秩序,也不指向一种全然他者的颠覆性力量。如果说一种哲学的审美实践意味着什么,那么,它意味着对这些分配的破坏。所有疆界都是以一种感觉分配的单一形式为前提的老生常谈。一种可思的地形学通常是一种操作剧场的地形学。没有特定的思想疆域,思想无处不在。其空间没有外缘,而其内部划分通常也是可思性分配的一些临时形式。可思的地形学是一种独特的关于感觉与意义的联合,关于临时的节点与间隙的地形学。一种知识的美学创造了种种增补的形式,它们使得我们可以对那些老话题,对相同或相异的位置,对知识与无知之间的平衡的配置进行重新分配。它暗示着一种话语实践,这种实践将重新铭记处于话语战斗(在此,没有明确的边界将作为科学对象的嗓音(voice)与把自身作为对象的科学的逻各斯(logos)分离开来)之中的种种描述与论述的力量。它意味着,它将在发明(invent)对象、故事和论述的共同语言和共同能力的平等中对其进行重新铭记。如果这种实践可以命名为哲学,它将意味着哲学并非一种学科或疆域之名。它是一种实践之名,是将不同疆界之特异性遣返至思考能力的平等共享层面的一种表演。在此种意义上,哲学的审美实践也可称之为一种平等的方法。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卷第2期。 本文选自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思(Nikolas Kompridis)主编的《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The Aesthetic Turn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London. New Delhi. Sydney: Bloomsbury, 2014),最初发表于Critical Inquiry 36 (Autumn 2009)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