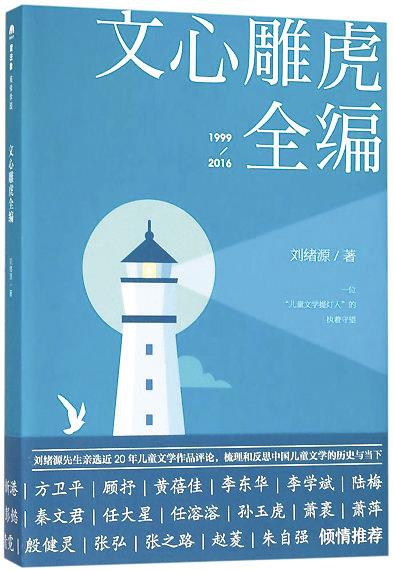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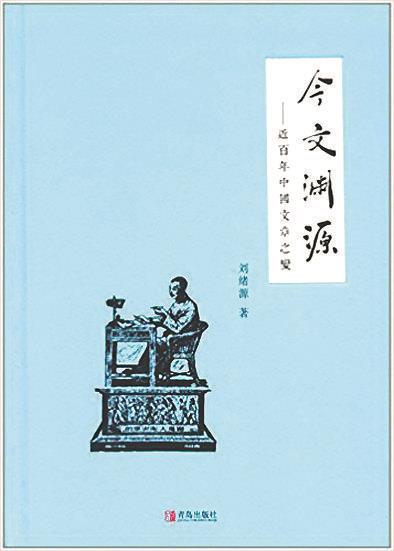 一 刘绪源先生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影响深广,但他首先不仅是一位儿童文学家,更是一位怀有开阔的学术志趣和深厚的文化关切的当代学者和文人。背衬着他的儿童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的,是在文学与文化里浸淫多年积累起的广博精深的见识、洞察和底蕴。所以,从儿童文学的视角解读刘绪源,应该看到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1995)与《文心雕虎》(2004)背后,他的大量研读、评说古今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犀利深透的书话与批评文字;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2013)的背后,他的梳理百年中国散文文体与艺术流变脉络的《今文渊源》(2011);看到《周作人论儿童文学》(2012)的背后,他的细考周作人其文其人及其文学史位置的专深独到的《解读周作人》(1994);也看到《绘本之美》(2016)这样的儿童文学普及读物背后,他的关注婴幼儿及“人”的审美发生的《美与幼童》(2014年初版,2017年增订版),以及《美与幼童》的背后,他与李泽厚的两部哲学对谈《该中国哲学登场了?》(2011)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2012)。这些看似非关儿童文学的研究旨趣与成果所代表的那个远不受限于儿童文学文类边界的视野、积淀和情怀、趣味,构成了刘绪源先生在当代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独特身影,也构成了他儿童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独特面貌和意义。 二 在当代儿童文学批评界,刘绪源先生的名字或许最令我们想起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初,在“五四”新文化思想和精神的激荡里,儿童文学这个不起眼的小文类在那些“素养深厚、心态自由”的大文化人中激起的关注和关切。当这些文化人带着他们深厚的素养和开阔的眼界进入儿童文学的地域,他们也带来了一种开阔高远的儿童文学的文类观、文化观和艺术观。某种程度上,刘绪源正是以他所激赏的那种 “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的姿态踏进儿童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地界的。他看待儿童文学的角度和视野,进入儿童文学的方法和姿态,都提醒我们,现代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囿于儿童接受层面的亚文类。在为“五四”先贤们所看重的儿童文学这个小文类里,蕴含着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一种高远的精神和抱负;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小体量和小题材里,也蕴含着现代文学写作的高级艺术与智慧。 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从来都是立足于儿童文学的这种“高远”、“高级”的境界和精神。而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同时,他也从未放下他在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哲学美学等领域的学术兴趣和研究实践。毋宁说,当他由普遍的文学和文化之“大”进入儿童文学的艺术及其批评之“小”时,他所做的不是专业范域的某种选择或限定,而是个人文化志趣的进一步实现和深入。在这里,儿童文学与文学、美学、哲学等领域的思考和创造,源头在一,归属在一,精神和标准的层级在一。因此,儿童文学“不应被小觑,更不可以妄自菲薄”。在儿童文学相对窄小的学科界域里,跨界而来的刘绪源的名字和他的研究批评一再向我们证明,儿童文学是一种具备“高级”性的文学样式,它也理该向着文学的“高级”境界不断打开它的视野、趣味和品格。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刘绪源谈儿童文学的作品、艺术、出版现象以及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等,总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而又切中肯綮的重要见解。《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做的是文学研究中毫不讨巧的主题研究,书中总结的“爱”“顽童”与“自然”三大母题,乍看同样素朴寻常。但你仔细读去,思想的光芒和洞见都藏在进一步的分析里。从今天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现实来看,刘绪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儿童文学的三大基本母题,其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母题本身的揭示,而在于它的有关母题的阐说,几乎涵盖了中外儿童文学发展至今形成的若干最基础的审美精神范畴,这些范畴是儿童文学层面的,同时也映照出人类永恒的文化思考、探求和困境突围的冲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修史的体量既不大,述史的规模亦不求完备,却以文学史脉的重新读解带出大量引人深思的新观点、新论见。全书第一论“白话文与《尝试集》”,提出“小儿声口”的儿童文学语体与现代白话语体源起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是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上对现代儿童文学的艺术与文化位置做了新的廓清和提升。这是刘绪源在《今文渊源》中已经提出的相关论点的进一步延伸,它对于我们从现代新文化的视角重观儿童文学,从儿童文学的视角重思新文化运动,均有独到而深刻的启迪。而书中关于陈衡哲、叶圣陶、凌叔华、老舍、张天翼、汪曾祺等现当代作家及其儿童文学或童年题材作品的重新解读,对于今天亟须重新整理的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而言,意义重大而深远。他的《美与幼童》,并非儿童文学专域的研究著作,但作者将儿童文学材料极具创造和洞见地发挥运用于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以及人的审美发生的探析,为审美发生学研究开拓了一个重要的新疆界,也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阔大的新方向。 三 刘绪源是一位富于创造力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但他从不提出大而无当的伪理论命题。或许是批评家的性格使然,他所做的一切历史的追溯、现象的总结、理论的建构等,无不密切关联着当下文学创作与出版现实的观察、思考和批判。《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中的历史重梳和重述,“不经意”间总会带出他对于当前儿童文学现状与问题的审视。《美与幼童》中的基础理论阐说,同样不时落到当下儿童教育、生活和观念的现实反思中。这些年来,刘绪源对于儿童文学现场的介入热情绝不亚于他对理论的兴趣。甚至,对于许多儿童文学的读者来说,刘绪源的名字更多地因其代表了当代儿童文学批评的一种精神和风骨而广为所知,并且受到大家的敬重。这些年来,他在充分认可儿童文学发展的通俗道路的同时,也向商业童书的艺术品质与艺术问题、儿童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等发出深刻的质询。他极其关注、肯定、鼓励年轻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也对他们的作品公开提出诚恳、坦率的艺术批评建议。他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个时代儿童文学批评的良知,他所赢得的尊敬则向人们证实着批评的精神和价值在这个时代并未被真正遗忘。 然而,比理论的气象和批评姿态本身更重要的或许是,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理论创造的智慧,以及儿童文学艺术批评的锋芒,无不扎根于最生动的作品感受和生活体验的土壤中。他从不抛开感性谈理论,从不远离作品谈批评。他的理论和批评因此不但是有风骨的,更是有温度的。那是文学的温度,生活的温度,归根结底,则是人的温度。绪源先生是对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美怀着最细致的敏感和最深切的热爱之人。这种敏感和热爱滋养他的精神,也在他身上默化为一种人文伦理的自律,那就是一切理论和批评的实践,都致力于永不对文学说谎,永不对美说谎。“美是不会欺骗人的”,这种建于开阔识见和深透洞察之上的对“美”的真诚信仰,构成了刘绪源的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底色。 仿佛命中注定地,他的学术志趣和人文追寻会在《美与幼童》中得到光芒璀璨的最后定格。他的所有关于和看似非关儿童文学的思考积累,奇妙地汇聚在书中这个与美有关的“儿童”的形象身上,迸发出令人炫目的理论华彩和思想灵光。在他最后的这部著作中,遍布着高度浓缩的思想发明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发现,它们在提出一种以儿童为独特对象的审美发生研究路径的同时,也照亮了通往“儿童”和“儿童文学”研究的许多幽暗、深邃、有着无限可能性的道路。 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上,刘绪源的名字会是一个被铭记的重要符号。但他同时也应是一个充满发掘可能的重要课题。他的那些富于生命力、生长力的理论和批评思考将向我们证明,时间的长河磨蚀一切,但思想的光芒永不黯淡。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