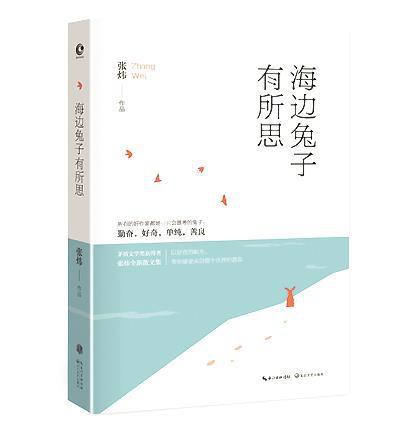 作家和动物都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小说中以动物的口吻自居,如夏目漱石在《我是猫》中的独特视角;或是寻觅着别样的自我,寻求一种镜像体验,如麦家在《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中以《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雪》展开了想象。张炜在创作随笔集 《海边兔子有所思》中如此说:“……它们注视过我少年时代的写作,分享我的快乐,也感受我的痛苦。我有时想想自己也是一只兔子,穿行在无边的海边林野中,因为写作,带来了那么多的幸福和哀伤。这些兔子是友伴,是读者,是知音。它们在倾听和阅读,最后也拿起了一支笔。”它们不同于厄普代克笔下那只爱吃窝边草的兔子,也并非《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神经兮兮的白兔先生,而是拥有勤奋、好奇、单纯、善良的正义形象。 不难看出,张炜的文学世界里住着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精灵,这与他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胶东半岛数十载的生活赋予了他对现实世界瑰丽的遐想,齐文化接近自然、充满自由的精神气质贯穿在他的创作之中,从《古船》《九月寓言》到《你在高原》,再到《独药师》,主人公变身思想的游牧者徜徉在半岛的海雾缭绕之中,传奇与荒诞基因融入到了血脉和举手投足之间。童年时期穿越森林,海上漂泊,驻足岛屿,也正是在这种奇异秘境之中锤炼出了他独特的个性语调,如他所言,一个好作家有两颗心特别宝贵:一颗童心,一颗诗心。这二者同时也是文学的初衷,更接近生命的本色。如果说,童心是张炜的创作起点,那么诗心则是引领他抵达文学的密钥。 张炜并不自诩为单纯的小说家,而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时代和地域变迁的记录者,日常理性观察为感性写作做着充足的准备。张炜始终将康德的道德理念视为创作的标尺,尤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声鼎沸、众声喧哗,许多人忽视了对自然的观照,正像他对这个文字泛滥的时代所提出的质问:“矜持自尊的作家面临尴尬的处境,究竟是做一个小丑引起火爆的围观,满足他人和世界的窥视癖,还是一如既往地专注于诗与思的追求,有自尊地活着?将小丑当成伟大的艺术家,将低俗下流当成伟大的艺术。可怕的是,当今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浊水,的确已经浸泡出这样黑白颠倒的古怪认知,并且进而怀上了这样的时代怪胎,它们正在成长一个个力大无穷的妖怪。” 诗心不仅意味着编织独具匠心的语言,还蕴含着虔诚之意,也就是对文字语义的敬重和写作机会的珍惜。如今随着读写工具的智能化,这种高效率给作家、读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出现了弊端,名利之心、外界影响、大众趣味左右着写作的初衷。相比于上个世纪末文艺美学思潮蔚然成风的时代,手捧经典之作阅读的读者凤毛麟角,事实上,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才应成为阅读的首选,而且在每一代读者的阐释中得到不同于往昔的回声。 张炜相信,历经时间洗礼的作品即是经得起推敲和打磨的,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一部长篇在心里埋藏少于十五年是不能写的。就像酿酒,年头短了,味儿不会醇厚。如他所说:“写了二十多部作品,每一部都全力以赴,不重复自己,不人云亦云。提防模仿和依从,警惕精明之念。”《你在高原》耗费了二十二年,创作之中他一度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长篇小说《独药师》也是历经了二十多载的“酿造”,聚焦于古代研究养生的“方士”和源远流长的“长生术”,这场寻仙之旅融入了他对齐文化情感复杂的想象。 尽管经历了无数场“文学马拉松”,张炜仍然自称为“业务选手”,他坦言,“写作应该是业余的,一个人当了所谓的‘专业作家’,更要保持业余的心情”。文字赋予读者的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沟通,因此在写作的旅途中,他把写作看成一座高峰,越是险峻陡峭,就越有征服的信心,越是陷入困境,就越能激发起文学理想初衷。怀揣着那份热腾腾的灵感,不惜在月夜穿过河流、沙丘、树林,长途跋涉与对方分享喜悦,暗夜独行的恐惧感全无。 (《海边兔子有所思》张炜/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