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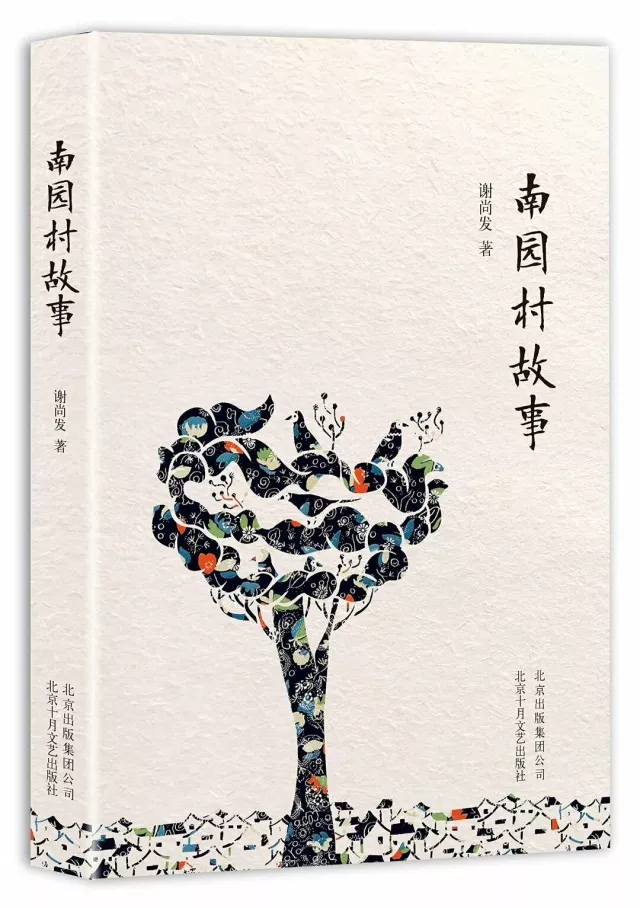
1
曾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亲朋好友说过,我这一辈子,不管干什么,批评,写作,或学术,都只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死亡问题,或人应该如何生活。这种看上去虚无缥缈,大到空洞无物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强调小切口,精耕细作的年代,以这种方式提出来,多少显得有些幼稚可笑,且容易引来别人的侧目。以犬子小民之力,撼汪洋之寥廓与峻岭之崇高,不自量力乎?确实有些不自量力,还天真的紧。然而又总是固执己见,秉性难改,就怪不得人家听了之后,摇头晃脑,叹息连连了。某一个瞬间,其实连我自己,都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如此问题,这样口气,除了庄子、孔子以及柏拉图,后来的黑格尔,外加中国的朱熹和王阳明,也包括海德格尔在内,敢于触碰一番之外,大概也就耶稣基督,佛陀和真主们,去殚精竭虑地考校这个事情了。但回头一想,古往今来的学问也好,思想也罢,其所谓的诉求,大约不超过这样一个命题的范围。那么以这个问题作为指导方向,当做高山,又有什么问题呢?奔着这个问题去,并不是说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何况,对于这样的问题,又有谁敢说自己窥探到了其中的奥妙呢?更别说彻底解决。任何人,恐怕都只能够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管窥其存在的一二罢了。这样给自己树立了一面大旗,也只是作为目标和追求,至于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还是十分难说的事情嘞!毕竟,一个人倘若要去爬山,而且立志要爬出别样的风采来,他选择万米高山,就无可厚非,还应该鼓励一番——说难听一点儿,那就是不自量力;说好听一点儿,那可是志存高远哩。所以我还是想尝试一番,提供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些许理解。其实,《南园村故事》的整个写作,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了这样一个方向。写作之前,不会给任何一篇小说设置什么样的“主题”,也不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诸如人性、善恶、救赎、性别、命运等之类的,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那就不禁自问,到底是要写什么呢?末了,写来写去,小说最后还是成了对这个宏大问题的某个侧面的触碰。
我一直以为,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死的存在。倘若死哪一天不存在了,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老不死”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完全可以肆意妄为,随心所欲——反正又不会死!末日的审判已经不存在,作恶也好,行善也罢,总之,都会活着。只有在死的拷问下,生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才会拥有意义。那么死就定然不是可怕的去处,反而是生的成全。只有在死那里,生才能获得最终的完成。貌似,这个问题就这么的解决了。但其实不然,因为从死里看出了生,还应该从生里,看出死的种种来。这恰是千百年来,多少古圣先贤,志士仁人所念兹在兹的永恒命题。于是只能回过头来,重新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
2
依然记得,在西安医学院工作的五年时间里,给学生上的每一节课。我常说,那五年是自己最为庸庸碌碌的五年,几乎一无所获。现在看来,大概是太过于偏激了。五年里,我所主张的讲台就是思考的平台,一直在实践着。对于我而言,教学与其说是给学生讲课,不如说是自我的沉思。那时候常常借助《西方名著导读》和《美学导论》的课堂,沉思并宣讲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存在本身不具有先天性给予的意义,活着本身只是活着。但人为何还要活着呢?活着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存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如此一来,这意义就根本没有崇高、渺小、价值大小等的区分,因为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总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或大或小,或善或恶,那都是属于他的意义。《牧羊》一篇中的安意儿,便是这样一种存在。他出生,患病,然后死去,仿佛是不存在的。但对于他而言,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牧羊,最起码他在南园村的西埂上,牧羊的那一刻,是在创造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另外,《秋夜》一篇,说白了是一个借种的故事。对于三巧儿来说,生孩子,在孩子的身上延续自己的存在,就是她给于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意义,更是给丈夫的生命存在一种意义的行为,而不管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丈夫的亲生骨血。对于他们而言,活着本身就是意义,此外还别求什么呢?英雄救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虽然充满了故事性,但是我却更喜欢在几乎没有故事的地方,书写属于这些最为普通、平凡的人们的故事。他们基本上不被人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一隅,犹如一只蚂蚁,倘若哪天死去了,就像我们不知道蚂蚁的世界里死了一只蚂蚁一样。甚至我们还会一不小心,走路的时候,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对于他们而言,生命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去理解他们的活着?
这样,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宣讲的自己的沉思结果,也便成了我创作的动力。生命存在本来没有意义,之所以要活着,就是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这便是生命存在的意义了。说来有些拗口,且有点儿不知所云,但确实是一直萦绕心头的沉思,也是课堂上宣讲的“圣经”。这样一来,“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人应该如何生活,哪里有一定的程式呢?人生如戏,说的好听,可唱戏有唱戏的套路和规矩,人生哪里去找那故事的脚本和唱腔的调性呢?任何一个人,只不过各安了一份自己的生命样式罢了。乞丐有乞丐的存在样式,那就是乞讨;妓女有妓女的存在样式,那就是卖淫;书生有书生的存在样式,那就是读和写——如此,就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书生的生活方式,就天然地比乞丐和妓女高尚,或者在道德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在领受个人的一份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各安了自己的性命罢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南园村故事》基本上所写都是无名小卒们,各安了自己性命的一种生活方式。或长或短,或悲或喜,或生或死……无论如何,也都是他们安顿生命的活法。如此,《一八九二》中那个好色而淫荡的中学教师和那个四处偷情浪荡的女人,又有什么好谴责的呢?《父奔》中高频率出现的性器官和性行为的字眼,又有什么好扎人的呢?那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样式而已!这么说,意思就是,倘若取了悲悯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比他们高明到哪里去,并不比他们更道德、更谦谦君子!所以,写这些人物的生活,初衷里的目标,只不过是展示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罢了,且都带着悲悯的感觉去的。正如《哭丧》中,巧英对哭丧的理解,对死的想法。人都有一死,是欢歌舞蹈、鼓盆作锣如庄子一样,还是摧肝沥胆、思之如狂像韩愈、归有光一样,其实也都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那么哭丧,到底是唱,还是哭;到底是哭死人,还是哭自己,在巧英那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从生里看到死,再从死里看着生。以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多的沉思又返回到问题的起点上了——只有在死的拷问中,生才会显示出它的全部意义来。
3
这些小说陆续写于2009年到2017年之间,跨越的时间不可谓不长。但修改的时间却相对集中,也就这两年的事情。故乡之萦绕于心头,绝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那是一辈子的期许和依托。所以无论身在哪里,处于何种境况,故乡都会随时跳出来,显出它存在的丰富性和人物的鲜活性。想起故乡,除了对外在的田野、河流、庄稼等有一个轮廓性的概念之外,便是时时跳到眼前的故乡的人物。三教九流,男女老少,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酸甜苦辣,以至于生老病死,就不断地跳跃在眼前。某一种时刻,恍惚中,总觉得那写的并非是我的小说,而是他们跳将出来,或自言自语,或有一搭没一搭的叙话。既然是叙话,肯定是男人之间会神神秘秘,色眯眯地说起女人;女人也会嘻嘻哈哈,把身子的那点事儿当做笑话说了。无伤大雅,或者大俗大雅,其实形容他们都不太合适,因为对于他们而言,那还不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何须大惊小怪?连光棍都知道男女之事,何况那些经了男女之事的人呢!这些小说写起来,往往有时候会格外大胆而显得低俗不堪,令人诧异。但我总想,请他们出来说话,除了说这些话之外,他们还能说什么呢?聊哲学?侃人生?开口闭口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政党、体制或暴力?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和金融货币?都不会。他们的日子里,有的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吃饭睡觉去种地,时不时地热心着男女之事。所以内有一篇,名曰《土缘》——对于乡民们而言,土里土气,才是生活的本色。
但《南园村故事》又基本上都不是实有其事。大多都是取了一个影子,添油加醋,铺排抻拉,成如今的小说模样。往往也会有一些对号入座的嫌疑,那只不过是他们的影子罢了。《杀猪》实有其人,谢法钱我该叫叔,代金富是村子西南头的邻居,也能说上是亲戚。他们杀猪我是亲眼见了的,从记事儿起到2014年左右,就亲历了不少杀猪场面。大概2000年以后,家里常杀年猪,都是他们的杰作。小说里的华山,便是用了我自己的小名,因为每次杀猪我不但要帮忙,还得操心干活,逮猪、拉猪、割肉之类的。《年死》里的来运,也是该叫做三叔的光棍,兄弟吵架,其实比小说中来得还要惨烈。那一架吵的,整个南园村没有人不知道。可没有一个劝架的,打的头破血流才算散了。那时候,来运已经死了,吵架是两个哥哥的事情。南园村里,打架最厉害最凶猛的,闹别扭扯龌蹉最多的,差不多都是亲兄弟。不是一家人反倒客客气气,礼尚往来。这很奇怪,但也不奇怪。《一八九二》的原型,是初中的一个班主任,就不点名道姓了。他小有才气,吸引了不少女生的好感。一个女生初三毕业前,怀了他的孩子,为此女生的父母在校园里大闹了一夜。女生的父亲拿着铁锹就去砍那好色的班主任。后来大概是赔钱了吧,事情就算过去了。至于那个女生以后是怎么过的,也没有打听过。他们一家因了这个丑事,出外打工多年不回家,到现在也基本上是音信全无。《父奔》写好后,第一时间给一个朋友阅读,她说了一个担忧的理由——别人家到时候告你!颇使我有些顾虑。里面的叙述者,是我的小学同学,也舞文弄墨。为这个小说,还特意告诉他,将会用他的名字和故事。人有其人,事有其事,但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怕就怕我的虚构反而会变成另外一种以讹传讹。无奈,只得将姓名隐去,做了较大的修改,勉强算是符合了小说与纪实的区别,才放下心来,收入其中。《先生》虽曰小说,实则是一种心念。人无其人,事无其事,却是心中的执意,久久不能挥去,取了老辈人中的两个姓名,铺排关于他们的故事,却早已经成了渴求、期盼。但院落却是南园村的院落,花草也是南园村的花草,以至于麦田、竹林、河流,无不印刻着南园村的影子。
4
小说基本上都是截取了南园村的人们生活的某一个横断面,不刻意强调故事的吸引人,而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展示。所以褒贬是没有的,谴责与愤恨也是匮乏的,要说有什么情感的话,也顶多是——说好听了是悲悯之心,连着自己也被悲悯了一把;说得难听点,也不过是兔死狐悲罢了。人和人都是一丘之貉,也就必须铭记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训诫。小说也就不可能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以怒目圆睁和哀其不幸的方式,批判谴责他们的腌臜肮脏,龌蹉猥琐,再高高在上地给芸芸众生指点迷津,从而走上康庄大道。还是那么一个意思,每个人活着,只不过是取了一种各安自己生命的样式罢了,充当圣人去指责、教会愚顽,本就是可疑的态度,自己所主张的种种也未必就在智识上高人一等。最终还是坐下来,搬个凳子,和他们平起平坐地叙话,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的表情,说他们的心思。整个《南园村故事》就是用了一个“内在的外来人”的视角,去观察他们的生活,然后写下来,以他们的悲喜为悲喜,以他们的爱恨为爱恨,以他们的生死为生死。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写作态度。我不是那种善于打腹稿的人,不可能把一篇小说在肚子里已经摸得滚瓜烂熟了,再动笔一气呵成地写下来。我习惯于“以意贯之”,先有了那么点儿意思存在心里,然后想他们的故事,给他们推到独特的情境中,让他们来表演,至于细节到底如何发展,还要看他们在故事中自己的表演如何。所以每一次,我只有进入到小说的写作状态中,他们的故事、行为、言语和音容笑貌,才会那么逼真地展露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在写作中,我才知道该怎么写,才知道该写什么。毕竟,那是他们自己的表演,也就需要我自己的投注其中。《父奔》是这么写出来的,《杀猪》也是这么写出来的,几乎所有的《南园村故事》都是这么写出来的。最典型的就是《哭丧》。2016年的冬天,萌生了写故乡哭丧的想法。原因是好几年前的冬天回家过年,有一夜,南园村的北边,大约是段庄,或者后段庄,也许是谢庄,大梁营,传来了悲戚的哭丧声,且经久不息。大概唱到凌晨三点钟左右。听来字字悲伤,句句传情,其中情感的婉转曲折,凄惨哀怨,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抑扬,甚是动人心魂。念念不忘,竟至觉得,应该将它写出来,把故乡的那一群哭丧的人的生活给写出来。于是就展开想象,思考如何去经营。2017年过年回家,很悲哀的是,又听到了故乡那些老人们的丧事,却并没有了哭丧人的身影。不免心中失落。这些年,哭丧确实比以前要盛行的多,但因为火葬的政令非常严苛,而人们又想要全身下葬,不愿意死了还要再遭受火烧的痛苦,居多都是偷偷地,埋掉拉倒的,谁还会那么大张旗鼓地,哭丧呢?过年后,立春节气带来了暖意,想着该是写的时候了,但立意却不明确,想着纯粹现象的描述又太过于单调,就在聊天中,和家人说起过这个小说。至于到底如何去写,虽然心中多半是想得差不多了的,却还是觉得朦朦胧胧,细节并不清楚。于是,迟迟不能动笔。《杀猪》一篇写完后,是要开始写作《哭丧》了。走在路上,头脑里一直转着,仍旧不知道如何开头。倒是先想到了另一篇小说《先生》的开头,于是就先写下来。结果,《先生》的开头还没有写完呢,《哭丧》的开头就唰的一下,从天而降。不敢怠慢,赶快写下来。其实是极其简单的一句。后来逐渐地,自己融入到小说之中,根本觉得那写的不是别人的故事,以至于究竟要怎么哭,自己先实验上一回,出声,拉腔,前推,后压,扬出去,再收回来。一次次地,模拟着哭——还得是持久战的哭,夹杂着唱的哭。写作过程中,想到悲切处,不自觉地,竟也眼泪涟涟。于是,自己在写作中,融入进去之后,也时时地像巧英一样,哭啊,想啊,揣摩啊的。那声儿,那腔调,那曲折婉转,一样也不曾少过。因此,整个小说写来,才更加的顺利。不管是悲欢,还是生死,只有把自己放进去,在文字中过活一回,小说才能写得圆满,才会写得感人,才会有一种爱充盈于文字间。
曾经在一个创作谈中言及,我特别喜欢修改自己的东西,因为觉得它们总是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也因此就极端地不自信,总以为写得不怎么好,需要修改,再修改。到底是不是修改后的比以前更好,我自己都拿捏不准了。但写作就是工作,认真的工作态度是对任何一位读者的负责。往往,花费在修改上的功夫,比写作还要多出几倍。写好后,妻子往往是第一读者,她从自己的角度提出的一些建议,也丰富并提升了小说的纹理和质感。可以说,她算是这本小说的第二作者哩!
常常莫名其妙地想文学到底何谓?写作到底为何?逐渐地,心中也多少得了些启发和顿悟。写作是难的,是永无止境的跋涉和不知疲惫的精神拷问,甚至有时候带着自噬其身的残忍和决绝。但真诚的写作者,应该是勇往直前的尝试者,也是执著如一的冒险家,更是躬身自省的生活人,不会因为伤痕累累而退缩,也不会因为清汤寡水而放弃——写作更像是指向自身的沉思,是返身观照自我的一种方式。它总是要求扪心自问,忏悔救赎,以便自渡渡人。生命存在的永恒命题便是认识你自己,而最智慧的人拥有的知识,也只不过仅仅是自知自己无知罢了。我也是一个无知的人,只不过是知道了自己的无知,且试图去探求更多的未知世界的摸索者而已。
我得继续前行。我还是继续前行的好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