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為準”與“中文為準”
──香港中文的一個難題 姚德懷 [本文見《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聯合出版, 1996年12月。本文也曾在《中國語文》上刊出, 1996年第2期總第251期, 第113-120頁。] 長期以來, 香港社會重英文輕中文。早期只有英文是法定文字。七十年代以來, 雖然中文也成了法定文字, 但是重英輕中的本質沒有改變。法律上的文件、合約都是以英語寫成。有時即使有中文本, 文件上卻注明:有歧義時以英文本為準。現在面臨九七過渡, 很多人希望能把重英輕中的局面扭轉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條也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除使用中文外, 還可使用英文, 英文也是正式語文。”1 但是, 語言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社會現象, 基本法的規定只能視為引導性的原則。以後是否可以改變社會上重英輕中現象, 以至如何才能改變重英輕中的現象, 這都牽涉到一系列極為複雜的問題。 這些問題更須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二百年前清廷鎖國時代, 語文也是自給自足, 既不輸入, 也不輸出。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807年來華。那時候“中國人教授外人以中文是犯死罪的”,“外人學習其語文或購藏其書籍為大罪,……藏有外國書籍為大罪。”2 十九世紀的變局導致了亙古未有的變化。鴉片戰爭 (1840年) 引起漸變, 甲午戰爭 (1894年) 引起突變。語文方面也是如此。1915年的《辭源》編纂緣起說:“癸卯甲辰 (按即1903-1904) 之際, 海上譯籍初行, 社會口語驟變, 報紙鼓吹文明, 法學哲理名辭稠疊盈幅, 然行之內地, 則積極消極內籀 (Induction, 現稱“歸納”) 外籀 (Deduction, 現稱“演繹”) 皆不知為何語, 由是縉紳先生摒絕勿觀, 率以新學相詬病。” 二十世紀的種種變化導致目前華人分居五湖四海三洋兩岸的局面。中國本土的風俗習慣觀念語言本來就有東西南北的差異3, 經過了百多年來歐風美雨日霜俄雪等等的侵襲或滋潤, 各地華人的風俗習慣觀念和語言變化極大4, 而往往又不是同步的。就語言現象來說, 不少人純從語言本身來說明問題, 我嘗試舉例從觀念的角度來闡釋一些有代表性的混亂現象。 1. 改曆法引起的混亂 a. 中國本用陰曆。民國改用陽曆, 或稱“國曆”(名“國”實洋)。但是民眾在觀念上在長時期內還不一定能適應。例如張三填報出生日期時填寫 a. 1941年12月1日生, 但他實際上是 b. 陰曆辛丑年十二月初一生。幾十年後要填表時一時無法查到陽曆生日, 也就無奈以“陰”為“陽”。而實際上他的陽曆生日應為 c. 1942年1月17日。因此張三現在 (1995年12月9日) 應該是53歲 (按 c 算), 但也可以是54歲 (按 a 算), 也可以是55歲 (按中國舊虛齡算法。) b. 民國改用陽曆, 並以舊曆元旦為“春節”。“春”有多種定義。中國本來也有以農曆元旦為春天開始的簡單化的說法, 所謂“大地回春”。但是過了接近一個世紀, 國人仍有“以陽代陰”在陽曆1月1日就慶祝“大地回春”的。例如1990年元旦,《人民日報》刊出了題為“九十年代第一春”的社論。1994年1月, 徐世榮先生在“歲朝清供”一文中說:“喜迎1994年的到來。……聊當歲首新春的芹曝之獻吧!”5 1994年1月12日, 香港《大公報》在南京金陵飯店舉行“新春酒會”。1994年12月23日 (冬至翌日) 周南先生發表“新年賀詞”, 內說“1995年元旦即將來臨, 我謹……致以新春的問候……。”詩人會說,“冬天到了, 春天還會遠嗎?”6 2. 改度量衡制引起的混亂 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 以米突制為度量衡標準, 採用“公尺”、“公斤”、“公升”。並設輔制, 分“市尺”(=1/3 公尺),“市斤”(=1/2 公斤),“市升”(= 公升)。民眾又簡稱為“尺”、“斤”、“升”。 此制50年代仍為人民政府沿用。但新制舊制 (清朝、民初、目前香港) 都用“尺”這個字, 實屬不智。現在香港用的“英尺”也常簡化為“呎”、“尺”, 讀如尺, 更形混亂。向諸位提兩個問題, 香港1995年的“斤”是什麼“斤”?7“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里”是什麼“里”? 1933年, 我國著名學者嚴濟慈先生在他的名文《論公分公分公分》8 中, 已經指出同名異物為禍之烈: ‧今乃一個名詞, 包含三種意義, 其混淆費解恐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任何民刑公私法規條例中, 決不能容有如是混亂名稱之存在。 ‧今此數種基本單位之取名, 不幸竟相雷同, 毫無殊異, 則日常應用上, 困難之從生, 固屬無可避免, 而科學教育上, 貽害之深遠, 更不知將伊於胡底。 ‧未來之國民, 於面積觀念, 將永無了解之一日。戕喪兒童腦力, 阻礙學術進步, 莫此為甚! ‧小則誤人耳目, 大則顛倒是非, 其足阻礙我國科學之發達與普及, 可斷言也。 香港近二十年來推行所謂“十進制”。只看香港中文“十進制”, 難以理解, 要看英文口號、標語“go metric”才能明白。原來香港中文“十進制”意即“米突制”。但是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 3. 學術名詞的混亂和誤導 且以語言學名詞為例。 a. 英語 word, 早期譯作“字”, 後來譯作“詞”(一般香港人仍然說“英文字典”, 不說“英語詞典”)。但是漢語裏是否真的有“詞”, 漢語“詞”的定義是什麼, 語言學者也還沒有一致的看法。9 b. 英語 verb 譯成“動詞”, 但是有的動詞不動。季羡林先生說: “我學外國語言是從英文開始的。當時只有十歲, 是高小一年級的學生。……當時最使我苦惱的是所謂‘動詞’, to be 和 to have 一點也沒有動的意思呀, 為什麼竟然叫做動詞呢?我問過老師, 老師說不清楚, 問其他的人, 當然更沒有人說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 我才知道, 把英文 verb (拉丁文 verbum) 譯為‘動詞’是不夠確切的, 容易給初學西方語言的小學生造成誤會。”10 c. 英語 adverb 英漢辭典譯成“副詞”極易誤導。adverb 和漢語“副詞”是兩回事。 d. 譯詞混亂妨礙學術討論。香港中文大學黃繼持先生1994年到蘇州去參加了“當代華文散文研討會”。回來後寫了一篇文章。11 他說: “‘散文’是甚麼, 幾天會開下來, 論者各說各的。到了最後一場小組討論, 主持人籲請與會者, 他日刊出論文時, 先用幾百字說明自己對‘散文’所下的定義。聽來有些好笑, 但此中實在蘊涵一個很嚴肅很重要的論題:源於五四前後西方文學觀念移入, 導致本國文學概念與文學術語之調整, 以及在調整過程中, 古今中外觀念雜糅, 造成一定的‘模糊性’。” e. 譯詞混亂常使學術討論偏離主題。1995年5月6日, 香港中文大學何萬貫先生在“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香港) 宣讀了“論範文教學的統整”一文。與會者對“統整”一詞大感興趣, 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後來何萬貫先生指出“統整”一詞實譯自英語 integrate。英語 integrate 有多義多譯。個別與會者提出是否譯為“整合”、“綜合”為更好。何先生指出,“統整”一詞其實已為台灣語文教育界採用。這一節語文教學的研討差不多變成了詞語的研討。 4. 譯詞難用 詞典說:“拷貝”只能用於電影, 其他物品的 copy 不能用“拷貝”。錄音帶、錄像帶、磁盤等的 copy, 香港人為了貪圖方便, 常常在中文裏直接夾用“copy”。要用純正漢語, 必須轉個彎兒來說。但如此則須處處小心。一不設防, 便會引起誤會、麻煩。 據說中國某學者甲出席某一國外會議作為 observer。回中國後自稱是某一會議的“觀察員”, 引起了一些同行的不滿。那些中國同行認為“觀察員”必然是高身份的, 名稱不能亂用, 認為某學者甲是自己抬高身份!如果某學者甲照實自稱為“observer”, 那就沒有問題了。12 又有中國某學者乙是國外某學術機構的 academician, 他自稱是某機構的“院士”, 也引起一些同行的不滿。那些中國同行認為,“院士”必然是高級的, 某學者乙也是在自己抬高身份!同樣, 如果某學者乙照實自稱為“academician”, 那也就沒有問題了。中文譯詞真是難用啊! 香港也有類似現象。英語 officer 一詞有多義。直譯可以是“負一定責任的辦事者”, 政府裏就是“官員”, 有些機構裏就是“幹事”。香港中文, 經常譯成“主任”。例如香港政府“中文公事管理局”裏就有上百位 Chinese Officer, 從事有關中文和翻譯的工作。他們都是“中文主任”。因此有一百多位“主任”, 而沒有一個副主任! 5. 對等問題 這就牽涉到所謂“對等”問題。再舉大學職稱對等問題為例, 說明混亂的情況。“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實際首長, 根據英制, 稱 Vice-Chancellor, 簡稱 V.C.。香港中文稱之為“校長”13。但按照字面, 或根據英漢辭典, Vice-Chancellor 的中譯, 只是“副校長”。因此, 據說在大陸和香港雙邊學術交流初期, 雙方為此曾經發生過誤會。英制大學 professor (教授) 以下有 reader 一級14。英漢詞典一般譯為“(英國大學的) 高級講師”。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初, 定譯 reader 為“教授”。之後香港中文也就一直稱 reader 為“教授”。1995年香港, 大學的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字面義為“講師”、“高級講師”) 據說對等於中國大學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另一方面, 大陸高等院校教師中據說以“博士生導師”地位最高。而不成文說法是:英制大學的 lecturer 原則上都可以是“博士生導師”!最近的發展趨向是:香港各大學教師職稱制度正全面由英制改向美制、中制。“講師”將自動轉稱“助理教授”、“副教授”。 國內 (大陸和台灣) 都以“研究員”為高級職稱, 相當於教授。但在香港, 任何大小機構的研究人員都可稱為“研究員”。“高級研究員”也非少見。 6. 譯名問題 譯名問題是老問題, 也一直是熱門問題15。這裏舉些個別例子, 以見問題的嚴重性。 a. 香港習慣替外國人取一個中國化的姓名。這種“譯名”(其實是“取漢名”) 方法, 可以追溯到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香港前任總督 David Wilson 本來就有一個漢名“魏德巍”。他任港督時香港中文公事管理局替他改換新名“衛奕信”。香港中文公事管理局的一項工作就是替外籍官員起漢名。風氣所及, 香港很多學校、機構的外籍人士多有漢名。 b. 英國政府高級官員也都有漢名, 據說全由英國駐港商務專員公署決定。 Malcolm Rifkind 任國防大臣時, 該公署已經為他取名“聶偉敬”。1995年7月6日, Malcolm 出任外相後, 該署為他改名“李文君”。但是, 7月19日, 該署又罕有地發表聲明, 棄用“李文君”改回“聶偉敬”!這種做法, 是否太隨便了? c. 中文報章提到外籍人士時, 如果用漢名, 則華洋不分, 撲朔迷離。這樣, 中文報章只能淪為輔助讀物。要求真相, 必須還得經常閱讀英文報章! d. 香港有“麥當奴道”或稱“麥當勞道”。此“麥當勞”與快餐店的“麥當勞”是否同宗?通過英文才知道前者是 MacDonnell, 後者是 MacDonald, 兩者並非同宗。九龍有“彌敦道”。彌敦又是誰?他是一百年前的香港總督 M. Nathan, 中文近代史文獻裏有稱之為“那桑”、“納桑”的16。 e. 不少人為外籍人士“翻譯”姓名時, 凓重點在於“好”還是“不好”, 不理會“譯名”是否可以成為有效的語文工具。例如著名電影演員 Vivien Leigh 香港“譯名”為“慧雲李”。一般中文工具書不收“慧雲李”條。國內三四十年代以來, 一直“譯”成“費雯麗”。然而是否可以在中文工具書上找到呢?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icropaedia 收有 Leigh, Vivien 條。該百科全書兩岸都有譯本17。大陸書名《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 有關條目為“麗 Leigh, Vivien”。台灣書名《簡明大英百科全書》, 有關條目為“Leigh, Vivien 麗”。只會中文的讀者要在“麗”字下才能找到“費雯麗”。看來打開這本知識寶庫最方便的鑰匙仍然是英語! f. 譯名混亂當然也為學術研究帶來障礙。南京魯國堯先生, 為了“布文”一詞, 始則“百思不得其解”, 繼則“一日不解決, 一日心難安”, 後來查《中文大辭典》, 有“布國”、“布路斯”條, 才“恍然大悟:‘布文’者, 德文也!鬱積兩載, 一夕渙然冰釋, 浮一大白可也。”18 原來一百多年前,“德文”曾經寫成“布文”, 源自 Preussen (即英語 Prussia。魏源《海國圖志》上是“普魯社”, 後曾譯成“布路斯”, 後譯為“普魯士”。) g. 譯名混亂, 連上帝也不能置身事外, 但也無法解決。把 God 譯作“上帝”還是“神”, 是19世紀以來基督新教人士歷次重譯中文《聖經》的爭論重點。1987年, 基督教和天主教雙方再次討論合作翻譯統一的中文聖經。開始時, 天主教方面接受以“上帝”代替“天主”, 但後來天主教高層不同意, 理由是:“大家覺得有共同之聖經 ──《合一本》是好事, 但以《合一聖經》是為大家念的, 假如把聖經中的‘天主’全改為‘上帝’, 天主教教友在整部聖經中找不到天主, 那大有危險。”19 7. “基本法”裏的用詞 翻閱一下未來香港特區基本法的中英文本20, 也可發現英語語詞比較穩定, 中文語詞改變較多。試舉例列表如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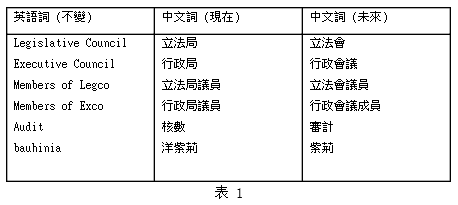 “紫荊樹之花。用以美兄弟之不分遺產也。(續齊諧記)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書言故事、兄弟類) 美兄弟不分者、用紫荊花。” 這是一個美麗的傳說。今人也有把此傳說誤套在 (洋) 紫荊名下的。這又是傳說的移花接木了。21 8. 香港法律翻譯 這裏再講幾句關於香港法律翻譯的話。香港法律源自英國法律。基本法第8條: “香港原有法律, 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 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 予以保留。” 香港原有法律以英文為準, 其實根本沒有整套的中文法例。十年前有關當局開始了香港法律翻譯的艱巨工作, 其間過程和問題可參閱古應佳先生最近的文章22。文章提到: “可惜由於中文常用詞彙不及英文的多, 往往是不敷應用的, 因此便要以創造新詞作為解決辦法之一。至今, 該科創造的新詞包括‘押記’(charge)、‘契諾’(covenant)、‘容受’(suffer)、‘信納’(satisfy)、‘管有’(possess) 等, 但願讀者他日讀到法例的真確中文本時, 能夠明白譯者的苦心。” 我們希望, 將來“法例的真確中文本”完成時, 同時也會有新詞的詳細注釋, 用中文說明什麼是“押記”、“契諾”、“容受”、“信納”、“管有”等。否則這些新詞恐怕不過是英語原詞的模糊代號而已!23 9. 人云亦云 香港曾經有人提倡“少做工夫, 多嘆世界”, 形成了人云亦云的風氣。港英的 New Territories 香港中文襲稱“新界”, 其實應稱為“新英占區”才對。香港近代歷史的標記為:1842年淪陷 (英佔) ── 1941年再淪陷 (日佔) ── 1945年續淪陷 (英再佔)。香港中文有把1945年的香港美之曰“重光”的!今年為抗戰勝利50周年, 香港中文有照抄日語名之為“shusen 終戰”50周年的, 也頗有些人說無所謂。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 香港有稱之為“大限”的。最近有一位老作家因有意外而見報, 某大報稱之為“老稿匠”, 頗引起一些作家、作者 (writer) 的不滿, 認為該報記者欠缺水平。我的看法是, 該記者寫的可能還是正宗的香港中文!香港警署內的案件紀錄滿紙本地俗語。案件紀錄裏如果出現“寫稿佬”等字眼絕不奇怪。這些才是可據以“為準”的香港法庭文字!香港傳播媒介, 滿紙、滿口都是“弗”、“睇真D”等等, 似乎沒有人對這些提出異議。好像還有人以香港有這類“新聞言論自由”而沾沾自喜。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接受社會用語反映社會生活這個事實, 那麼, 以上現象是否說明了:香港社會, 一般地平均地來說, 是一個多麼庸俗的社會? * * * 文章已經太長, 該是來個初步總結的時候了。“‘英文為準’和‘中文為準’”這個題目牽涉到語文的各個方面, 本文只涉及詞匯方面。這個題目也可從多個角度, 例如從翻譯的角度來觀察。但是文學翻譯者和法律翻譯者的基本態度可能也不一致。24 這個題目也涉及語文教學。老師常教學生寫“好文章”, 好文章是否也是“準確的文章”?這些問題這裏俱不及一一細論。香港以前是以“英文為準”, 希望將來能以“中文為準”。我說“希望”, 因為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首先要有一個觀念上的改變。中國人有望文生義的習慣, 有尚簡潔的習慣, 還經常根據愛惡, 任意命名、任意譯名、任意簡化、任意美化、任意醜化、任意誇大、任意“張冠李戴”, 玩弄各種文字遊戲。我常說,“簡化字”不是問題,“簡化詞”和“任意命名”才是大問題。杜詩“葵藿傾太陽”, 今人多注“葵”為“葵花”, 而“葵花”一般辭典釋為“向日葵”。但向日葵要到十六世紀才由新大陸傳入舊大陸。唐代中土何來向日葵呢?Esperanto 原義只是“希望者”, 中文把它誇大, 升格為“世界語”, 還稱之為“意譯詞”。Matthew Ridgway 既可寫成“李奇微”、“李奇危”, 又可寫成“里吉威”。“大猩猩”既可指 gorilla (產赤道非洲), 又可指大的“猩猩”(orang-utan, 產婆羅洲、蘇門答臘)。法國男士 Christian Dior 變成女性化的“姬仙蒂奧”, 撲朔迷離。 這個題目當然涉及“規範”問題。現在做“規範”工作的, 多是由上而下, 不大體諒民眾的苦衷。如果有人擁有《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而找不到“開士米”(見注17), 那不但是那人的損失, 也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損失。我常說, 中文版的“世界地圖”(指只有中文地名的) 最沒有用。同時也不能否認, 中文版“世界地圖”的編者們的確付出了極大的勞力。付出最大的勞力而得到最小的效果, 是不是最大的損失? 當缺乏適當的漢語詞彙時, 漢英雙語者不得不用英語 (或其他外語) 來思考, 這時譯詞只是模糊的代號而已。例如雙語者看到“共識”, 腦中就是以 consensus 為準, 看到“情意結”, 就想起 complex。以下再舉一些例子 (有 * 號者見上文): 傳意 communication 痛風 gout25 身份 identity 統整* integrate 互聯網絡 INTERNET 分享 share26 廣場 square, place, plaza27 品味 taste28 “以中文為準”的一種理想境界應該是腦海裏不用浮起任何外語。150年前的中國人可以這樣, 也只能這樣。將來的中國人在語文上仍然可以自給自足嗎? 後 記 朋友看完上文, 寫評語說:本文結論稍嫌灰色, 應該加些積極的步驟。我覺得積極的步驟首先應該是“多做工夫, 少嘆世界”。我們現在提倡“考今學”, 提倡要建立一種特別的“詞庫”來解決一詞多義, 一物多名, 譯名混亂 (等等) 的問題。通過這種詞庫, 既能從“山羊絨”找到它 (cashmere) 的釋義, 也可以從“開司米”、“開士米”、“茄士咩”找到它們 (= cashmere) 的釋義。有了這類基本語文建設工作作為基礎,“中文為準”就是扎實的“中文為準”。29 所謂基本“語文建設”, 也就是廣義的規範化工作。現在大家比較注重字形和字音, 談詞義詞源的較少。字形工作做得比較好, 起碼使人有跡可尋。新版的《新華字典》簡化字旁仍附有相對應的繁體字, 用者稱便。審音工作有需要改進的地方。舊字音給審掉後不再在新版《新華字典》中出現, 變成無蹤可尋。詞匯工作似乎還缺乏觀念上的突破。例如《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說:“‘社會主義’一詞, 大都認為起源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其實這是指 socialism 而言。漢字“社會主義”似首先在日本使用, 到1899年梁啟超才首次借用。 不少人非議中文夾用英文 (或其他外文)。我覺得用得適當也無可厚非。正如方程 x2 + 1=0 沒有實數解時, 引進虛數解 x=± i 就很方便。這已經是中學生的常識。同樣, 例如新西蘭有個城市叫“克賴斯特徹奇”, 反正沒有多少人懂, 就不如乾脆用 Christchurch。但是, 這就需要有一個觀念上的改變。 然而, 濫用外語或拉丁字母或其他符號究竟是不對的。1995年11月10日, 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致函全港中學校長、志願團體及機構, 宣布已與“亞洲電視”聯合製作了名為“基本法知多D”的電視節目, 並定於11月20日開始播出。不知道, 像“基本法知多D”這樣的“中文”, 是否就是香港公民應該用的中文, 是否就是香港校長、教師應該接受的中文? ─────────── 附注: 1.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0年4月。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1990。 2. 海恩波著, 簡又文譯,《傳教偉人馬禮遜》(M. Broomb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 1956, 1987。第8章。 3. 1995年來香港交流的北京少年發覺粵式“炸醬麵”不是他熟悉的炸醬麵。 4. 香港粵菜現在有“大蝦沙律”、“日式拼盤”等。 5. 徐世榮:《歲朝清供》,《文改之聲》第23期, 1994年1月1日。查1994年2月10日才是農曆正月元旦。 6. 古人也說“冬至-陽生”。宋朝詩人趙蕃甚至在秋天已在尋春了:“正是霜凝更雨濕, 春其漸起但無痕。莫嗟草色有垂死, 定有梅花當返魂。”(《雨後贈斯遠》) 7. 香港斤=0.605公斤, 參見香港政府度量衡十進制委員會“常用換算因數”表。參閱姚德懷:《‘市尺’、‘市斤’、‘市升’都是外來概念詞》,《詞庫建設通訊》, 第3期頁28-29, 1994年3月。 8. 嚴濟慈:《論公分公分公分》, 原載《東方雜誌》第32卷第3號, 頁79-82, 1935年。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編的《自然科學術語研究》1985年第1期 (即該會“成立大會專輯”) 頁57-59曾予轉載。題目中的三個“公分”實指 centimetre (厘米), gramme (克), deciare (10平方米)。 9. 徐通鏘,“加強‘字’的研究, 推進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語言文字應用》, 1995年第1期, 頁8-10。 10. 季羡林:《我和外國語言》, 上海:《外國語》, 1987年第1期 (總第47期), 第1頁。 11. 黃繼持:《‘散文’這名目》,《大公報》, 1994年8月3日, 香港。《詞庫建設通訊》第5期頁16-17 轉 載, 1994年12月, 香港。 12. 《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第三版 1984, 香港) 譯出席會議的“observer”為“觀察員”。按這本詞典的說法, 則學者甲並沒有錯! 13. 兩所大學的 Chancellor 必然是香港總督。 Chancellor 香港中文稱之為“校監”、“監督”。 14. 《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第三版 1984, 香港) reader 條:“2 (GB) university teacher of a rank immediately below a professor:(英) 階級低於教授的大學教師; 講師:R~ in English Literature. 英國文學講師。” 15. 參閱姚德懷:《外國人名地名的中譯問題》,《抖擻》創刊號, 1974年1月, 頁28-35。《語文建設通訊》第45期 (1994年9月) 頁8-12 部份轉載。 16. 見李恩涵著:《中英廣九鐵路路權交涉》, 原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期, 1972年, 頁139-172。該文收入作者《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2年, 頁392-437。該文第二節稱 Nathan 為“那桑”, 第三節又稱之為“納桑”。可知兩者只不過是模糊的代號而已。該文第一節有一句話值得我們警惕:一百年前我國在外債築路諸合同中,“由於合同中文字措辭的籠統含混, 使我國常常遭受到許多意外的損失。”但是這句話本身也有語病。它是指合同裏的“文字”呢, 還是指合同裏的“中文字”呢? 17.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icropaedia, 美國 1974。大陸編譯本《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5年。台灣中華書局在取得原書出版社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同意後, 在1988年出版編譯本《簡明大英百科全書》。同一百科全書, 現分兩中文版、兩名稱、兩字體、兩“中國特色”。台灣版的“中國”仍包括“外蒙古”。 這裏再舉一個例子。如要找“茄士咩”或“開士米”或“開司米”, 在上述中文版百科全書裏是找不到的。必須查“山羊絨”或 cashmere 才能找到。也許百科全書的編譯者只收規範詞“山羊絨”。但是這樣就苦了不知規範名的老百姓。中國的老百姓一般怕查詞典等工具書, 這是一個原因。 18. 魯國堯:《‘布文’辨識本末及其他》,《中國語文通訊》第29期, 1994年3月, 香港, 頁21-25。 19. 趙維本:《譯經溯源 ── 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1993。 20. 同注1。 21. 參閱《詞庫建設通訊》第3期, 香港1994年3月,“植物名稱庫”詞條選刊 (2)“Bauhinia blakeana Dunn 洋紫荊”條和“Cercis chinensis 紫荊”條。我曾建議改稱“洋紫荊”為“香港紫荊”, 但不得把它簡化為“紫荊”。 22. 古應佳:《香港法律翻譯工程艱巨》、《香港法律翻譯人才難求》兩文, 載香港《信報》, 1995年11月8日、9日。 23. 1995年香港政府出版了《英漢法律詞彙》(第一卷)。由英文詞彙可查到中文詞彙。例:由 charge 可查到“押記”。但由“押記”難於找到 charge。香港政府副法律草擬專員黃薇薇談到:部分法律界人士批評《詞彙》內對法律用詞的翻譯過分書面化, 難以在日常生活或法庭審詞中使用。她則認為一切也是習慣問題。見1995年11月11日《明報》專訪:“黃薇薇對法例全中譯胸有成竹”。 24. 思果先生有一篇自己文章的譯述, 題為《翻譯歐化結構探討》, 刊《中國語文通訊》第29期, 1994年3月, 香港, 頁43-47。這個題目不好懂。看了原來的英文題目, Europeanized Structure in Translation, 就明白了。漢譯把 in 這虛詞省略了。其實“虛詞”十分重要。“虛詞”用“虛”也是誤導。如無虛詞, 何來結構? 25. “痛風”(gout) 病症早已為人所知。但是中文“痛風”, 常使人“顧名思義”, 以為與“風濕”有關。其實毫無關係。 26. 香港中文:不管“快樂”或“痛苦”或其他, 都能“分享”。這裏“分享”只是 share 的代號。 27. 參閱姚德懷:《也談‘廣場’》,《中國語文通訊》, 第26期, 1993年6月, 香港, 頁51-52。 28. 楊振寧曾說:“一個做學問的人, 除了學習知識外, 還要有‘taste’, 這個詞不太好翻, 有的翻譯成品味、喜愛。一個人要有大的成就, 就要有相當清楚的 taste。”見“楊振寧談治學之道”, 原載上海《文匯報》, 1995年8月10日香港《大公報》轉載。 29. 參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刊物《詞庫建設通訊》(1993年創刊, 現出至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