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载于《哲学门》总第三十一辑(2015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作者丁耘和《哲学门》授权刊发。 文 | 丁耘 陈来先生的新著《仁学本体论》可说是我国本世纪出现的第一部纯粹哲学作品。陈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及中国思想史多年,著作等身,学界对他的研究路数和学术风格应该说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此书出版,足以新人耳目。我作为陈先生旧著的受惠者,拜读之下,且惊且喜。惊喜之余,更欲对此书之意涵,有所申论。以下从内外两层分说。  《仁学本体论》 陈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6 外在方面,指此书的取向、进路对于当前中国思想及中国“哲学”大势的意义。内在方面,则涉及此书的具体立论。内外当然无可分裂。一般而言,书的内在方面更重要一些。不过轻重缓急,端赖时势。斯时斯地,此书之外在意义格外值得重视。 陈先生的治学,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属于“中国哲学史”这门“二级学科”。同时也可算作广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近年兴起的“国学”特别是“儒学”潮流,对陈先生的全部著述,当然也要参究引述。因此,陈先生的学术工作,可谓交汇、牵动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儒学”等多重学术思想脉络。 不过,《仁学本体论》在其意图和效果上,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部陈著。打个比方,旧著大体是在冯友兰先生几种《中国哲学史》的工作范围内展开。即令颇树己义,也不过是老田地里养出了新花果。《仁学本体论》则更接近冯先生的《贞元六书》,属于体系性的贡献。如今冯、陈格局大略相似,但入路乃有差别。冯先生的入路是从哲学到哲学史。陈先生反之,是从哲学史到哲学。 冯先生其实是以《六书》尤其《新理学》为本,整理哲学史的。哲学史是解释历史上所发生的哲学。解释中最重要的不是材料,而是处理材料时所依的哲学见地。冯先生几种《中国哲学史》之见地,根子在其体系。而其能入哲学(非哲学史)之门,契机在于学习形式逻辑时顿悟概念之纯粹性(对此冯有回忆)。 陈先生则不同。他最早的学术贡献,是对朱子书信编年的考证。其史学工夫之强,足以掩盖其概念分析的能力。其实,无论治晦庵、阳明、船山还是先秦简帛,均非单纯的考证爬梳即能胜任的,还须同时糅合概念分析与生命体会的方法。而陈先生的著作虽有思辨与体会的方法论底色,却仍以史学论著的面目出现。甚至在这部纯粹哲学论著中仍然如此。陈先生在哲学史研究中,淡化概念论证、强化历史叙述的方法,原是他力图摆脱冯友兰哲学先行的哲学史工作方式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有效的,也是有影响的。但在纯粹哲学的构建中,明确提出史学叙述而非概念论证是“必须”的(参见《仁学本体论》第23-25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或仍属空谷足音。 不能仅从方法论的转向去理解作者对历史叙述的强调。陈先生其实提出了另一种哲学观:非概念中心的哲学非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中国哲学”有史以来的正统。此正统非但可以回应,而且可以化解概念中心的哲学形态。 因之,从哲学史到哲学,在陈先生并不是断裂性的进展。而哲学史研究对其哲学研究的影响,也不象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说得彻底些,并不是哲学史研究影响了哲学,甚至也不是浸淫哲学史的多年积累让作者在哲学创建时能自如地调动各种资源。《仁学本体论》的大意义在于,陈先生是把在其哲学史工作中本来就内蕴或随之成熟的“哲学史的哲学”自然延伸到了纯粹哲学的王国。如果说冯友兰先生的几种《中国哲学史》是“哲学化的哲学史”,那么《仁学本体论》可谓创建了“哲学史化的哲学”。两者虽然都是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但其风味与底蕴则有所不同。冯先生的著作,风味的中国性重于其底蕴的中国性。陈先生则反之。《仁学本体论》的发心,就是接住李泽厚抛出的问题(“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探索具有真正中国性的哲学(参见第501页)。此著的方法论,是隶属于中国性及其主旨(仁体)的。 这里,我将通过历史叙述进行哲思的一系哲学,称为“叙述的哲学”;将以概念说理为主轴建立的哲学,称为“概念的哲学”。“概念的哲学”包括分析哲学,但也包括以其它的方式进行概念思考的哲学。例如,熊十力、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也是典型的“概念哲学”。而李泽厚、牟宗三、唐君毅的哲学,则多少算“叙述的哲学”。西方哲学则大多是概念哲学。也有不少哲学家是以叙述带出概念的。 《仁学本体论》的出现表明,哲学仍可被选择为中国思想的恰当形态。李泽厚的时代过去之后,随着中国学界风气和格局的变化,中国哲学可谓命悬一线,不绝如缕。其原因大体有三: 第一,由于哲学鲜明的西学渊源,对中国哲学自身“合法性”的质疑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而是以新的形态潜藏了下来。 第二,近年来,儒学复兴运动实已进入了经学乃至儒教复兴阶段。经学传统及理学的工夫论传统同样质疑将传统学术思想“哲学化”的现代学科建制。 第三,由于当前西方哲学格局的变化,即使中国思想保有“哲学化”的余地,局面与出路仍颇复杂。 “哲学”云云,当前大体已分三途。一为逐渐坐大之分析派。此派小智间间,别无他技,唯将科学方法中最初步浅显者用于哲学。故论理细密而套路简单,虽器狭才庸,亦可入门。易学易用,浸浸然遂为大派。此派对哲学史文本,中如孟子,西如柏拉图,均以彼派之格套,还原为论证而后加以绳墨。其中不能论证化者,一概斥为“非哲学”。又一为逐渐式微之欧陆派。此派原本高明丰富。亦即立意高远、立论多方,善于将非概念的东西(历史、现象、生命、体验、情感、意志、政治等等)概念化。而高明难继,丰富难择,遂后学凋零。前后两派,不无分河饮水之势。后一派又衍出政治哲学一支,对哲学之显,有所限制。此三派对中国思想之哲学化,都有各自方案。分析派与政治派均有落入窠臼格套趋势,其“哲学化”实新经院化。欧陆派之总问题源自西方哲学之正统(本体论、形而上学)。其具体学说虽多有可采,而其总问题则与中国思想尚隔一间。[1] 在这样的形势下,《仁学本体论》的出现表明,中国哲学毕竟迈出了方向性的一步。这是续中国哲学慧命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中国哲学的道路要么踏上歧途,要么逐渐掩没在时代杂草之中。 《仁学本体论》以自立学统、自做主宰的方式不言而喻地回应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这个方式可以同时回应中国哲学界内部的质疑与来自经学复兴运动的质疑。 合法来自“正统”。建立传统就是建立合法性。需要争辩的合法性已经是第二义的。从不被争辩、而在争辩时被默默当作背景的合法性才是第一义的。背景就是正统,就是最原始、最广大的共识。建立正统依靠的不是“论证”(因为论证就带入了争辩的可能性),而是“历史叙述”。在这种哲学中,最彻底的批评不是激烈争辩,而是不齿、不提及,也就是不列入正统。[2]“叙述”本是源自“经学”的方式(在西学那里是诗、神话与法典的方式)。陈先生是以经学的方式回应了中国学术只属于经学、不属于哲学的质疑。在陈先生建立的儒学正统里,他是接着朱子、熊十力、梁漱溟、和李泽厚叙述中国之道的。这在首章“明体第一”中昭然可见。冯友兰则在此章末尾被判为非儒家的中国哲学。 同时,陈先生对西方哲学的传统仍有所回应。这些回应似乎零散即兴,但关键处都点到了,其格局是全面的。在对西方哲学多有回遮、吸纳的同时,陈著最重要的一个表态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存在”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是误入歧途的。这就将中国思想“哲学化”在当前涉及的麻烦都清理了一遍。 把大而化之的古今中西问题聚集、收拢在经学、理学与哲学之间。不仅主张,而且推进了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不仅让中国哲学包摄了西方哲学的一些重要学说,而且把这些学说纳入一种更为本源的思考中,从而更新了哲学本身的形态。所有这些,大概就是《仁学本体论》最大的外在意义。 外在意义是自其内核焕发的。《仁学本体论》的立意,是要把仁体演为宇宙的本体、道学的正脉、普遍的价值基础。按叙述哲学的方法,前两个意图可合并实现。全书正文凡十二章。前十一章贯彻了前两个意图。终章用力于第三个意图。 《仁学本体论》的思想来源丰富,而统绪清晰。渊源虽富,并不碍作者折中损益、取舍进退。简单地说,《仁学本体论》的基本作法是在分头推进的基础上,一方面综合了熊十力的宇宙论和李泽厚的情本体论[3],另一方面将这种综合直接追溯到朱子之仁学(参见第38-47页)。这种综合是创造性的;这种追溯以及推进(参见第215页)则表明,这种创造性并非一己才力的表现,而是符合正统的。此综合他人或者可及,此追溯当世非陈来不办[4]。 陈先生的直接发心是把李氏的情本体从其心理学、文化学的人本主义背景下解脱出来(参见第501、502页),提到熊氏宇宙本体的境地中考量。李氏情本体说的弱点是担当不起宇宙化生的大用,故情本体充其量是心体,并非真的“本体”。熊氏本体说发明《大易》生生之理甚明,而其障在于偏说成物势用(一翕一辟),未从仁德体会生生之理,故所立终非仁体。陈著俾二子相济,唯以仁德大用逆证生生之体实即仁体。此的是明道血脉,而提至晦庵格局矣。依识仁血脉正熊氏之偏,凭宇宙格局充李氏之狭[5],是陈氏之学也。 陈著用力,本在体用之间。述用易,明体难,即用明体尤难。清通晓畅,素为陈著之长。此书则不乏深邃繁细,偶有未臻圆熟,多在论体处,不得不然。近儒论体用,无出熊十力之右者,故陈著纠熊处较拓李处尤费周章。熊学一脉,传至境外,多依西学(康德及怀特海等)立论。故陈著又不得不旁通西学,为化解康德,前追斯宾诺莎,后引海德格尔及现代犹太诸哲。用心良苦,援奥良多,而理脉丝毫不乱:引海德格尔等,为摄用;述斯宾诺莎,为定体[6]。 限于篇幅,本文且就体用及仁体等,略做评点。 第一条,关于本体、实体、主体、体用之体。 “体”“用”论式,虽可远溯至汉代道教(魏伯阳)、魏晋玄学(王弼),而其大成,当在隋唐佛学。佛家多“体”“用”“性”“相”并举。或说“体性”,以对“相用”。佛家重“性、相”,理学重“体、用”。而彼此又非全不相涉。朱子批评佛家“作用是性”,欧阳竟无以“体用”圆满并摄孔佛。是“体用”亦可用于佛学,“性相”亦可用于理学。本、体,对末、用而言,道、体,对器、用而言。道器本末始终之对,源自先秦原典。而合道、体、本,齐器、用、末,则是后世踵事增华。实体、实学,是理学为辟佛,强调此体本非虚空。本体对工夫,参入心性,是理学修证语。以上是中国学术史之固有涵义。 洎乎西学东渐,体用之义渐迁。张文襄说“中西体用”,庶几仍可入旧义。严几道驳以“牛马体用”,是误形器为体、功能为用,已与宋学不合。虽汉唐古注,亦偶见以“体”为“形体”,而此非张之原意可知。西方哲学典籍大量汉译之后,本体、实体之意更转繁复。大体先是以中格西,将ousia、substance、onta等一系列源于古希腊哲学对“存有”之主词化解释之西方哲学基本概念,译为“体”。但这些“体”均不与“用”“器”“末”“相”“工夫”相对,而是与“属性”“样态”“思维”“真理”“现象”等相对。 名相译释,非同小可。自此一变,本为以中格西产物之“实体”“本体”等回过头来入室操戈、代西格中,全盘换了问题,反以“体用”之“体”、“道器”之“道”问的即是“存有”“主词”“基础”。种种紊乱,因此而生。而此种紊乱,又非单纯纠正解释可解。此间涉及中西思想各自脉络的本源性问题。西方哲学之“实体”,本源自陈著自始即排斥之“存有”问题。而陈著所之赞许苏格拉底之“善”(参见第74页),亦绝非与“存有”问题毫不相涉。西学中作为宇宙原理之“善”,不可能缺少“存有”而成立。故引“实体”入儒学成立仁学的体用论,当对存有问题有所化解,而非仅判为歧途便可了事。 陈著化用斯宾诺莎之实体说,为接续熊十力,立本体兼摄心、物。此法固妙,在陈氏亦非权宜,然立此超越道体,或亦可有他方,不必牵涉西学(详见下文诸条)。而援斯入儒,亦带入其系统之固有问题,亦有其他牵扯,不得久立。 熊门后学如牟宗三等,本援康入儒,其弊在以心统天。牟遂跳出朱陆,据明道一脉极力浚通心体性体,盖有所憾也。康德费希特之后,德国哲学亦有此憾,故亦有斯宾诺莎主义之复兴。其“实体”固超越心、物,而非康德“实体”范畴所能笼罩。而斯氏“实体”之门,亦从“自然”可入,乃至“除自然外没有上帝”。然此亦非了局。逮黑格尔出,以“不仅将真理理解与表述为实体,而且也理解与表述为主体”统摄康费与斯氏。 揆诸陈意,当以牟氏为康德主义或曰主体主义的新儒家,则陈氏无疑为斯宾诺莎主义或实体主义的新儒家。陈著抨击主体主义儒家甚力,如将甘泉、阳明之争归为实体与主体之争(参见第205-206、页)。若陈氏只说“实体”,当仅为斯宾诺莎主义。议者如径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批评,彼未必领受。而作者今并举“实体”“主体”,则当已接受黑格尔之判教。既已接受黑格尔,则不得不接受黑格尔对斯宾诺莎之了断:绝对【“道体”“全体”】不落实体、主体二边。实体主义之新儒家必被“绝对主义”所扬弃。如作者以为,斯宾诺莎之“实体”既已超越“心”“物”,其实已含主体,当是“绝对”,则作者实如众多学者,误解黑格尔之“主体”概念。此主体决非实指“思维”或“心”,而是“思维”的原理——“活动性”。这概念表面来自费希特,其实来自亚里斯多德。相反,阳明学归诸“心”之当下呈现(在黑格尔那里叫做“直接性”)原理,黑格尔则归诸“实体”。黑格尔之主体性,与“心”之关系,远不如与“生生”之关系密切。和亚里斯多德一样,黑格尔哲学关涉的是体用问题,而绝非“心”“物”或“心”“性”问题。心体与性体都可以或是“实体”,或是“主体”。 对理学而言,既没有独立于体用问题之外的心物问题,也不可误于译名,将“体用”问题误为“实体”“样态”。斯宾诺莎以及一切摆脱心学思考神学的西方哲学的症结所在,就是体用二分,断为两橛。论及体用,陈先生一如牟宗三,尊怀特海。而西哲论体用,无出亚里斯多德与黑格尔之右者。可惜陈先生与黑格尔失之交臂,犹如牟早年错失亚里斯多德一样。 第二条,“体”“用”之间。 摄用定体之旨,在理学当为“体用不二、显微无间”。如何证其“不二”?古人首重默识、工夫。今人则不得不主说道理。熊氏借华严宗“大海沤”之喻,发挥大易生生之理[7]。牟氏承其师说,变其名相,乃以“即活动即存有”为基本架构。此架构可溯至亚里斯多德[8]。熊牟之说,实可贯通,要之基础存有(实体)不离活动而在,本体不离显现而有[9]。 陈著亦推进熊说,然不取刹那不息意[10],唯取包摄心、物意。陈著以仁说生生,固比熊借刹那说为正。然陈又借朱子立仁体。仁在朱子只是一气流行,非体上事。而陈说仁体,以理、气为用。如只在气上说流行,则仁只是用,不是体。如立仁为体,实当在体上说流行。则或从气本论,或依熊牟解。陈著只说“实体必有流行发用”(第225页),此一“必”字,如何成立?迄无演证。斯宾诺莎如真能有此一“必”,不待黑格尔批判矣。不依熊牟,立体用不二,流行主宰不二,须得在体上说气。故明儒多立气本,以为性体。蕺山以气摄心,船山以气摄理,皆是明证。而陈著引朱子后,续引明儒中王门弟子(参见第64页),似乎两下无间。是陈先生仍立朱子门墙下,不欲人说其发皇气论欤? 体用论难立,难在极易断为两橛。离活动建立之实体,是“基础”。离显现建立之本体,是“本质”,皆离用之体也。如欲破体用二分,须立二旨:实体不离活动而在、本体不离显现而有。西方哲学中,黑格尔辩证法建立前理,兼摄后理。现象学成立后理。二宗皆可溯至亚里斯多德,然后知活动就是显现、实体就是心体。中国思想中,破体用二分,门径尤多。佛家及心学传统中,在在皆是。心物、心理、理气、知行、天人,不是不可说,要在当摄于体用论下,从体用不二看,面目自然不同。 体用之学,可分四支。有即用见体之学,有据体演用之学。有见体而后据之演用(诚则明矣),有演用而后即之见体(明则诚矣)。后二支乃圆转为全体大用矣。古今之学,多前二支。儒家之用,要在心、气。佛道两家,研幾虑深,转为念、息。姑置勿论。 气是仁体由天向人发用,由上而下。心是仁体由人向天发用,由下而上。前者鱼跃在渊,后者鸢飞戾天,上下察也。体之大用,唯定在心,此孟学正脉(详见第四条)[11]。仁体发用,在恻隐之心。恻隐是仁之“端倪”,即仁体之显现。在心性上说,体用不二。在工夫上说,知行合一。就仁体说,不可离仁之显现识仁。离仁之显现,就是不仁(无知觉),不仁其实无仁。欲仁而仁至。仁就在这个“欲”上有,而不在对“仁”字之考释、了别、思辨上有[12]。此是从仁体说。从宇宙本体说,天地是乾坤之体,乾坤是天地之用。乾即健,坤即顺。即用定体,不健非天,不流非川。非先有个昭昭之天,而后发现它一直“行健”,才是不已之天。天就是“行健”名词化、主词化了。凡行健必是天。人能行健,亦是天德。此理西哲以火燃、河流、日照、目视、心思等喻出之。火即是燃,日即是照。非先有个太阳,而后发现它也能照亮发热。川不舍昼夜,道行之而成。先从流行,方能见道。即此大用,方能定体。 悟性到处,即用定体。义理熟时,据体演用。顿悟本体,先于演证名相,方是真儒学。否则只是戏论(概念游戏、思辨哲学)。近人之中,熊梁即用定体,引人观道。金冯据体演用,空口论道。如金岳霖劈头即说“道曰势、曰能”。冯友兰先从“逻辑”上造出“大全”概念[13],而后独断地(即“形而上学”地)说它“也”是流行不已的[14]。诚如黑格尔所云,哲学就是要破除这个“也”。熊梁或仅望道而未之见,而金冯实不知有望道一事。陈著大处用熊、排冯,吃紧处似仍未脱冯学气味。因工夫论史料揣摩极熟,故较冯为优,能在大处用熊而不为所缚。而其纠熊时,暗袭冯学。详下。 第三条,翕、辟、动、静与存有问题。 陈著以仁体纠熊之生生本体。生生原即仁体,而熊以不息、不已,而非以仁之发用揭明此体。体用不二,熊既未由仁入体,故其生生本体在陈即有所偏。即有取于生重,有取于成轻;有取于元重,有取于贞轻;变动迁流意重,收摄保合意轻。在熊氏,一翕一辟之间,辟为主,翕为次。此虽《易》语,而熊实以佛家刹那说贯通《大易》变易说而建立。陈著先破刹那说,后纠翕辟说。前多引西哲,发挥连续性之理。后多引理学,以为翕辟之间,当以翕为主。而仁之为宇宙原理,相当于稳定、同一、存有,故翕与仁合。 陈纠熊翕辟说处,丝毫未及冯学。然陈之纠熊,与晚年冯友兰以“仇必和而解”商兑毛泽东“仇必仇到底”之绝对变动观,实出同一意趣。翕、辟、仇、和,都既是宇宙本体,又摄历史现象。辟于唯物辩证法,相当于运动、斗争;翕相当于静止、同一。于历史唯物论,辟相当于革命、阶级斗争,翕相当于仁政、阶级和解。以翕为主,即以静为主。以翕为仁,即以和谐为政。此的是袭冯之处,而运用高明。冯氏用“静”“和”,仍囿于唯物辩证法藩篱。陈氏说翕、仁,则主说宇宙,更独标仁,直续理学正脉矣。西哲本源自存有问题,陈著虽判为歧途,而翕辟动静,实通存有/变易问题。总熊冯陈而论之,可谓熊主变易(生生、辟),冯主存有(终极、“底”、理)。陈阳用熊学,阴袭冯学。主存有而名之为翕。陈之转熊学,用依李(情感),而体实有取于冯(收聚、静止)。 西学于变易,定之以存有、实体等。苏格拉底定之以善。陈摄翕归仁,与苏氏通。宜其对苏氏青眼有加矣。而苏氏以一切知识围绕“善”,生活优劣,决于对善持臆见,抑或真知。而此知是思想、理智事。陈虽于知行有间(如论明道处追问:“什么是仁”),特因孟子、明道一脉,终不昧于西学,决定了然“识仁”“明善”不在界说,而在存心、尽心矣。要言之,变易流转,陈以为当定之以仁。故实体于工夫言,即至善心体、本体;仁体于存有问题言,即实体、本体。此一路向,陈仅点到为止,及其至也,似可包摄中西而周圆无碍矣。然陈于熊氏翕辟说下转语处,窃以为义有未安。容略说之。 熊十力翕辟之说,本以衍乾坤大义,以辟说乾,以翕说坤。此盖已乱《易》语。《繋辞》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是翕辟皆坤元之德。而“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揆熊之意,当云阖辟,而非翕辟。熊云翕辟,实即阖辟,亦即乾坤,要之主变也。变易非不干存有,而是否定(“辟”)存有。如以“变”否定存有,逻辑上必当后于存有,此即落黑格尔逻辑学。然在此逻辑学,后起者必是在先者之真理[15]。论先后,有先于变。论轻重,变重于有。《易》固以为乾尊坤卑。且非以逻辑秩序排诸卦象,故乾元亦居首。变易之中,以辟为主,以翕为次,即以乾、阳为主,以坤、阴为次也。易固有三义,然变易先于不易。神无方而易无体,不容实体据变易之外、变易之上,此固《易》理也。 而陈攻熊云,当以翕为主、辟为次。谓逻辑上亦当先有所翕,方有所辟,故翕当为主,辟当为次(参见第67页)。此逻辑非《易》之逻辑,亦非黑格尔之逻辑。盖于黑格尔,先后实不与主次相应。陈著之翕辟说,实以存有为主,变易为次[16]。此是冯学,非易学也。以冯学攻熊学可,以之为易学而攻熊学则不可。而陈著雅不欲绍继冯学,于存有、变易语焉而不详,唯以张大仁体为务。以仁释翕,乃云以翕为主,即以仁为主也。此释于陈著之内,已不周延[17],恐亦非《易》之本意。《繋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李道平疏曰,“仁者偏于阳,见阳之息谓之仁,故仁者观道,谓道为仁。知者偏于阴,见阴之藏谓之知。故知者观道,谓道为知也。”[18]李疏虽本虞翻,而此处可与王注孔疏相通。“辟户谓之乾”,王弼注曰:“乾道施生”。孔颖达疏曰:“辟户,曰吐生万物也,若室之开辟其户……”。孔疏《乾.文言》引庄氏云:“‘元者善之长者’,……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为施生之宗”。又疏“乾元亨利贞”,引《子夏易传》云“元,始也。”故辟、开、元、始通,为施生、始生之意。“元者善之长也”,《乾·文言》自释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孔疏曰:“施于王事言之,元则仁也……”是辟翕之间,辟属乾而有始生之意,仁也。仁意本始生开辟,扩充推演之后,方包摄终成收聚。此意陈著所引《朱子语类》甚明:“仁义如阴阳,只是一气。阳是正长底气,阴是方消底气;仁便是方生底义,义便是收回头底仁。”(第214页)。故经学、理学传统中,开辟、始生属仁,翕阖、终成属义或知甚明。如张大仁德,则礼义知信均是仁,翕阖终成亦可繋于仁。而此是发皇之语,已落第二义。开辟乃仁之原意,不可掩也。陈著据理学史,将仁之始终二义,归为“生生之仁”“一体之仁”,而翕、辟俱摄其下。此固有本。然而正因如此,不宜在翕辟之间,复为抑扬。果欲抑扬,当随周家之《易》,扬乾始生之辟,抑坤终成之翕。何以故?生生为元、为本,无生生即无一体。生生开辟肇始、越自通他,感通所止,乃有不为形骸所限之一体。 陈著于经学、理学虽熟极而流,而不甚囿于家法,于朱子乃至五经,皆有所月旦。[19]故陈著能以“哲学”再释经典,得失功罪,恐皆在此。陈云翕是聚合、辟是离散、乾主生等,尚见古意;云翕是关联、辟是消耗及个体化、坤主爱,则是以“现代哲学”阐发经之旧辞矣。此等运用,盖包含极严肃之意图,不可轻诋。如力守旧义,论不破经,固是理学旧业。即令颇按新调,当非浮泛,而亦有所指。如以辟为个体化,以翕为一体化而归之于仁,此固是宇宙论层面事,意在以仁纠正个体主义之价值论。然据旧籍原义,亦可另作“哲学”阐发。辟是超克、敞开、自身超越,而翕是建立界限、止于自身之内。此如用于思考存有乃至价值问题,当别有所见,兹不赘。 第四条,心学与仁体。 陈著最醒目之贡献,在跳出心学理学、理本气本之争,以超越仁体统摄心物、理气,将中国哲学史上这些“本体”尽数黜为仁体之用。开此生面,自是大宗匠手笔。 陈非但欲跳出理学(理气之争),且欲跳出西方哲学东来后之基本争论(唯物唯心之争)。其筚路蓝缕之功,当属熊氏。熊学主旨,乃以体用论跳出理学(其门弟子皆属此列);而以实体兼摄心物者,是熊氏以其余力回应西学,此为其门人所未及者。然心物之对,虽出自《大学》,且列入阳明学公案,按诸儒学统绪,允非心学基本问题。朱陆之心、理,二程之心、天,孟子之心、性、天,均为心学传统所涉之大问题。心物问题,隶属于其下。遑论西方哲学基本问题,非中文字面之唯物、唯心可尽。陈著黜心为用,固有得于熊氏。然非欲回应西学,而欲以跳出心学、理学之争。黜心为用,指仁为体。则心亦为仁体之流行发用耳,一如理气等。 体用之学,可简别为四,已见于上文。据此观之,心学偏即用见体,理学偏据体演用。气学两可。养气、观生观复,则前支。论气、说虚说象,则后支。孟前诸子,多即用见体[20]。周张之后,多据体演用。明道、象山、阳明,复孟之学也。至于群经,多即用见体。《易》《庸》体用圆满、诚明相倚,是后二支之学。 按此统绪判之,陈著本意,在体用圆满。即依熊氏即用所见之体,而后据而演之。唯熊以生生为全体、不息为大用,海水为全体,海沤为大用。是全体大用而又体用不二。而陈以仁体为全体,心、物、理、气俱各为用。是有全体,无大用,而体用不必无二矣。下分大用、全体而略说之。 先说大用。心学无他,以心为大用,心体为全体尔。以心体为全体,固是心宗之偏。而以心为大用、即心见体,则的是孟学精义、明道阳明血脉矣。孟子之于性、天,唯凭四心,单刀直入。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则四心非大用而何?宗孟者即此大用而见全体,无非尽心而已矣[21]。明道识得仁体,是尽了恻隐之心。阳明识得明觉,是尽了是非之心。明道见仁,阳明见知。四心在孟子似无分轩轾,而明道唯尽恻隐之心以识仁,盖有以矣。以仁体为性为天,虽不中,亦不远矣。以明觉为性,恐近佛性。以明觉为天,则偏甚。诸卦中乾卦为大,乾德中元德据首。乾者,天也。乾之元,仁也。立仁知天,孟学也,亦固易理也。明道《识仁》《定性》,贯通《易》《孟》之学。乾元四德,元亨利贞,《文言》配仁义礼信,固未及“知”。而《定性书》引孟子恶智之凿语,又以定者必“以明觉为自然”。是明道有深造于知者之学而遗之也。仁者通,通者内外两忘(去内外,即“辟”义之一)。而“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22]。兴于恻隐之心、以仁为己任者,必自然而明。兴于是非之心、省察克治、以明觉为务者,明觉可得,以明觉为自然不可得。以心之灵明仰天之高可得[23],尽此灵明以知天之生生仁体不可得。故阳明学纠葛之多,远甚于明道学。阳明宗有弊,在不尽恻隐之心以知性知天[24]。经明道淘洗,全体大用在心,心之大端在恻隐,乃卓然不可掩之孟子精义。 阳明宗有弊,明道、孟子何辜?乃朱子则并明道而远之。朱子攻《识仁》,因明道隐去所即之用,单说见体效验。此篇隐去其用,非明道之学凭空见体耳。明道本从恻隐之心、天地生气入仁体。明道观天地生气,是观其生意、仁德,仍是天地之恻隐。故明道学所即之用,以心为主。陈著以仁为全体,自是明道遗意。而以宇宙论接引此仁体,故尚理气。此欲以朱子之用,接明道之体耳。两下所合者,唯一气耳。故陈著黜心学甚力。黜心学,非仅黜陆王也,必黜孟子。黜孟子,全体之大用不依四心,则儒家工夫难立。工夫不立,说仁统诸德,难有着落。 再说全体。儒家论体之典,高明圆满,不过《易》、《庸》。《庸》以“诚”为体。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又“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原即“信”(《说文》诚信互训)。于乾元四德,信配贞,仁配元。乾元统此四德,遥应坤元。《中庸》诚学及陈著仁学,皆张大乾元四德之一,而为全体之指。“诚”之原意,只是“贞成”。而《中庸》亦赋“不息不殆”之意(“至诚无息”)。不息不殆,原属“生生”。《易》以生摄成,《庸》以成摄生,皆生成全体也,不落一边。 元亨利贞,仁本配元,于四时配春。如以始生为全体,则秋冬之肃杀零落闭藏,在全体之内否?故以仁为全体,为《易》所不许。欲立仁为宇宙之单独原理,必赋它意,犹“诚”亦当禀“生生不息”之意。全体之全,须于一正一反现之。故《易》立乾坤二元,又说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熊氏以一翕一辟说全体,亦是此理。以仁为全体,当将非仁(义礼智信)乃至不仁[25],统合、涵摄于全体之下。 仁者之学,在《易》即非全体之学。《繋辞》论道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此论极微妙曲折。可与《庸》相参,两处皆论君子之道焉:“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庸》云费而隐,《易》云显而藏;《庸》云微之显、诚不可掩,《易》云显诸仁;《庸》云夫妇之愚可以与知,《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庸》云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易》云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庸》之诚体,广大精微。虽精微,而不可掩,愚夫妇可知。虽不可掩,天地莫之能载,故圣人难知。《易》《庸》大同处显豁如此,小异处则更堪玩味。 《易》于《庸》意,必云“诚者见之谓之诚。”《庸》于《易》意,必云“仁之不可掩,如此夫。”而毕竟《易》自《易》、《庸》自《庸》。《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隐微者尽现于诚矣。《庸》固云道大,圣人有所不知,而“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圣人不知者,因道之大(“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非因道之隐。大至无穷、不测,亦可一言而蔽之曰“诚”。虽圣人难知,道无非诚体。而《易》云道体“显诸仁”,非显者即仁也(如同《庸》言,当云“仁之不可掩也如此”)。既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则全体自非仁可以尽。又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此非因其大,乃因其隐,非仁心可揣摩忖度。道“显诸仁”者,仁为全体之大用,依仁可优入道体,非仁即道体也。 陈著以心、物、理、气为仁体之用,而于诸用等量齐观。《易》则以仁、知为道体之用。而诸用之中,以仁为其皇皇大者,一超直上,优入道境,顿现全体。是道体有生生之仁,而不拘于生生。有成性之知,而不限于成性。全体对大用而言为“无限”,此方是斯宾诺莎之奥义[26]。于《易》,唯仁可当全体之大用耳。仅由仁窥体,此体可强名曰仁体。此体是仁体而超仁体者也。故《易》之为学,即仁见全体也,仁而超仁者也。仁者之学,固为《易》所许。而以仁体为全体,非《易》所许也。陈公大著,允为仁者之学也。 注释 [1] 此一间是否仅如陈著所云:存有问题是误入歧途,则可再商量。 [2] 注意《仁学本体论》对牟宗三思想的沉默。 [3] “后期熊十力的体用论与后期李泽厚的情本体论是我们正面面对的中国现代哲学本体论的主要场景,对此两者本体论的反应与回应构成了我们的仁体论建构最初的基本思路。”陈来,《仁学本体论》,第62页。 [4] 既有此一溯,牟宗三必不能得位于此书矣。 [5] “对李泽厚的情本体哲学下一转语,便是我们的使命”(第418页)。此转语就是把仁体也理解为“人与宇宙的共在”。 [6] 此法甚古,大可玩味。当代西方哲学盖反之。实以斯宾诺莎之“用”(欲望),进海德格尔之“体”(存有一般)之境地。破体用二分,亦从此途。 [7] 故欧阳竟无责之不当以新唯识论自命,毋宁为“新贤首宗”。 [8] 参见拙文,《生生与造作》,见丁耘,《中道之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页。 [9] 陈解熊不同于牟,虽亦反复强调体用不二,但似未完全去除“现象之后”的本体观、“流行之基”的实体观。盖因朱子、斯宾诺莎不能尽脱此气味欤? [10] 非但不取,对熊氏借佛家“刹那刹那”所说“不息”之意,实有微词。见《仁学本体论》,第68、69页。 [11] 告子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是之。 [12] 识仁是存恻隐之心、尽恻隐之心。不是识“仁”这个字。此文字学之所以为“小学”者。此学只是入道之门,未立大体。极而言之,不识字,不碍其为大人。识字,不碍其为小人。盖儒门之“学”,原非读书识字可尽其义。此固是极而言之。亲教圣人,旷世难遇。唯典册是学,而后德性可尊。 [13] 此诚康德所谓“纯粹理性之先验幻相”。 [14] 犹陈著所谓“实体必是流行发用的。”此是论断,而非实证。 [15] 黑格尔谓,变易是第一条具体的真理。盖有无皆抽象,不可自立,必过渡至对方。 [16] 以唯物辩证法术语云,即静止为绝对,运动为相对。 [17] “此一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即是仁的根源性表现,或者说,翕即是仁在宇宙的表现”(第65页)。“翕即是聚合、关联、维系、吸引,即是仁。”(第68页)。“在宇宙论上,生生即辟,一体即翕,皆仁之体用。”(第39页)。“仁是生生流行之总体,故乾坤并建乃可当仁,此专言之仁也。偏言之,乾主生,坤主爱,并建言仁……”(同上)。“辟是离散、消耗、个体化。一体是翕,离散是辟,皆宇宙大仁之体现。”(第65页)。如翕、辟皆是仁之体现,特言翕(聚合、关联)为仁有何意义?个体亦是一体,不自聚其体,何来个体。辟既为离散,如何能“个体化”?上引合观,不无未澈难周之处,盖作者未能始终一贯,以《易》之本意释翕辟仁知。 [18]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8,页560-561。 [19] “《繋辞》的作者已经接近到仁体的大用的认识,但尚有所未达”(第112页)“这是朱子仁学不彻底的表现”(第215页)等等。熊氏释经,自无此语。此是冯友兰式“演进”的哲学史语言。 [20] 此夫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命与仁,子贡之所以不得闻性与天道也。 [21] 尽四心,《中庸》总名之为“诚之”(“择善而固执之”),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22] 程明道,《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定性书》)。 [23] 阳明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的高”。 [24] 象山并江右,尚尊《书》所谓“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是心宗固有其正知见也。 [25] 老氏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见天地消磨万物一面。儒家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是见天地化育万物一面。仁者唯见其生,正是仁之为仁,自非仁者之过。唯欲将仁发皇为全体,则此全体之仁,须对“以万物为刍狗”一面,有所化解、包摄、超克。 [26] 用斯宾诺莎的术语说,道体是实体(substantia)而仁体只是样态(modus)。化用笛卡尔-斯宾诺莎运用过的经院哲学术语,道体对仁而言,不是“形式的”(formal),而是“超越的”(eminent,或译“卓越的”)。换言之,仁体这个谓词不足以尽道体,道体的实在性比仁体更为完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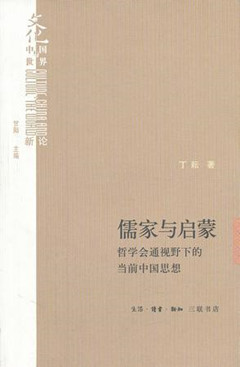 《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 丁耘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9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