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流亡者的“诗与真”
|

第一次读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12篇),那是在二十多年以前;因为《象棋的故事》,记住了斯蒂芬·茨威格这个名字;由此知道在他的名下还有一本众口交赞的名著《昨日的世界》。
不过,当时我没能把这本书读完,因为他描写的世界、书中的人和事与我的认知相距太遥远。我虽然在大学读了文学专业,对词藻华丽的抒情文本却天生迟钝。对那时的我而言,茨威格的写作语言——德语——与他笔下的那个“昨日的世界”都太渺茫,太遥不可及。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能读茨威格的德文原著,甚至还有机会把他的两本书(《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昨日的世界》)翻译成中文!况且还是受到一位著名出版人的委托!!
“时运既来,我等且安然以对。”在《昨日的世界》的篇首,茨威格引用莎士比亚《辛白林》中的这句话作为题记。这也正是我的态度:对天降的好运也要安之若素嘛!于是,我坦然地接受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的委托,开始读这两本书的德文版。
我先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入手,毕竟书中单篇随笔篇幅短小,容易一气呵成。当年读舒昌善先生中文译本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斯科特征服南极的故事,于是我把“挺进南极的争夺”这篇当作我翻译茨威格之旅的出发营地。
就难度而言,完成茨威格两本书的德译汉于我不啻于斯科特探险队的南极之行。只是我和斯科特们的心态完全不同,我既没有“当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也没有“不成功便成仁”的英雄情结。我把这个任务当成磨练文字技艺的机会,也想透过细读文字去了解一个人,读出文字背后的那个人。
可是,在斯蒂芬·茨威格这一个案中,似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茨威格是深受中国读者热爱的德语作家之一,豆瓣读书网站上能搜到很多其作品的译本。比如,三联书店1991年版《昨日的世界》下有这样的作者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Srer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主要作品有《三大师传》《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心灵的焦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等。
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世界各地游历,结识罗曼・曼兰和罗丹等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20世纪20年代赴苏联,认识了高尔基。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寂和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双双自杀。
这段简介提供了一些“硬”事实,尽管他的名字“斯蒂芬”在德文中的正确写法是Stefan,而不是Sreran(也许这是技术上的文字识别错误)。茨威格,活跃在世纪之交奥地利犹太富二代著名作家,因为“纳粹”的迫害而被迫流亡,年过六十而在远离欧洲家乡的巴西自杀身亡。这是简单的线条式勾勒。
当我在《昨日的世界》读到茨威格对自己父亲的描述文字——一位俭朴、勤勉的工业家,生逢好时代,就因为从来不做投机生意、依靠稳妥的经营,财富便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时,我就不得不多想一下:他父亲经营纺织业,财富来自在中欧和东南欧设工厂,我们可以设想那里与19世纪英国纺织业的情形不相上下,而德国诗人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则以“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我们织!我们织!”的愤怒之词,明确写出工人的悲惨处境。
是怎样的盲点和理由,促使茨威格这位号称有强烈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会如此这般浪漫地诗化资本的原始积累?简介文本中列举的作品以及他的名人交往,都无法给出答案。类似的困惑堆积得越来越多,我脑海里茨威格的人生图景便成了一张有待补充完整拼图。况且搜寻越久,我感觉缺失的拼图块就越多。
我对自己说:打住!肯定有专业学者在做这些工作,你不要越俎代庖。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茨威格是什么样的人?我会诚实地回答:真的说不好。
茨威格的第一任妻子曾经说过:他的作品只占其自我的三分之一。确凿无疑的是,茨威格是一位多产而成功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他长于撰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在对人物(尤其是女性)的描写中,他精于将历史氛围、传统上的修养与现代心理学结合在一起。
他的书有着广泛的读者,他的每一本书都很快被翻译成不同语言,他是一位真正蜚声全球的作家。他也是一位收藏高手。按照《昨日的世界》里的说法,他自认真正的成就在手稿收藏方面。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灵魂的追猎者”、“虔敬的天才热爱者”,为获得伟大艺术家(尤其是音乐家)的创作手稿,他不惜奔波在欧洲各地,耗费巨大钱财。
在同时代人眼里,他也是一位“呵护友谊的天才”,是最热情好客的主人,他在萨尔茨堡的山间别墅是欧洲文艺界名流的聚会之地,就算他临时下榻的旅馆房间,都能成为文学交流的中心。
此外,他也有慷慨助人的美名。他也被贴上了一系列的标签,其中被重复得最多的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尤其是,他是一位流亡者。对茨威格的每一种断言,都可能因为不同材料(书信、日记、各种档案,这些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新发现而受到撼动。
最近,兼具记者和作家身份的Gorge Proschnik怀着对茨威格的好奇,搜寻着阅读了包括书信等诸多关于茨威格的档案材料,在其新作《不可能的流亡——世界尽头的茨威格》(The Impossible Exile: Stefan Zweig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勾勒这位诗人、作家的形象:
斯蒂芬·茨威格——富裕的奥地利人,不停歇地游荡的犹太人,令人刮目相看的多产作家,不知疲倦的泛欧洲人文主义争取者,毫不松懈的关系搭建者,无可挑剔的待客主人,家中的歇斯底里者,令人敬仰的和平主义者,低门槛的通俗作者,性情温和的人,爱狗,恨猫,书籍收藏者,穿鳄鱼皮鞋的人,花花公子,抑郁者,咖啡馆的热衷者,孤独之心的安慰者,偶尔沾花惹草的风流者,对美男青眼相向的人,大胆的吹嘘者,天花乱坠的撒谎者,权势人物的恭维者,无权者的英雄,面对衰老喋喋不休抱怨的胆小鬼,对自己进入坟墓并无恐惧的人——这位斯蒂芬·茨威格,体现了其所处环境中的魔力和疮疽。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茨威格的作品,尤其是《昨日的世界》便在德国读者中受到广泛的关注,这在犹太流亡作家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书中到处体现出来的那些可以归档在人文主义、欧洲文化、个人主义、精神生活、和平主义等概念标签下的价值观,表达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这种渴望在战后胜过以往任何时候。在当时的图书市场上,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类似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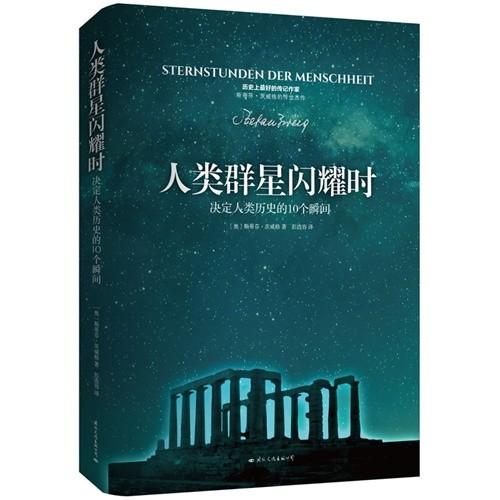
况且,茨威格的作品也有着其特有的内在质量:他是一位严肃的娱乐者,一位敏锐而细心的观察者,他将各种习俗、特色、激情和错误尽收眼底。《昨日的世界》的回忆式展开,有着非常高超而纯熟的叙述艺术,如同放置在不同时间维度中的几台摄像机在同时工作,而茨威格能在这些画面之间进行熟练的切换。
不仅如此,甚至在不同的文类之间的切换,茨威格也能游刃有余:从人物描写到历史陈述,再到哲理思考或者人生感悟,这些不同内容能在一个段落中穿梭来往。
Prochnik认为,茨威格带给世界的礼物,有赖于流淌在他血液中的超级感觉能力。他善于在文字当中抓住他人的想象力,这造成了一种沟通上的温暖。身为一位流亡者,他写出了遭受颠沛流离之苦的人共有的伤感和忧郁。
从青年时代开始,茨威格便不停歇奔走在各地,在哪里都无法扎根。一方面他对维也纳的文化生活极为崇尚和认可,而作为维也纳文化生活最突出标记的圣诞树却与他无缘,有一棵圣诞树的童年愿望在家中得不到满足,让他从小就逃进自己的“白日梦”当中,而后便试图逃离家庭、甚至要逃脱自己。
在Prochnik看来,茨威格从一开始便是一位流亡者,此前漫游世界的生活可以说是1934年后流亡生涯的前奏。就拥有金钱和人脉关系而言,茨威格不是一位典型的流亡者,但是他却能深刻地把握流亡者的心态和感觉。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本书当成历史描述,也不能看作自传。茨威格也没有以“客观性”这一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明确地声言,这里纪录下来的都是在意识深处为自己保留的回忆,只有那些为自己所珍视而保留下来的回忆,才配与读者分享。
记忆与事实或者档案材料中的偏差,尤其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所作所为的描写,已经有研究者进行了对比(我不想在这一话题上展开)。作家茨威格,更像是一位古典意义上的诗人,他精于用文字营造充满冲突性的情节和戏剧化的高潮,像古代诗人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一样。这一点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显得尤为突出,甚至他也直接采用了诗歌和话剧剧本的形式。
茨威格也以写历史人物的文学传记而享有盛名,但是他对关涉到传主的事实的把握,我们则有理由带着怀疑的目光。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是他描写心理学家佛洛依德的传记式随笔。茨威格在年长25岁的佛洛依德面前尽显谦恭和尊崇,二人算是忘年之交,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他们二人的流亡生涯当中。当佛洛依德于1939年客死伦敦时,茨威格在其葬礼上发表了追思演说。
但是,佛洛依德对茨威格在1927年出版的他的“传记”非常不满意,并直言不讳茨威格缺少对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解。学科史研究者Johannes Cremerius甚至认为,出自他笔下的佛洛依德传记对于公众对精神分析这一学科的认识有误导,虽然茨威格盛赞佛洛依德的勇气,实际上给该学科带来的后果则是有损害。
《昨日的世界》一书的外在形式,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中的主观成份,因为全书屏蔽掉私人生活和家庭成员,给人留下了“客观”“正史”的初始印象。而在前言的文字中,茨威格却刻意强调这本书的主观性。这种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也许正是茨威格的精心设计。
如何读茨威格
在战后的德国文学批评界,很长时间茨威格不怎么被提及,但是他的著作却一直都不乏读者。倒是茨威格最心仪的法国,回报给他以相应的热爱。这两本书的法文版,都被收进著名的经典文学系列“七星文库”,并有专家评注。这是迄今为止德语出版界尚未做到的。
2012年以后,茨威格的作品成为公版书,这又促成了新一波“茨威格热”。英语、西班牙语的“新译”,成了茨威格进入新老读者视野的新契机。
对茨威格的新老“粉丝”们,至少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上来阅读这两本书。
其一,作为文学,享受作品本身的戏剧性场景、豪华铺排用词所展示的魅力。这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读者更多去了解所涉人物和历史事件;反过来,对人物和历史事件了解得越多,对其中时而出现的睿智洞察之语就能有更深的体会。
比如,《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行刑前的最后的瞬间因沙皇的赦免令而侥幸逃脱死亡的情景,那是在1849年。“自从领受了那燃烧般的死亡之吻,必须为了经受苦难而去热爱生活”——茨威格这样解读这一死里逃生对作家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摆脱死神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多。1862年,经济状况好起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一次欧洲旅行,第一次接触到轮盘赌(当时在俄国这是被严禁的)并染上赌瘾而难以自拔。
在《三大师》一书中,茨威格曾经这样写到:“如果说西伯利亚只是他受苦的前庭,那么法国、德国、意大利便无疑是地狱。”在德国的威斯巴登和巴登-巴登的赌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输掉全部资财,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他把全部家当都送进当铺换成赌资。赌瘾造成的痛苦和困顿持续了整整十年,
而在这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系列重要作品:《罪与罚》、《赌徒》、《地下室手记》、《白痴》、《群魔》。茨威格的作品之所以能长销,也许这正是其魅力所在:在读过更多的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读者会愿意带着会心一笑再回到他的描写,再经历一次情感上的酣畅淋漓。
其二,从其作品中读出一个复杂时代里那位多层面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财富、名声和才华都是稀缺资源,而斯蒂芬·茨威格却一项也不缺少。他是时代的幸运儿,他在记忆中留住的昨日的世界,曾经是只有极少数像他这样经济与文化双重精英阶层的特权。
德国作家特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在1877年的一篇文章里将“大众旅游”描写为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民俗学教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指出:就旅游者的人数而言,冯塔纳采用的“所有的人”这类用词毫无疑问太言过其实了,当时能有时间和财力来每年一次度假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
然而,后来出现的(甚至直到今天尚有的)大众旅游现象所具备的形式,在当时已经出现。假如今天处于普通社会阶层的读者在茨威格的回忆中能获得共鸣,或者能产生强烈的代入感,那恰好表明世界在变好,曾经的特权享受已经进入平常百姓家:我们断无理由去惋惜那个逝去的美好旧世界,反而应该庆幸经历了一个更好的新世界。
假如我们还停留在那个旧世界,作为普通社会成员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都无由与茨威格相遇。
至少在外人看来,茨威格是一个快乐而成功的人。他有大量的铁杆粉丝读者,他的书只要出版便销量上万(如果考虑到在今天的德国销量超过一万六千册就被列为“畅销书”的话,在20年代就有过万的销量,那是非常骄人的成绩);他结交来往的都是各界名流。
然而,茨威格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德语文学主流的认可:后来负有盛名的萨尔茨堡艺术节,虽然茨威格参与了发起活动,但是因为与艺术节压轴作家霍夫曼斯塔尔不睦,主办者有约在先:艺术节期间不得上演茨威格的任何作品,这一规定永久有效。
他热爱的小城萨尔茨堡,他的家在这里,从那座半山间的豪华别墅他能将小城尽收眼底;文学和戏剧艺术盛会是最看重的精神家园,然而他被关在门外。每年夏天,当世界各地文艺精英齐聚萨尔茨堡艺术节的当口,他却选择躲离家乡到比利时海边去度假。
他留给外人的印象永远是高朋满座,他也不乏慷慨助人之举在同行间传为佳话,但是关于他的流言和恶语,对他的指责和要求从来都不曾停息:有因为钱财而反目成仇的,有因为政治观点而恶语相向的(比如他与克劳斯·曼在政治上的分歧,他因为不愿意投身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而受到汉娜·阿伦特的指责)。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在给前妻的信中失望地写到:“我的每一份友谊都腐烂掉了。”茨威格,一个身处复杂时代的多面人,一个我们尚且所知甚少的人,无论其作品还是其人格,原本都是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研究的绝佳个案。
其三,茨威格的个案会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回忆著作,尤其是那些“劫后余生”者在经历了整体上为黑暗吞没的时代后撰写的回忆文章。重构茨威格的人生这块拼图,仍然有着许多残缺。
我们找到的块数越多,就越能看出来《昨日的世界》里的种种刻意之处,某些描述中有意而为的模糊用词,某些有意的、不经意的、抑或是潜意识的避重就轻,而这些都是在一切回忆文本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洞察回忆录写作者的行文技巧,会让我们对这类文本的历史价值形成更加敏锐的感知。随着近年来茨威格作品的再度升温,对茨威格的档案文献研究也日益广泛而且深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专业学者将最新研究成果整合进对这部作品的评注当中。那会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版本。
关于这个译本
在本文的开头,我曾经把自己翻译茨威格的这两本书比作斯科特挺进南极的行动。“这里什么也看不到,与前些天放眼所及的单调在任何方面毫无区别”——茨威格引述了斯科特在到达南极点那天在日记中写下的话。
在完成这两本书的译稿后,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很难说通过翻译这两本书我的德语水平是否有所提高,尽管我在此期间查词典的频率之高,在过去很多年中都不曾有过。有些词汇查过之后真的会马上再忘掉的,正如某些单词你一生只能在某个考试中和它打过一个照面一样。
茨威格同他的第二位夫人绿蒂
但是,肯定让我从中有所受益的,是关于欧洲文化史的知识,因为我把此译本的重点放在“正确性”上。豆瓣读书上列出《昨日的世界》有14个中文版本,大多数版本的读者评分都在9分以上,可见读者对该书极为认可。
我自己当然也参考了现有的译本。比如,茨威格在讲到自己在1901/1902年因为能在《新自由报》上发表文章而在公共文化场合备受瞩目时,用Benjamin这个词来指称自己这位“年纪轻轻的后生”,而某个译本中却把Benjamin理解为那位柏林的文艺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并写了一条注脚来介绍本雅明,把这个句子理解为茨威格以瓦尔特·本雅明自喻。
我惊讶于这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硬伤误译:1892年出生的瓦尔特·本雅明当时还是一个10岁的柏林孩子,怎么可能出现在茨威格在维也纳的世界当中?在我读到的有关茨威格的材料中,未见到二人曾经有过任何交往的叙述。(此处在“人生大学”一章)
还有一处的“硬伤”也让我吃惊:在茨威格写到一位勇敢的女和平主义者时,某版本上出现这样的句子:“她抱着佛罗伦萨夜莺般的热情,认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战争,完全杜绝战争。”我搜肠刮肚地想“佛罗伦萨夜莺”会是怎样的典故,终于不得头绪,于是去翻看原文。原来那根本不是一个典故,只是一个名字:Florence Nightingale,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丁格尔护士。
同样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豆瓣读者的评论、读后感、溢美之词都不缺乏,唯独对这类“硬伤”没有人指出来。这让我意识到一个事实:一般读者其实是无力意识到这类误译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新译本中,在大多数读者的“盲点”上多做些改进。为了避免自己也和读者一样被拖进误译的窠臼而受到蒙蔽,后来我干脆放弃参考已有的译本。这种追求“正确性”的取向,的确帮助我去学习和重温欧洲文化史,是我翻译这两本书的最大收获。
文笔的好坏,也许最是一个评判的问题,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我会认为,好的行文风格意味着能用简单的句子把复杂内容说清楚,而不是正好相反,堆砌一串华美罕见的大词而并无实质性内容。
比如,对于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个夏天,茨威格这样来描写:“连续多日,天空像蓝色的丝绸一般舒展,空气柔软而温热;草地暖暖地散发着幽香;树林郁郁葱葱,到处都是新绿。至今,当我一说出‘夏天’这个词,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的灿烂七月天。”
这样的文字,算文笔漂亮的美文?我觉得这无非是从文学描写的旧货摊上随手拣出来的配件,按照常见的套路组装一下而已。在文字风格方面,我力求在译文中把我理解到的原义表达出来。
我甚至都不敢说是否能穷尽他文字里的“微言大义”,至于说文笔是否如某些不看德文原文的读者所期待的那样优美流畅,就只好臧否由人了。也许自己不懂外语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理直气壮地指责译者虽然懂外语却母语水平太差,但是至少也还有理论与实践双修的专家知道翻译的要义并非尽在通顺:“如果作品本身有一定的阻力和张力,可能未必要翻译得那么通顺”,复旦大学德语系魏育青教授如是说。
茨威格有很多过人之处。他的读者数量大、忠心度高;他是讲述高手,能把叙事中的视角转换运用得柔曼轻盈,天衣无缝;他能左右叙事的节奏和韵律;他对人的心理有极深邃的洞察;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阅读积累,不时地有蕴含深刻哲思的金句嘉言。他甫一步入文坛,便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上述这些特质都功不可没。
但是,茨威格的文字水平难以得到德语作家和文学批评界的认可。茨威格多年来遭受冷遇,并非仅仅因为同行们嫉妒他辉煌的市场战绩。德语文学批评家们为文学语言设定的“金线”,把茨威格挡在精品文学的殿堂之外。当然,如果把评判标准做些调整,文学史上的“英雄榜”座次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