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哲学、科学,乃至道德观和价值观如何与孩子的趣味、审美,乃至他们的内心世界连接起来,真的是很大很难的课题,如果真的做不到,那么我选择更保护孩子的、更注重展示和应和他们内心世界的绘本与动画,让他们保持充分的,深入的内观状态,培养起他们对更为广阔的全人类精神世界的好奇心和同理心。”
想要写这个题目,是因为女儿的早教机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小兔子家种了许多南瓜,南瓜成熟了,兔妈妈让小兔子去收南瓜,小兔子说:“南瓜太重了呀!我搬不动!”兔妈妈说:“妈妈也搬不动呀,怎么办呢?”小兔子出门玩耍,看见小熊胖胖被一块大石头压在路上,小熊胖胖说:“谁来帮帮我呀!”小兔子上前帮小熊胖胖搬开了大石头,小熊胖胖说:“谢谢你小兔子,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一定会去的!”小兔子说:“哎呀真的有呢!我家的南瓜丰收了,我和妈妈都搬不动,你能帮我搬一下吗?”小熊胖胖一口答应了,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帮兔妈妈收了南瓜。
故事讲完了,这其中有多少逻辑错误,我连数都不想数,只觉得哭笑不得。这样的故事在早教机里有很多,几乎可以算是“常态”,当然,这种“常态”在幼儿绘本中也比比皆是,人物形象粗暴,内在逻辑混乱,比如某本教小朋友认识形状的,说天要下雨了,所以大熊从天上摘下了一个长方形和一个三角形,做成了一把伞。且不说伞柄是不是长方形,单是这个叙事就很令人困惑,天上怎么能拿下来一个长方形和一个三角形呢?孩子要是问我这个问题,我又该怎么回答呢?强行将抽象概念和具体场景联系起来,对于对象读者——12月龄以上的孩子来说,应该是很难理解的吧。相对比的,我在另一本形状认知的国外绘本中,具体场景都是以明快可爱的简笔画绘成,并以高亮线条的方式,标出其中的抽象图形元素,简单易懂,重点突出,逻辑清晰。明明就是很容易想到的点子,为什么有些国产绘本就是要继承老一辈那种知识主打的灌输式认知教育方案呢?
再说说低龄儿童的行为认知培养绘本,在几届童书展上,这类绘本都几乎包圆给了译介绘本,德国的厕所书和睡眠书,日本著名的《乳房的故事》等等,我也不能说这些绘本就做得怎样出众,但至少它们以一种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把孩子所不能理解的世界耐心地、以一种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展开在他们面前,比如来自德国的厕所书,是一本引导孩子自主如厕的绘本,但作者没有贬低戴着尿布的孩子,只是通过反复的对比、夸张的语气和高涨的情绪渲染自己上厕所有多么开心,多么方便,利用孩子的好奇心慢慢接受自主如厕,看起来是不是比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宝宝你怎么还戴尿布啊,羞不羞啊”这样的羞耻教育,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内心呢?

《乳房的故事》插图
以上说的是认知教育方面的绘本,但我们已经能从中看出当下童书创作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怎样对孩子介绍成人的世界,如何让他们接纳成人的认知系统?同时,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和放飞孩子的想象力,如何把这二者按照逻辑并用优美的语言和谐地表达出来,承担合理的、符合孩子生理与心理发展阶段的教育作用,这可能是童书和儿童故事面临的最大挑战。近几年去看了两三次比较大型的童书展销,通过大量而集中的阅读和比对,我发自内心地为中国本土的童书创作感到担忧。我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展台上,看见大概已经卖了30年的《上下五千年》和《十万个为什么》,曹文轩的《草房子》再版了又再版,插图版、绘本版、手写寄语版等等,换汤不换药。而低幼读物的展柜上则是“喜羊羊”、“熊出没”、“植物大战僵尸”以及各种各样的识字卡、识物卡,什么流行卖什么,什么畅销卖什么,创新的、温柔的绘本不是没有,但真的太少了,本土原创的更是凤毛麟角。
当然,我更深切的体会还是人文教育的匮乏。中国的童书状况似乎可以从这个超大的展台上窥见一斑:重知识、重娱乐,轻人文,尤其是文学与哲学。文与理,从幼童开始便是泾渭分明的两条线,我们的童书创作者,似乎非要将人文与科学对立起来。对于低幼的孩子来说,文学似乎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他们只要会认字,会简单的科学知识,就足够了,不论这科学是怎样生硬地刻进孩子们的脑海里。当然,他们对人文教育也似乎有什么误解,纵观为数不多的人文童书,名著缩写版、古文普及本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其实这些与他们制造的科学读本没什么区别,仍然是知识量的累积。而原创的儿童文学,曹文轩、郑渊洁和秦文君几乎成了无法逾越的高峰。儿童文学温暖向、科普向,似乎是永远的基调。
我记得我童年的阅读体验,还没有到如此粗暴匮乏的地步。我还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给我的睡前故事是《简·爱》,那时候的我并不懂得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的爱情,也无法分析简·爱的童年生活对她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我每晚都会听到流泪。孩子不能体会成人那种复杂的情感,所以只能阅读和聆听简单、快乐、拟人化的睡前故事吗?我的经历提示我并非如此,人类生而共情,即便孩子不能表达,或无法完全理解和深思这种复杂的情绪,也不等于他们是无知无觉的小动物。我认字之后读的一套儿童文学经典,更让我记忆至今,那里面有很多并不快乐的故事:为朋友失去光彩的快乐王子、为了捍卫时间秩序而战斗的嫫嫫、在母亲怀中安详死去的白喉的孩子……他们和最终圆满的白雪公主、灰姑娘一样重要,没有他们,我的童年阅读不会完整。
但随着我女儿的慢慢长大,我对中国童书的看法从愤懑到有所期冀,直到现在变得更加迷惘和困惑。从她出生伊始,我就致力于培养她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希望她能接触到的阅读材料、视听材料都能是高雅的,至少是不那么俗气的,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但事实证明,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而且我这样的培养可能太过超前,违反了她的生长规律,她尚且没有能够理解感情,也还没有能够理解语言美、形式美,更或者,也许人生就是从“低级趣味”开始的,而我们不可避免地把孩子生在了一个充满“低级趣味”的时代。我开始怀疑,那些拙劣的童书,也许并不是源于作者的敷衍或愚钝,恰恰相反,是他们太过精明,以至于果断迎合孩子的这种“低级趣味”,来换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比起阅读,她显然更喜欢看电视、看手机、看iPad,比起听故事,她更喜欢认东西、翻翻书,感情、趣味、审美,都远不如她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知来得重要,两块钱一本的识字卡,她喜欢得不要不要的。也有比我将“高雅”实践得更为彻底的妈妈,试图给孩子营造一个“无电子产品时代”,孩子直到快两岁都不知电视为何物,但只是春节时她家仪式般地打开电视看了会儿春晚,刚学会说话的孩子便真诚地对她说:“电视好看。”看来人类从童年开始,便充满着懒惰的、渴望大剂量娱乐的基因。
但我也发现,孩子的趣味并不会永远俗气下去,或者说,他们的兴趣是短暂而易转移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培养,但这可能更多的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她小月龄的时候,喜欢质朴可爱、故事简单的小猪佩奇,开始听得懂话时,开始喜欢熊出没,甚至猪猪侠,但现在她又重新爱上了小猪佩奇,抛弃了熊大和熊二。我无从了解促成她这种转变的原因,也不知道如果把海量的视听材料都提供给她,她自己又是不是有去芜存菁的能力。如果每一部动画片都能够像小猪佩奇这样寓教于乐、可爱生动,如果孩子能够一直生活在这种令人愉悦的审美之中,她的“低级趣味”是不是也会相应地提高值域呢?我前面所提到的合理的教育,便在于此,不过分迎合孩子的原始趣味,不过分迎合父母揠苗助长的教育需求,保持自己的审美和教育原则,大概是童书最难做到的部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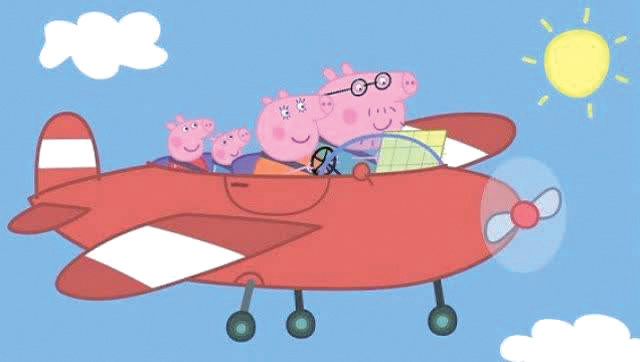
《小猪佩奇》插图
尽管我已经对女儿所能接触到的童书和动画片做了挑选,但面对我所能挑选的待选项,我还是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无力。女儿还处在学语阶段,她的兴趣尚且是个人化的,但她对视听阅读材料的选择和同龄的孩子是不约而同的,她不需要和别的孩子交流,就能够从眼花缭乱的选择项中挑出“爆款”。去年冬天的童书展,童书主题已经显现出了某种同质化与垄断的趋势,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三字经、弟子规、声律启蒙、叶嘉莹乃至古文字的展位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是爆款儿童读物的寡头地位逐渐稳定,小猪佩奇、小马宝利的展台设在最为醒目的位置,占地也颇为奢侈,从图书到玩具周边应有尽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偌大的童书展,仿佛是父母趣味与孩子趣味之间的一场战争。
近年国学的兴起,对“崇洋媚外”论调的隐隐反抗,对传统文化的大力宣扬,构成了父母对国学类绘本的趋之若鹜,这是成本最低的高雅教育,是了解语言美的重要途径,是语言和意象、能指与所指的诗化连接,但父母更为重视的,可能是在聆听与背诵中便能建立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是父母代幼年时背古诗运动的延续与发展,是能够达到“开口跪”水平的捷径。但孩子显然不这么想,他们需要的是两个世界、和小朋友开心玩耍的现实世界,以及中二的、有好看衣服的,有超能力的,被伙伴簇拥众星拱月拯救地球的幻想世界。
我们真的要和孩子这样对峙下去吗?童年时期被凿壁借光囊萤映雪悯农支配的恐惧你们都忘记了吗?正如我开头所说的,文学、哲学、科学,乃至道德观和价值观如何与孩子的趣味、审美,乃至他们的内心世界连接起来,真的是很大很难的课题,如果真的做不到,那么我选择更保护孩子的、更注重展示和应和他们内心世界的绘本与动画,让他们保持充分的、深入的内观状态,培养起他们对更为广阔的全人类精神世界的好奇心和同理心。前几天朋友送了我一本《给孩子的美的历程》,恕我直言,那就是《美的历程》啊,真的要给孩子看这种学术著作吗?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中国童书的一次进步,虽然仍显得粗暴一点,但至少,我们已经跨出了带着孩子走向美、走向更广阔的对人类内心世界探求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