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曰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应用语言学研究室主任,语料库语言学暨计算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多语言多模态语料库暨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1年安徽大学外语系研究生毕业,1985年获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系语言研究优等硕士学位,1987年获该系语用学与修辞学博士学位,师从英国学术院院士Leech教授。1988-1990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许国璋教授。1991-199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二系主任、应用英语学院院长。1994-199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兼应用英语学院院长。1998-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当代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当代语言学》主编之一。迄今发表英语论文37篇,英语教材和著作39部,发表汉语论文36篇。 学术兼职有:英国诺丁汉大学特聘教授 (2004-2011);兰开斯特大学特聘研究员(2008-2010);香港理工大学校外学术顾问(2005-2012);俄罗斯彼得大帝彼得堡科技大学讲习教授(2016);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外聘教授(2015-2018);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教授(2015-2018);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名誉教授。 在10个国际学术刊物任编委。中国计算机辅助教学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语用学协会常务理事。先后获霍英东教育基金第四届青年教师科研类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国氏”博士后奖,国家级“优秀回国人员”、国家级“优秀博士后”称号、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等。  1.迈入语言学研究之路 李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副研究员):顾老师,您能谈谈您是怎么跟语言学结缘,走上语言学研究之路的吗? 顾曰国:本人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可以说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幼年读小学时适逢文革初期,除毛主席语录外,其他书籍一律不让卖。是时家父开书店,不让卖的书封面封底一撕,扔在后面的书库里。书库对门便是我们家。家父因怕我们上街被武斗打死,时常把我和双胞胎弟弟锁在书库里。我们因此便有了免费的图书馆。当时无论是大人书还是小人书,统统翻一翻,大多数书是犹如猪八戒吃人参果,读而不知所云。不过有一点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长大了想当个作家,写些像《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样的小说! 到了中学时代,幼年的梦想似乎变得更现实些了。时逢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学校开始鼓励读书学习,本人跟许多同学一样开始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快就迷上了无线电。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本人高中也毕业了,便加入了回乡知青的洪流。 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我开始通过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广播英语。这可以说是我学习语言学的启蒙阶段。之前,用母语说、写,犹如听人唱歌、用筷子吃饭那样自然,很少关注其内在的构成。学外语情形就不同了,总让你感到外语很奇怪,“老外”怎么会这样说话,逼着你开始注意起语法来。不过当时学英语是为了消磨时光,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学语言学,以研究语言作为一生的职业。 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了。学无线电的夙愿再次燃起。因加试英语后矮子里面挑壮丁,我被安徽大学外语系录取,读“英语特种绝密专业”。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设的专业,就是给国家的一些机要部门培养英语口译和笔译的人才。我们进校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遗留专业也就不了了之了。 上大学跟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相比,可以说是进了天堂。读书跟面朝黄土背朝天相比,是不折不扣的享受!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翌年本人便报考本校研究生,录取为英美语言文学研究生。“语言文学”是专业设置名称,在当时还没有设语言学专业。我们的研究生课程没有开语言学课,全部是英美文学。学习不到两年,颇感吃力。主要原因是觉得文艺评论不讲逻辑,用现在的流行话说,全是跟着感觉走。我总是找不到感觉。由此给自己下了判决书,本人不是学文学的料。幼年想当作家不过是自不量力、不知天高地厚的梦想罢了。 我开始认真读语言学著作,是1981年。第一本中文著作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第一本英文语言学著作是J.Corbett 的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这两个“第一”让我终生难忘。在此之前,也读过不少用中文写的关于英语的语法书。然而读这些语法书时,不是作为语言学书来读的,是作为学好英语的工具而死啃的。读上面的两本修辞学书时,情形完全不同了,眼睛睁大了,有点开窍,朦胧意识到这是另外一片天地。 我真正下决心学语言学,以研究语言作为一生的追求,是在1982年。是时我已经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一天在图书馆了看到了G. N. Leech教授的Semantics,便爱不释手,反复阅读,从此便暗暗下定了决心,语言学是我的兴趣所在。自那以后,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读语言学的书籍。 1983年国家组织出国进修考试,我有幸被录取后便申请去英国Lancaster大学,追随Leech教授,攻读语言学。1984年秋终于如愿以偿,面对面见到了这位语言学大师。如果说上大学是我一生中第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Leech教授接受我,做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里程碑。 在Lancaster大学读书期间,对语用学和话语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话语分析在历史渊源上就是古老的修辞学。非常遗憾的是,当今,修辞学在欧洲已经衰落,被话语分析所取代。在欧洲Leech教授是对修辞学仍有研究的少数几位语言学家之一。我的硕士论文地地道道地是属于语用学范围,而博士论文则想把语用学、修辞学和话语分析集成为一体的研究。这跟Leech教授当时的研究兴趣基本上是一致的。 1988年在驻英使馆的安排下回国,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许国璋教授。之前我跟许老并不相识,也从未有过书信往来。这也许是天意,我跟许老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他的国学和西学功底之深厚让我折服。记得刚到所里,许老是名副其实的三日一小宴,七日一大宴,用的不是公款,而是他掏的个人腰包! 回眸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有四位不可或缺的领路人,那就是我的四位老师。大学期间的吴娴华,研究生期间的杨巩祚,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Leech和许国璋。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待学生如学友、挚友、家里人,是平等对话者。吴娴华老师虽年过花甲,我们见面时她还是用她给我起的绰号“老马”叫我。记得1980年春节,因囊中羞涩没有回家,杨巩祚先生命他的儿子冒着大雪寻我到他家过年。1985年春节我在英国。一天我在信箱里摸到一个信封,是Leech教授留给我的。打开一看,里面有张购书券,还附着个便条,歪歪斜斜有三个汉字:压岁钱!1990年,准确的日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我住在北外西院18号楼602房间。听到有人敲门,没想到站在门外的是提着篮子的许国璋先生。他听说我病了,特地给我买了点菜,顺便来看望我!是时他已经73岁。这些老师通过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要想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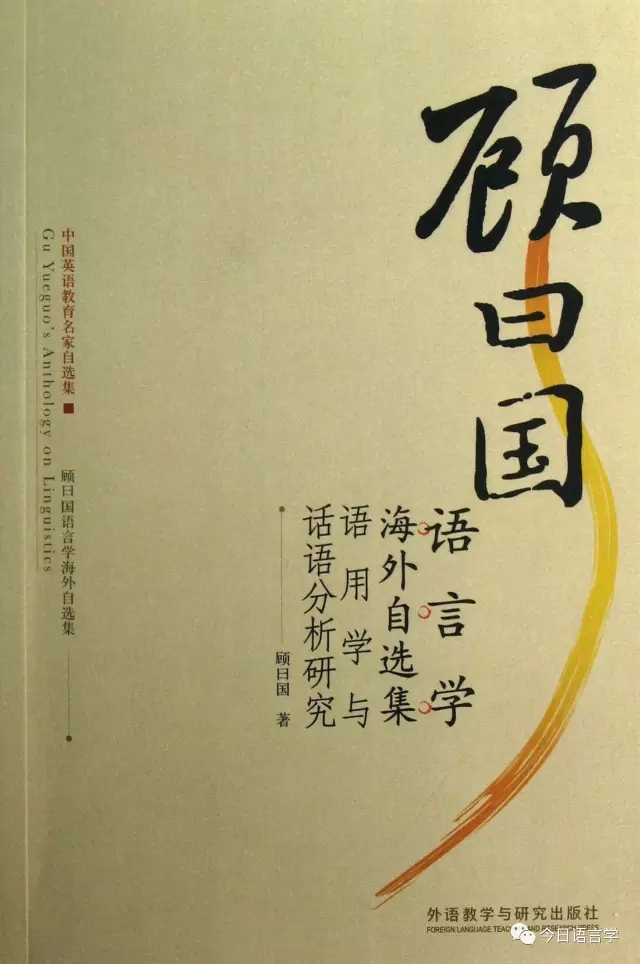 《顾曰国语言学海外自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2.体悟语言研究之道 李芸:您从事语言研究这么多年,一定积累了非常多、非常好的研究经验,您能谈谈您的语言研究之道,给年轻学者一些建议吗? 顾曰国:说起语言研究之道,我感到有得说的是一些不入道的体会。记得1982年我第一次发表“论文”。拿到了有我文章的杂志和随后寄来的稿酬,虽然表面上还显得谦虚,心底里却自鸣得意了许久,飘飘然自以为成了“家”。英国留学生活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之一是知道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再读当年的一些所谓“论文”,恨不得钻地三尺。问题出在哪里呢?我那时把读书加上对其归纳总结所形成的文字等同于论文,而实际上充其量只能算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对前人的研究在文献上做严肃的梳理工作,分析其优劣得失,是研究任何一个语言学课题所必须做的。即使做到这一点也不等于论文,只能作为论文中“先前研究文献回顾”这一部分的内容。真正算是自己的东西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超出前人的地方。 在国内一些学术交流会上,立志研究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的年轻学者,往往问我应该读些什么书,如何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等问题。本人的体会是,读专业著作自然不用说,而读相关专业的书往往比读专业书还重要。这是因为西方的当代语用学和话语分析,在知识结构上都是建筑在相邻学科之上的,比如语言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古典社会学、法兰克福批判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等。假如不读这类书籍,研究西方语用学和话语分析就很难深入下去,无法跟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做不到平等对话,在他们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自然就十分困难了。我现在读书花时间最多的都是在读相关专业的书上,收获特别大。因为这使得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西方学者在语言学方面的最新成果,不但容易理解他们的思想,同时也能看出他们研究的漏洞。俗话说,旁观者清嘛。能够指出他们的不足,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文章,肯定能够被接受和发表。 怎样才能做到“山高我为峰“呢?我以为最终的答案要在语言事实中去寻觅。再好的理论,再好的假设,经不住语言事实的检验,最终必定是要被淘汰的。创新不能成为鼓励狂妄的托词;大胆假设必须建立在对前人研究熟烂于心的基础之上,精密求证是把大胆假设上升为理论的必由之路。必须指出,我先前的一些文章并没有达到我给自己定的要求。聊以自慰的是自1990年起本人便着手构建现场即席话语语料库,时至今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我虽已年过不惑,仍雄心勃勃地学习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数据建模语言,现在盘点一下,收获极大,使我想起30多年前在农村劳动时农民老大爷常说的一句话,磨刀不误砍柴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