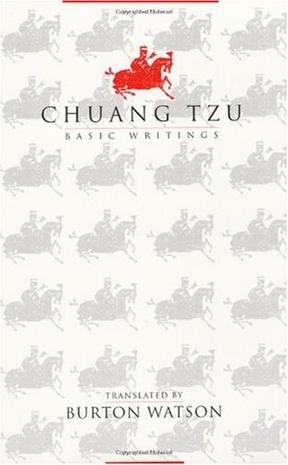“吁──这是最后一站了。”在北京三里屯一家咖啡馆刚落座,如约而至的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就长出了一口气,她用流利的汉语说,这几天有点累,但更多的是兴奋和感动。接受完本报记者采访,她就奔赴机场,为2012年春天的中国行画上句号。五天四夜,从上海到北京,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座,上海书城和北京单向街书店的两场对谈加读者见面会,其间还得见若干家媒体,见缝插针地同个把北京老友叙旧……她对中国并不陌生,这些年也时常举家前来旅行,但如此正式如此密集的日程于她还是头一回。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已在香港和台湾多家中文报纸开专栏,“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不少,但能说能写,而且写得好的,只有罕见的新井一二三”,香港作家蔡澜的这番评价见仁见智,但可看出港台读者对她不陌生。专栏写得多了,结集成书水到渠成,掐指算来,台湾大田出版公司已陆续推出十几本她的书。中国内地读者多是近几年从散见于《万象》杂志上她的文章接触到这位日本作家的文字,她的书在内地陆陆续续也出了好几本,继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等三本书之后,她的《午后四时的啤酒》等作品也排上了出版日程。 身为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她多年来一直用中文向华人世界读者介绍日本历史与文化,举凡日本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美食旅行等等,在她的文章中每有涉猎。她满含怀旧情绪的笔触记录着日本城市的变迁,不忌惮以客观、犀利的文字观照、反思今日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她的写作未囿于纯粹的涉日话题,也写自己这些年遍布世界很多地方的行走印记,写她在北京、广州的留学生活,写她对台湾的复杂情感。她的文笔流畅好读,既富一定文学性,也有难得的幽默感,与中国作家的中文写作形成特别的相异与映照。 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上,新井一二三半开玩笑地说她当年之所以学中文进而用中文写作是因为想要“摆脱”让她害怕的母亲的支配、控制,“母亲是日本人只看得懂日文,我得创造一个她不能进来的空间,我用中文写作她就看不到了,这是多么大的内心自由”。中文写作令她“进入另一种语言之后,好像没有来自母亲或母语的束缚,这个空间更大更具体”,这种自由延伸到众多中国读者那里,成为他们认识日本、认识世界的一扇书窗,“用中文写文章才会让我被这么多读者认识,世界都像被扩大了”。“中文读起来很悦耳”,这亦是她当初学中文的缘由之一。她告诉记者,十九岁那年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要选第二外语,“当时的选择只有德语、法语、俄语和中文。我高中时学过两年德语,但德语发音我不喜欢,于是选了中文”。不过,她没想到后来能以中文写作并一发而不可收。 新井一二三很早就在日本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她觉得从日文写作到中文写作并非根本性的转变。“读大学时我办过校园杂志,这类杂志如果办得比较成功,就会吸引一些社会媒体的注意。”于是,《读卖新闻》的记者采访她时听说她要去上海旅行,就顺便约她写写旅行见闻,“他们说,你去上海多拍些照片啊,回来帮我们写写稿子,没想到后来真的登出来了。我记得我拍了上海厕所里的老式木马桶,那个在我这个日本人看来是很新鲜的东西”。再后来,香港一家杂志约她写东西,很自然地开启了她的中文写作之旅。 最开始写中文,她的思路需要先转换成英文才行,“再把英文底稿翻译成中文,我发现英文和中文的语法还有些相似,而日文和中文是倒过来的”。现在不存在这样的思路转换问题了,“我已经可以直接用中文写作,走在路上我想问题都是用中文。我是日本人,生活在东京,但我用中文思考,也许就因为这个,我看问题的角度和很多日本人不一样”。她略带感慨,幽幽地说,“学中文我没觉得难,日本人学中文肯定要比西方人学中文有优势,我们对汉字本来也不陌生。有时候我甚至感觉,我这辈子是日本人,可能前世我是个中国人吧。每次我用中文写作,就好像有个中国人的灵魂不知从哪里飘过来启发我。一切来得特别自然,肯定是种缘分”。 她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旅居加拿大为语言所困的情形,“英文对我来说是比较难学的,去了加拿大足有两年多,当时我还在做学生,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刚刚老师说的一句话里,每个词的含义我都能听懂了”。 和很多同龄日本女子读书、工作、相夫教子的按部就班人生不同,新井一二三有颗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蠢蠢欲动的心。十四岁就已独自长途旅行。1982年夏天还在读大二的她初次出国到北京进修汉语,之后为期两年在北京、广州两地的留学生活让她利用假期走遍大半个中国。旅行之外的收获是一路走一路和沿途遇到的中国人学中文。1987年,她移居加拿大,从此一步步实现周游世界的梦想。旅行不止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也大大拓宽了她的视野,进而成为她写作的一大主题。就连她的另一半都是在去香港旅行时结识的。 她的人生和写作,刻意的成分并不大,反而天马行空享受生命之不可测之处甚多。比如,她从不奢望完美的旅行,“旅行就是要有各种各样的状况,这和交朋友一样,没有完美的朋友。最好有不同的朋友,每个人有不同的魅力,这就像我去北京、上海和台北旅行,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不同的旅行经验”。一个地方吸引她前去探访,最主要的因素不是风景、名胜,而是故事,“这故事可能来自历史、电影、小说、我认识的某个人,我就会想着要去故事的发生地去看看,去找那个故事”。爱看书的她,每一次出发前总不忘选上基本和旅行目的地有关的书,好书是她路上最好的陪伴。 不管走多远,她如今的内心最牵挂的仍是她在东京的家,她的一双儿女。“人去旅行,为的是回来。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始终是最初的出发点即故乡,不然的话就不叫做旅行了,那是自我放逐”。她认为,旅行的开端是寻找世界的入口,比如她当年去北京就是这样。“为了进入世界,你首先得离开家,出门以后才能入另外一个门。只有旅行才能真正找回故乡,紧紧拥抱它。” 旅行、文学、美食,这些深为时下文艺青年或小资白领青睐的关键词是新井一二三写作的几大主题,或许这也是她的作品日渐受到中国读者认同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世界性话题,不同国度不同城市里的年轻人对这些话题的关注是相通的。没想到中国年轻一代对这些关键词这么有兴趣,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写。当然同样是这些关键词,不同作者来写有不同写法不同风格,我的基本写作态度是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我对一个地方或一件事情没有真正感兴趣,就不会去写。我对日本有很深的感情,即使我也写了很多日本社会负面的东西,那就像孩子对父母的爱一样,说什么都是真诚的。” 她在那么多文章中写到日本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雅致、美好,但《伪东京》一书里,关于日本现实社会的种种荒谬、虚伪、冷漠、无奈经由她的时评文字呈现,客观而冷静,极富自省意味。“那些文章最早是给台湾《非凡经济周刊》写的专栏,写的时候没有太多去想正面还是负面。”她说,“我想写的其实是新闻,是东京正在发生的事情。说到新闻,每天的报纸上谈的肯定是负面的消息多。写《伪东京》那些文章之前,我有好几年不写时评。我做过记者,总是遗憾新闻报道作为文章的寿命很短。于是我写了很多像《我这一代东京人》中那样的文章,专门写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文学,我希望借助那些我谈论的历史和文学的生命使得我的文章也长命一些”。 台湾是新井一二三去过很多次的地方。大学时代去台北走马观花待了两天,她当时的感觉很奇怪:“怎么台北街头保留下来的日本统治时期老建筑那么多?连火车站都是。街上卖的很多食物,分明是日式的。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不了解,所以吃惊。那是八十年代初,中日已经建交,海峡两岸的政治环境和今天相去甚远。“那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对待台湾的态度好像有点逃避,故意不去看不去了解。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我们对光复之后台湾的历史知道得很少。一提到台湾,我只想到欧阳菲菲和邓丽君。但到底台湾发生过什么,二二八事件啊白色恐怖啊,根本不了解。当时日本人的注意力都在朝着中国内地的方向。” 她后来读了一些台湾的历史,也读到台湾作家黄春明写日本旅行团去台湾观光集体买春的小说《莎哟娜啦·再见》,“觉得很内疚,心里很难过”。“我后来到台湾好几个地方走了走,发现很多和我同时代的台湾人,生活中有很多与日本有关的东西。这不奇怪,那五十年里很多台湾人去日本读书、工作,我在台湾遇到的很多朋友都给我讲他们家里的日本故事。”在她看来,战后日本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台湾的,而台湾人的生活中却处处有日本的痕迹。“台湾人的眼光对日本也是有些好奇,他们在想,日本到底怎么回事?统治了五十年,就这样算了?为什么没有关心我们?多少有些谴责的意思。” 后来,她看到台湾导演魏德圣的《海角七号》,这部讲述当年日军离台时日籍教师与台湾女子爱情故事,并以今日台湾年轻人的励志、爱情及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为两条线索的电影令她异常受触动,“看了好几遍,每次电影那段主题音乐一响起我就要流眼泪”。魏德圣听说了这件事,笑称“太夸张啦”。“他觉得我看这部电影时的内心太沉重了,其实我是想到很多日本和台湾的过去,想到这些年来的内疚。之前我去过那么多次台湾,却没去过南部,以前看到的所谓台湾人,其实是当年和国民党一起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和台湾南部的原住民不是一回事。”为此她专程把台湾从南到北走了一遍,不止台北、高雄,还有恒春、垦丁。简直是一次《海角七号》之旅。她也见到了魏德圣导演,做了一次长谈,连同那些她写台湾的文章成为《台湾为何教我哭》这本书的内容。 如今在内地、台湾、香港都不乏读者的新井一二三,觉得台湾读者给她最深的印象是对日本资讯很了解,对关于日本的很细微的东西感兴趣。而北京和上海的读者,“好像他们真地把我当成世界的入口,他们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的写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入口的感觉”。她也用日文写作,写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给同胞看。不过她很看重自己的中文写作,“毕竟中国有十几亿人呢,我的潜在读者很多呀”,她笑着说。 虽然当年在北京留学只一年,但她对这座城市颇有感情,说每次到北京都像回到故乡那样的温暖。“那年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她在《我这一代东京人》一文中如此描述北京之于她的意义。她回忆对八十年代北京的印象,“感觉一切都像从零开始,过去的历史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来临,空气中是真空般特殊的自由。当时的中国人好奇、天真、乐观,对外国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我从那时的北京联想到1945年之后的日本。我们是战败国,可是毕竟战争结束了,我们觉得获得很大解放”。1997年她从香港回日本定居,那之后,北京是她旅行计划中的常客,“一般每两年来一次吧,带着小孩全家出动。到处走走,和老朋友聚聚,吃吃饭”。 在她的书中有不少对东京老城区、文化传统乃至具体到一张榻榻米一道点心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灰飞烟灭的嗟叹,而北京这些年令人猝不及防的变化在她看来仿佛循着东京昔日的覆辙。“我越来越不认识北京了,八十年代的景物没有了,连九十年代的黄色面的也不见了。马路越来越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走在北京街头,哦,这到底是北京还是新加坡?”针对记者“为何不写一本关于北京的书”的建议,她表示,“我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抽一段时间住在北京,我当然愿意写一本关于北京的书。” 专事写作的新井一二三对文学始终情有独钟。日本的作家中,流派众多、大师纵横,她喜欢明治时期大作家森鸥外的作品,连带着也读读同为作家的森鸥外之女森茉莉回忆父女情的《父亲的帽子》。对于“日本最有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她则是从他出第一本书一直读到现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村上了,虽然他比我大十几岁,但他的小说还是让我有同时代人的感觉”,她还记得少女时代去书店买不同封面装帧的《挪威的森林》时那种单纯属于阅读的美好感觉。 学了这么多年中文,也写了这么多年中文,她对中国作家的作品相当熟悉,特别是五四时期的那些作家。“刚学中文的时候读鲁迅、老舍和巴金的书,我是一边读一边学,印象深刻。”有一天,她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一本张爱玲的书,“初读到张爱玲的文字真有一种惊艳的感觉,那是和鲁迅不一样的文学,她所表达的观念和审美也不同于我之前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记得书中有个短篇《心经》,是写一个女孩和她爸爸、妈妈的关系,那几乎是最让我难忘的中文作品了”,她说,可能自己那时刚开始学中文,也还年轻,正是内心敏感的阶段,“张爱玲作品散发出来的气质特别让我着迷”。 结束了这一次的中国行程,她又将回到她“和山口百惠是邻居”的家,像是又挥别一次旅行,从出发点又回到世界的原点。她说,她平日的生活和写作相当有规律,“周一到周五我有三天在明治大学教中文,其余两天在家写作──早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四点”,其余时间她还要做回家庭主妇,陪两个孩子成长。 写了这么多年,她的状态很平稳,从未有过文字枯竭写不下去的瓶颈期,“写作是我的职业,就像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病人,怎么会说没有灵感而不给病人治疗”。目前,内地的《万象》杂志仍可不时看到她的文章,她还给台湾《联合报》写时评专栏,“多是写日本震后的话题”。她一点也不担心专栏写作对交稿时间和文章篇幅的限制会阻碍她的灵感发挥,“不同篇幅写出来的文章有不同的形式,表达不同的内容,就像诗歌不也分俳句与和歌嘛。写专栏的限制有时候是好事,跟玩游戏一样,在规则里面玩。规定写一千字,我就在一千字里玩。如果有人约我写一万字,我就把想说的尽情写出来”。有趣的是她的先生也是作家,“他主要写鬼怪小说,他不懂中文,所以无法介入我的写作”。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3月28日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