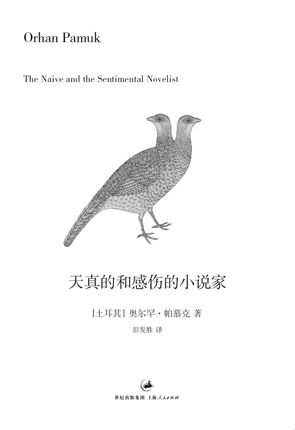四年前的秋天,土耳其大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接了个从剑桥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去哈佛大学作诺顿讲座。没隔多少日子,他们在纽约的餐桌上敲定了这件事,甚至具体到讲什么怎么讲等细节。这似乎意味着帕慕克对此并非全无准备。毕竟写作多年,佳作不少,赢得国际文坛与世界范围读者的认同,荣誉柜里更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一长串桂冠……他对文学的虔敬与痴迷与日俱增,对前辈作家作品的尊重和解读并行不悖,他把写小说视为一门手艺,把读小说看作折磨和享受兼有的精神体验,阅读与写作在他眼中有着微妙而不易言说的关系。这些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态度、观点恰好构成他登上哈佛讲台与人陈述、分享的部分,像吐丝似地,编织成这本《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在中国问世的十一种帕慕克作品中译本中,《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恐怕是篇幅最精短、开本最袖珍的,却不是最容易阅读、消化的。事实上,作者在脱胎于六场演讲的六篇文章中,将自己对文学、阅读、写作的认识以相当的诚意和盘托出,也许他的表述态度还算放松,但内里隐含的观念、思考实在需要一边读一边不时停下来走走脑子。由于帕慕克在书中谈到多位他个人欣赏的作家作品,也难免捎带上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些看法,使得这本书有了强烈的个人化气质。对读者来说,这种个人化意味着某种阅读门槛——如果你不熟悉帕慕克,如果你没怎么读过他的作品,再或者,你对诸如简·奥斯丁、博尔赫斯、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其人其文知之甚少,那显然你不在这些演讲的倾诉对象之列。 写作是帕慕克的职业,阅读则几乎约等于他的生活。“小说是第二生活”,他用这句话开宗明义,无疑为他的文学生涯平添几分宿命色彩。他对感知和探讨文学之于生活的蛊惑力量孜孜以求,乐得沉浸在现实和虚幻的模糊界限里,这可真是个矛盾的差事。就好像,他在书中提到席勒把诗人分为两种:天真的与感伤的。这除了为该书贡献了书名之外,也令他最初的写作总是纠结于“天真”与“感伤”间的平衡上。小说来源于生活,小说中所写的并不等同于生活,阅读是游离事外还是该带入感情?帕慕克更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带向那些我们尚且无法预料的地方——也许就像一部真正的小说”。 但达到这种阅读的理性谈何容易,特别是面对一部情节曲折、笔法高妙、动人心魄的小说时。除非读者从不曾对阅读倾注感情,那是读者和作者的双重遗憾。《纯真博物馆》出版后,帕慕克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这一切真地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帕慕克先生,凯末尔就是你吗?”显然,他们当真了。对此,帕慕克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小说终究是虚构的,不过他也承认,“愿意读者相信故事及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因为“小说写作的艺术就是要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相互矛盾的愿望”。只不过,从古至今,能够在虚构属性与现实映照上达到合理平衡的小说是少数。这或多或少揭示了小说的本质与阅读的意义所在。此外,帕慕克在书中提到非西方的小说家们往往“希望利用虚构性作为抵挡政权压制的盾牌”,同时藉此传递出内心所认为的某种真理。这听上去是不是有些玄妙? 有意思的是,帕慕克在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纯真博物馆》出版后,他路遇一位老友,沿着小说中写到的伊斯坦布尔街道边走边聊,走到一座清真寺前,老友以为帕慕克到家了,而那只是书中人物的住址罢了。现实与虚构夹缠不清至此,也算一桩笑谈。读小说与写小说,就在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辗转,这之间的猜测、品味、印证的过程,就是文学作品带给人的美好所在。由此,帕慕克列出这世上两类需要警惕的人,拿小说当真的绝对天真的读者和视文本为全盘虚构的绝对感伤─反思性读者,“他们根本体会不到阅读小说的乐趣”。 可能是经由演讲记录整理而来的缘故,《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虽然重在说理且言辞洋溢思辨性,却仍然延续了帕慕克在他的小说和随笔中常见的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风格。他的用意不止在陈述,现场听众和隔着书页的读者与他的互动程度有别,这大概也是他的作品中极富交流倾向的一种吧。 写了35年小说,早已是成熟、从容的作家,时时有从写作与阅读中体验到的乐趣和总结出的道理,这是文学带给他的快慰。这种快慰中肯定包含天真和感伤,也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未来的写作,那会是一种无限接近现实的虚构式写作。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10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