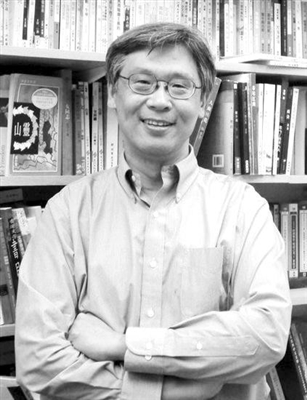王德威从社会、文化和意识的效应上寻找历史错综复杂的意义。他怀着歉疚的心情,为他负面的叙述表示不安。作为一个史学家或诠释学家,太多的谦卑、同情和哀矜,会不会改变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质?模糊了史学和文学的焦点?会不会是一种对历史不自觉的崇拜,甚至畏惧? 王德威采集作家生平的“事迹”和他们的“信仰”作为论述的根据,没有丝毫怀疑,且相信他们的作品都是历史的代言,这样写出的历史即使悲壮如史诗,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盲点。 一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景有一段有趣的对话。王子哈姆雷特向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说: 哈:你看见天边那片云吗?它简直就像一只骆驼。 波:哎呀,它的确像一只骆驼。 哈:我觉得它倒像一只黄鼠狼。 波:它拱着背,正像黄鼠狼。 哈:可也像一条鲸鱼呢。 波:真像一条鲸鱼。 宫廷里逢迎拍马的闹剧我们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这次莎士比亚的幽默撞开了真理的大门,让我们看见人心的万花筒,丢开了是非对错的指责,令人绝倒!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2004)是一部有关历史和历史诠释的著作。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他告别了传统的史学,采取新历史主义所惯用的手法,从社会、文化和意识的效应上寻找历史错综复杂的意义。要理解中国近百年来涕泪交零、充满血腥和创伤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以怪兽为名,以种种不同的形象,包括梼杌、魔鬼、困兽、爱欲、幽灵以及死亡等等,吊诡地见证了我们苦难的时代,刻画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学面貌,替中国现代文学史做了一个严肃的回顾。他虽自称此书的立论包含现代性(modernity)和怪兽性(monstrosity)二者,但他绝大部分的篇幅用在“充满恶行恶状”的一面,很少把笔墨花费在现代性的解读上。虽然他也描画了历史曲折的道路,他却怀着歉疚的心情,为他负面的叙述表示不安。一如上世纪50年代台湾作家姜贵的小说《旋风》(原名《今梼杌传》),以梼杌为名,以恶为书写对象,蕴含不祥的预兆,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同样也是满目疮痍,令人不忍卒读,几乎成为暴力论述和政治争斗的延伸,难怪让他生起了近乎基督救世的哀矜之心,甚至怆然涕下的诗人情结。 王德威以宗教家和诗人的情怀书写历史,使他脱颖而出,而他丰富的同情心和民胞物与的仁厚,不唯感动了读者,也让文学在他笔底取得了生命,产生了意义。《历史与怪兽》以文学的主题作为分类,巧妙地烘托出历史的形象,并为作品和作者赋予历史的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独树一帜。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提出两个问题,希望认识他历史的视野和对文学诠释的态度。 从他的《小说中国》(1993)到《如何现代,怎样文学》(1998)到《历史与怪兽》(2004),王德威用文学的素材作为历史的见证,颇具成效。在最后一书中,他更呈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历史自觉性和文学诠释的努力。但由于中国近代政治复杂多变,华人无限制向海外扩散,要看清中国历史和文学的面貌,其困难相较于《圣经》的《出埃及记》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福柯的历史观给了他出路。福柯相信历史的变化,有时不是由于“发展”,而是“转型”,不是由于“延续”,而是“断裂”。在王德威的著述中福柯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中国现代史演变的标准模式。由于传统历史直线式的叙述已无可能,他接受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物,那便是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文学的作品,包含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星马和美洲。换句话说,文本这个“新批评”的旧宠物,此时重回他的怀抱,成为谈论历史时必备的条件。事实上,这正符合他以“小说见证历史”的构想;而在这新的氛围中,他也创造了绝不可少的新词汇:“华人”的“华文文学”取代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学,既满足时代的需求,也巧妙地规避了政治的监视。 然而在文学批评的天地里,除了数不胜数的西方理论外,“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阴魂也始终不散。“新批评”是美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便执文坛牛耳的盟主,在文学批评史上拥有最悠长的寿命。他们的重要人物包括艾略特、利维斯、燕卜荪、布莱克穆尔,影响至今不衰。他们的美学思想偏向形式主义,把作品当做永恒的艺术品看待,不容许时代甚至作者本人的干扰。他们独断独行,私定雅俗,颇有西方贵族和父权专制社会的气势。例如利维斯1948年推出一份号称英语文学“大传统”的书单,强作取舍,替历史做人为的断案,招来不少物议。当时年少气盛的夏志清在他影响下,也有意给中国现代文学建立一个大传统,而他“筛选”的风波至今还鼓荡在我们文学的圈子中。 但王德威没有这一学派高蹈的气焰。他谦恭儒雅,实事求是,继承了新批评主观经验的优点,却避免了形式主义唯美的弊病,也不以权力意志为尚,诸如开书单、定高下这些不合时宜的行为。恰巧相反,他相信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不论好坏,都有存在的理由。他宁可自己不说话,让作者自己说话,让作品见证时代;他的主观是理性的、诠释学的、意识形态的,对当代文学多元面貌的认识应当有决定性的帮助。 二 文学批评最紧要的,不是用更多的工具去掌握文学、更犀利的武器去征服文学,而是有足够的预设条件去了解文学。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主观的学识、涵养,包含个人的信仰、见解,甚至猜测,只要至诚不息,都能像哈姆雷特的观察一样,给人提供思考或者接受的选择。根据诠释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意见,偏见带来错误和发现;因为有错误,我们才有批评,才有更广阔的视野作为诠释的张本。但在这些考量中,个人的好恶,对是非、善恶、暴力、创伤等的伤感或同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重要。 然而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序言中的一段话令人感到意外: 我的研究因此充满谦卑的心情。逝者已矣,生者何堪。正因为暴力和创伤已经发生,无从完全救赎,也无从完全被“取代”或“再现”,后之来者只能以哀矜的姿态,不断铭记追念那创伤,而非占有那创伤。 如果从诗人的角度看,他的哀矜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史学家或诠释学家,他的不安和谦卑实是多余。他的诚恳令人感动,但太多的同情使他显得软弱。历史在乎的不是如他所说的谦卑、正义、是非等等的命题,更不是宗教性的救赎。历史当然重视过去,但更关心人们的今天和未来。婆罗洲的猿猴哪里需要历史;它们拥有今天,早已忘了昨日,对明天也毫不关心。历史是人类独有的观念,个人的视野与历史的视野已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也是我们切入历史、评论历史时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也都从这种视野的融合中得来。刘勰所说“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文心雕龙·史传》)的话不是空话,而是我们生命中无可推卸的责任。尼采说得好,“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在这里,我们担心的倒不是个性强弱的问题。太多的谦卑、同情和哀矜,会不会改变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质?模糊了史学和文学的焦点?会不会是一种对历史不自觉的崇拜,甚至畏惧?历史的力量虽然庞大,却不是我们的敌人,更不是洪水猛兽。正像尼采所想,“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他们感到不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历史写过往,文学写未来”,今天虽已不再适用,王德威把这二者密切结合,用诗人和宗教家的热忱撰写历史,评论文学,读者想知道的,不是他写什么,而是他藉以取得读者信任的条件是什么?个人的意见固然重要,但终极的判断还在历史。例如在“诗人之死”一章中,他罗列了一长串自杀作家的名单,从朱湘到王国维,从老舍到闻捷,从施明正到顾城,把他们纳入“共同的宿命”、“殉难”,或者“一门忠烈”这一类振振有辞的名目中,并把这一笔账全都记在政治备忘录上,完成了他可歌可泣的《历史与怪兽》的主题。 然而自杀是一件复杂的私人行为,除了殉情或畏罪,自杀的理由可以千变万化,出人意表。就以王国维来说,王德威虽然对他有高度的了解,知道他许多致死的原因,例如对尼采、叔本华哲学的浸润,对传统的依恋、对末世景象的观照,但他仍然说: 即便如此,王国维之死或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触动今昔学者的心事。他的必死之志,与其说是来自家国世变,无以为对,更不如说是来自千古文化危亡之际,所引起的大忧伤、大绝望。 这些话可能都是事实,但除非他透彻掌握了王国维的身世,他的评语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自杀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可能有许多,而近因却常因近在眼前,被人忽略。王德威当然知道罗振玉其人,可能也读过周作人 《罗振玉这学者》一文(原载1964年香港《新晚报》,署名岂明,未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文中周作人谈到罗、王二人纠缠一生的私人恩怨: 溥仪《我的前半生》说罗振玉是个古董字画骗子,逼死了王国维,还假造“遗折”。……绍英托王国维替溥仪卖字画,……罗把债款全部扣下,……王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即使这个故事并不担保正确,王德威给王国维的评语,虽然大体说得过去,仍嫌下得过早。 自杀的前因后果,交叉牵制,很难有斩钉截铁的定论;只是太多的疑点,会不会让王国维昆明湖的自沉,和王德威所说“千古文化危亡”的“大忧伤、大绝望”之间,拉开了一点距离?而他“义无再辱”的必死决心,会不会也有可能是他对自己一生卑屈和忧郁沉疴的交代?培根早在1605年便说过,诗人写历史,其弊害在误导、夸张;给历史添加道德的成分;且常把平凡的故事渲染成不平凡。培根把这种历史叫做“杜撰的历史”(feigned history),并非危言耸听。 像这一类的问题很多,是我们谈论作家时必须防范的陷阱,想来也是新批评一派不愿谈作者、只谈作品的真正原因吧?放下有目共睹的作品,而抓真假莫辨的作者,难免会做出可疑的结论,或者写出歌功颂德的谀墓文。王德威采集作家生平的“事迹”和他们的“信仰”作为论述的根据,没有丝毫怀疑,且相信他们的作品都是历史的代言,这样写出的历史即使悲壮如史诗,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盲点。且看十七世纪英国历史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吧。他的《利维坦》(Leviathan,或译《巨灵论》),取名于《圣经》里一匹庞然巨兽,说是十七世纪版本的《历史与怪兽》也无不可,写尽了英国内战期间政治的丑态,宗教的昏暗,人性的罪恶。他不唯不为此愧疚,相反地,他坚信他的书会传之久远,而他的言论有益来昆,因为他所写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抽象的权力(the Seat of Power)”,易言之,就是永恒的真理。的确,霍布斯得到后世的景仰,正在他摆脱了对历史盲目的崇拜,用超然高举、直言不讳的勇气,带领人们走向希望的明天。这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高标和尊严。 三 王德威以历史为主轴,不惮其烦地重述小说里的情节,略过文本的分析和作者在艺术上成败的判断,虽然叫人遗憾,我倒觉得有一个可以谅解的理由:我们近代文学史中,如果真有可与莎士比亚、奥斯汀,或者曹雪芹比美的作品,我不相信他不会聚精会神,替它们做最详尽的解读,享受老饕过屠门而大嚼的痛快。然而我们现代的文坛令人气馁。在王德威心目中它虽然“众声喧哗”,够得上热闹,从文学的高度看,却有一段距离需要征服。即使王德威像夏志清先生一样,也愿意替我们筛选一个大传统,他到哪儿去找那金碧辉煌的宝山,做他挑精捡细的工作呀?利维斯在谈笑间替英国文学塑造了一个大传统,夏志清左右逢源,也替中国文学拟订了他心目中的大传统,不说别的,他们手头取用不尽的资源便令人羡慕。王德威面临的时代,跟他们相比,并不相似。在《罪与罚》 一章中,他谈到丁玲、周立波,在 《革命加恋爱》 中,他谈到茅盾、蒋光慈、白薇,在 《伤痕文学,国家文学》 中,他介绍了端木方、马烽、西戎。除非一个对历史或政治有兴趣的读者,他们的著作,如从艺术或思想的角度出发,泰半令人失望,至少很难让人有一读再读的勇气。就如茅盾的“名诗” 《留别》,若不是王德威一再鼓吹它隐秘的“深意”,认真做“寓言式的解读”,从“一切都完了!完了!”这样粗糙可笑的诗句中,我们实在看不见诗人的真情,更不用说艺术上的成就了。我们不能轻易抹杀茅盾文学上卓越的成就,但并非一切出自他手的文字都是登峰造极的神品。 如果说美学不是王德威的重点,我们姑且不论,但像这一类过分做作、缺少生命的作品,包括白薇的《打出幽灵塔》、蒋光慈的《野祭》、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能否以他们虚假肤浅的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的见证,恐怕还有磋商的余地。这个王德威在书中绝口不提的问题,实是一个严重的文学和文学史的问题,攸关作家和文学的素质,决定我们当代文学的地位,影响我们文学的未来。虽然在《罪与罚》一章中论及丁玲时,他曾简短地问道:“丁玲可真能言所欲言?”但他关心的是正义和道德之间的冲突,最多不过提出“做了女人真倒霉”(《小说中国》)这一类偏离文学的话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悲剧,是作家的炼狱,是暗中腐蚀我们文艺天地的元凶,王德威的沉默,的确难于理解。在动乱的时代中,作家可以写出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透过艺术和思想的升华,把历史转化为永恒的象征。可惜我们的作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在波涛汹涌中,稍一露脸,便黯然消逝,既不能照亮我们的暗夜,也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书绅的教训,或者创造出令人念念难忘的时代悲喜剧。读毕《历史与怪兽》,阖上书本,不由得不让人感到一阵子喧哗背后的冷清! 我们再看看王德威所引夏济安评蒋光慈的话吧,夏济安可谓搔到了痒处: 夏济安曾指出,像蒋光慈这种“才疏学浅之辈,除了二十世纪之外,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任一朝代跻身于文坛”。在夏的笔下,蒋光慈不仅肤浅滥情,自鸣得意,而且是“浪漫主义最喧嚣的鼓吹者,亦是浪漫主义最可悲的讽刺”。 这话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坛中捉襟见肘、不可思议的窘态,从夏济安锱铢必较的一贯态度看,这无疑是我们文学批评界缺少标准和把关后必然发生的灾情,他说此话时沉痛的心情,溢于言表。但王德威自己却说,“蒋光慈能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只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的怪现象之一而已”,言下之意,蒋的失败不过是冰山一角,不足为奇,夏济安可能低估了他失败的重要性。王德威自有他不同于夏济安的睿智:蒋光慈能把革命和性作为话题,写下他传诵一时的 《少年漂泊者》《野祭》《冲出云团的月亮》,替小说界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也是一种贡献,至于“他的作品好坏如何”,则是次要的问题了。夏济安的文学标准显然不同于市场上畅销书的标准,但在王德威眼中,如果畅销书能够制造“众声喧哗”的效果,给文坛带来热闹,即使是“反面的教材”,作者的“一无是处”也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了。 王德威如果真的认为这些小说家在“以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小说为范例”,进行认真的创作,他有没有想到,为何他们的作品,不论他怎样辩护,就是缺少真实的生命,见不到半点“写实”主义的影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无情的浪涛把他们打得无影无踪,更不用说追踪托尔斯泰,比美巴尔扎克,挑衅福楼拜,成为时代高耸的里程碑,辜负了我们伟大时代的托付!王德威虽然替作家们戴上了体面的高帽子,给了他们由衷的声援,然而他怎能满足于这些“才疏学浅”之辈和他们“肤浅滥情”之作,而梦想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呢? 王德威自己很清楚,像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缺点重重,夸张煽情;蒋光慈的《野祭》,陈腔滥调,亵渎了爱情的神圣;连著名小说家丁玲也不例外。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写农家女贞贞被日军强暴,事后决心“为国捐躯”,做日军军妓,套取情报,结果换来一身病毒,虽遭村人不齿,仍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像这种生硬不自然的故事,不论它是否有美化妓女之嫌,王德威对贞贞“心身表里不一”的指责,暴露了作家对人性认识的欠缺,而他们的作品也都一一葬送在自己浅薄无力的手中!这些作家所暴露的贫血现象,跟夏济安所说的文坛窘态,其实如出一辙。王德威终于接受了夏济安对文学严肃要求的原则。 至于台湾的施明正,我们对他当然有英雄式的敬仰和怀念,但他为自由民主的捐躯,和作为现代主义先驱者的尝试,是他短短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两件大事,必须给予分别的处理,方见公允。王德威毫不吝啬地给了他尼采的智慧,波德莱尔的光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魅力。戴上如此辉煌的桂冠,施明正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世界级文豪,不用说台湾本土文学的佼佼者了。但读过他书后的人,在艳羡仰慕之余,对王德威的评语难免有些沉吟,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叹息他英才早逝,同情他“兽的苦闷”,体会他监狱中“渴死者”对自由的向往,理解他“魔鬼的自画像”里犯罪的痛快和自责,像这些人性中人人都曾体会过的矛盾,有足够理由让它成为永远的热门书。但事实却不然。就以 《魔鬼的自画像》 来说吧,作者的文笔够旖旎动人,但他的魔鬼却没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威凛,足以挑战老成庄重的浮士德,让他甘愿以生命和他交换位置。究其原因,施所谓的魔鬼,是早熟少年自我膨胀的幻想,纯真可爱,让人遐想,王德威却以万钧之力,把它迅速成熟化,推崇他为跟上帝角力的劲敌,从巴酷斯的放纵,一跃而为西绪福斯的神人,变成了台湾现代主义思想的推手和巨人,叫人摸不清他批评的尺寸和方向。像这样天才的少年之作,虽然震撼了台湾,使人惊艳,但没有进一步的努力,很难傲视人寰,成为世界文学共享的经典,又怎能让尼采、波德莱尔折服,让浮士德拱手称臣呢!王德威的赞美,虽然给了年青一代极大的鼓舞,用心良苦,但不从文本入手,很容易发生与事实不符的结论,让人不敢贸然接受。 事实上,历史不是个人的流水账簿,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时代反躬自问的回顾和检讨。个人的成就当然是珍贵的珠宝,然而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尤其当今天我们华人遍及世界每一角落之际,我们不能不在主流的价值观和环球的思考模式中,一探自己的角色和意义。 王德威的 《历史与怪兽》 给了我们什么呢?除了伤痕和哀矜,他也让我们认识了近代的中国,看见了他心目中的怪兽。他把历史透过文学的介绍,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以诗人优美的语言,宗教家悲天悯人的热忱,把历史和文学做了一个巨细靡遗的转述。至于这场腥风血雨的历史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个可歌可泣的大时代,他却没有只言片语的交待。他也留给我们不少疑问,诸如梼杌这只怪兽究竟象征什么?我们真已沦为怪兽的一环而不自知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怎样的视野和立场?而什么又是他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除了猜测,读者很难从书中得到答案。 四 他把“梼杌”译成“怪兽”说得过去,因为 《神异经》 里“人面虎足,尾长一丈八尺,性喜斗狠”的梼杌,当然不是善类。但如说这怪兽有多狰狞,射影历史上一切的暴力和创伤,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梼杌一词最早见于 《左传》,指颛顼氏的“不才子”鲧,而梼杌二字是人们因为取笑他而送给他的绰号。依照《说文》,梼杌亦作梼柮,或榾柮,就是断木、折木,有“朽木不可雕”的意思。由于柮字读若《尔雅》的貀,梼杌遂从木字偏旁的断木,变成了豸字偏旁的野兽。从《左传》到《尔雅》,“梼杌”从植物变成了动物,从朽木变成了野兽,这种语意学上的变化,一如哈姆雷特的万花筒,既自然又有趣,无关价值的批判,不像“怪兽”二字那样一成不变。 然而不幸的是,也许真是怪兽作祟吧,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有意无意地走上了一个固定的方向,成为他诠释历史、解读文学时挥之不去的阴影,妨害了他运斤的自由。 霍布斯《利维坦》的“怪兽”和王德威的“怪兽”截然不同。利维坦是国家主权、社会治安的标志,不容侵犯;王德威的怪兽却是一个神话里的野兽,是“人与非人的混合”,“模糊了人性所赖以维系的文化及伦理界线”。这虽是王德威评论姜贵 《今梼杌传》 的话,但这阴暗的联想一再窜入他自己的书中,使他画地为牢,跳不出自己的圈限,甚至忽略了他“鉴往知来、敷衍正邪”的预告。跟霍布斯气壮山河、直言不讳的历史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生活需要历史,但历史必须服务于生活。我们读历史,除了了解过去,更要认识今天。我们不是唯一一个遭逢天翻地覆命运的国家。世界全变了,有些国家甚至走到了文化和经济破产的边缘。这是一个环球的、时代性的大纠缠,我们在重建家园的奋斗中,亟需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历史与怪兽》 承担的责任不轻。在人道思想还不疲软的今天,我们唯恐王德威不用尽他诗人的魅力,深沉的思想,替我们血泪交零的历史带来一些深刻的反思,让我们看见历史的曙光,找到奔赴明天的勇气,而不只是谦卑和哀矜。历史精神不死,它的再现,才是我们的慰藉; 而洒热血、抛头颅的悲痛,不能以“魂兮归来!”的一声叹息画为句号。历史不是哲学的代言,是经验的累积,而史学家高瞻远瞩的睿智,像司马迁、刘勰和霍布斯,都是我们暗夜中的北辰。即使错误,也给我们启示。亚里士多德曾经打趣说过,“生命充满错误,在错误中,灵魂才有更长久的生命”(《论灵魂》)。这才是生命的真谛,生生不息的宇宙有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永恒的意义,日日在等待我们耐心的发现。 王德威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弥补了我们文学知识的不足,即使哲学的思维不是他终极的目标,我们不能忘记伽达默尔的忠告,“不管哲学家可以怎样被认为能从一切事物中推出彻底的论断,他都不能扮演预言家、训导者、说教者或者无所不知的角色”(《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历史与怪兽》的“现代性”和“怪兽性”,似乎应从这里来开始认识。至于这部“最完整、最权威的第一手论述” (《历史与怪兽》 封底介绍用语)所暗含的启示,如果有的话,我们寄望在下一部论述中得到分解。 (作者系文学教授,曾执教于美国爱荷华大学、康奈尔大学) 原载:《文学报》2015年7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