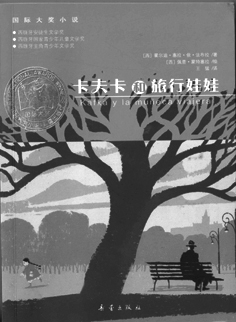2015年3月20日至22日,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开题暨首届汉文古写本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作为项目首席专家的王晓平在会上强调,在国学热的今天,“外学”同样不可偏废。“研究中国的学术要努力,研究外国文化的学术也要加油,而且在很多时候,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各国文化的互通互鉴需要共同的知解基础。”年近七旬的王晓平如今已是白发萧然,推进中外文化(尤其是亚洲文化)交流,是他毕生的事业和心愿。 “作者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比较文学结合起来,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描述中日一千多年的文学交流史,对亚洲汉文学进行一体化研究,拓宽了诗经学、敦煌文学和诗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日本《万叶集》等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注入新的思路,并因此成为获得日本奈良万叶世界奖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论者的这段话算得上是对王晓平毕生学术研究的最好概括和评价。 万叶世界奖是授予对《万叶集》研究与国际传播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学术奖,由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从各国遴选。首位获奖者是一位巴西学者,王晓平属第二位获奖者。日本任教十几年归国后,他先后出版了《日本中国学述闻》《亚洲汉文学》(修订版)《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等著作,其中百万字的《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2014年,王晓平获第五届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 “小时候最开心的是混进老河北大学(今天津外国语大学)那间平房小书店,钻到大学生堆里蹭书读,小说、诗歌、剧本、科普,摸到什么看什么。”多年后,王晓平翻译的第一篇日本文学作品,是著名的动物作家椋鸠十的《大造爷爷和雁》(收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月牙熊》)。在他看来,这种缘分或许可以追溯到那时的杂书乱翻。 王晓平的学术生涯,始于攻读硕士学位之时。彼时正值“文革”结束,思想文化全面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也打开了国人的视野。比较文学更是成为一大显学。尽管他在读研究生时开始与国学和古代文学结缘,但赐予这一缘分的还有他生活多年的内蒙古,尤其是乌兰察布。上世纪六十年代,王晓平到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以北的武川县插队,接触到不同民族的各式民歌,虽不无粗粝浅俗之处,但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原生态民歌,却成为他日后从事《诗经》研究的前缘。七十年代中期,王晓平到乌兰察布草原尽头的一个边防城市工作,不仅因涉足外事工作而常用俄语,而且有机会接触到汉、蒙、满、回等不同民族的文化,感受到不同民族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由此展开看待学术的不同视野。 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文学曾吸引无数研究者投入其中。但在学界同仁眼中,王晓平的比较文学研究却自有其独异之处。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中西(主要是欧洲和北美)比较占据主流,中日(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比较相对而言成果略少。因而,王晓平的研究颇多填补空白之处。 对话 读书报:前不久,您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暨首届汉文写本研究学术论坛上,提到这一项目的任务之一是对汉文写本史料进行抢救性挖掘。可否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这一项目的意义是什么? 王晓平:有学者将各国现存中国汉文典籍称为“汉籍”,而将汉民族以外各民族用汉字撰写的书籍称为“准汉籍”。从总体看来,这两类典籍都是汉文。“汉籍”多保存中国国内已散逸的宝贵文献,“准汉籍”则是中国文化影响东亚文化发展的直接见证,也是研究古代中国与周边各国关系的第一手材料。 汉字手书是汉文化圈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写本(也叫抄本)是中国典籍传播与影响周边文化的早期载体。保存在域外的汉文写本折射出中国文化独特的发展模式和传播方式,是研究我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书法艺术等多方面学问的重要资料。把它们一个不差地“请”回故里,是二百多年以来几代中国学人的一个心愿。汉字的艺术性、创造性和柔韧性是周边各国丰厚写本文化的基础。汉文写本的文献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同时,古写本中还不乏艺术瑰宝。今天,古写本面临岁月侵蚀、残损磨灭、失真失传的危机,一旦失去,无可补救。汉文古写本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对于纠正周边文化研究中轻视汉文化的偏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汉字文化研究也将给以有力的推进。 读书报:中国的写本研究有哪些独特之处?据您了解,西方对写本的研究现状是怎样的? 王晓平:中国传到周边各国的汉文古写本和各国文史写本,不仅使用文字大体相同,而且体例、书写规则等都相同,不仅与敦煌写本同源,而且多属同一时期文献。敦煌写本研究所建立起来的写本学基础,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参照,可以帮助我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各国汉籍珍稀写本进行全面整理。敦煌写卷研究的影响已经使敦煌学成为一种国际化的学术。另外,比如说女书、彝族的文书、纳西东巴经卷的研究,都是中国写本学独特的学术资源。 西方写本学最初主要研究中世纪拉丁文写本,进而扩大到希腊、犹太、阿拉伯和波斯文的原典。像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都保存了众多写本资料。很多国家对于“手稿学”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汉文古写本越来越引起国际学界关注。日本京都大学等学术机构已设立“敦煌写本与日本古写本工作坊”等研究机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在各国积极推动东亚佛教写本合作研究。 汉文古写本研究就是要借用敦煌写卷研究的“钥匙”,借鉴西方对写本物质性和艺术性研究的思路,破解周边各国汉文古写本研究的难题,不放过写本中任何一个传达文化信息的细节,哪怕是一点一画,也要为其清源解密,以呈现中国典籍外渐的历史原貌,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为汉字写本学建立数据库。 读书报:比较文学作为舶来之学,其历史不过几十年,而中国传统的朴学则绵延久远。若以跨越性视角来看,这一中一外、一古一今的两种学问方法能否融通、共生乃至相得益彰? 王晓平:传统学术博大精深,但也还有很大的生长空间,如少数民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的研究。我把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看作是中华学术的“内篇”,把对域外文化的研究看作它的“外篇”,不管是内篇还是外篇都反映中华学术的水准。内外篇研究跟两件事有关,一是与其他的文化互通互鉴,一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两者都离不开对内外文化传统的知解。 对中外文化的真知灼见是我们展开学术对话的第一利器。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朴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语言、文字等基本方面处理好中外文学文献,更重要的是,树立一种重视实证、不尚空谈的学风,使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从天上“空降”到中国文学这块沃土上,更加扎实,更具有与各国学术平等对话的实力。 读书报:您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价值和中国特色,并据此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您本人的“跨文化的新朴学”可否理解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 王晓平:以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一种中学和西学相对的模式,到了21世纪,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我们对于美国学、法国学、英国学、德国学等的关注,可能要比对于所谓整体的西方学术的关注要更多。同时,日本学、韩国学、越南学、印度学等等,或许会获得长足发展。中国学术的双边、多边对话场合越来越多,所谓“中国话语”,也可以说是我们为与各种面孔的对话者面对面的一种本领的准备,也就是那些能从根儿上说清楚中国文学是怎么回事的话语。 汉文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只有拉丁文在欧洲文学当中或许可以比较。实际上,汉文影响持续的时间要比拉丁文长,更重要的是,汉文的影响不是通过武力征伐和势力扩张来实现的。历史上周边各国汉文学,具有多种功能,以文为政、以文为教、以文为礼、以文为戏、以文为艺,比如诗歌就渗透到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等等。这些都跟中国文学渊源很深。汉文学传统在周边各国长期延续,这种现象不是套用现有西方话语能够说清楚的,“中国话语”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中国文学(智慧)与对话者的分享,当然也有对话者文学(智慧)的中国表述。 所谓“跨文化的新朴学”,简单说来就是尊重原典,赋予义疏、义理、小学等传统学术方法以新的生命,并寻求将其运用到对周边以及各国文化的研究中的途径。当然,这只是比较文学诸种方法之一种,而且我更在意的是能有“桃子”可摘,而不是贴上方法的标签。 读书报:中国古代名著《水浒传》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就被多位作家改写,而日本书店里集中摆放的“三国物”则是与《三国志》有关的一切读物,旧时开蒙读物《千字文》在日本竟被推演出数百个品种,在中国被煲成“心灵鸡汤”的《论语》,在日本则早已被改译为经商版《论语》、职场版《论语》、就业版《论语》等针对不同人群的俗译版本。您的研究让我们了解到很多中国古代经典在日本流传演变的细节。这些经典在亚洲其他国家的命运如何? 王晓平: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很多文学经典在日本以外的国家也都有很广泛的流传和影响,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修典藏书的传统。影响最大的是《史记》,朝鲜半岛很早就有《三国史记》,越南也有《大越史记》,日本有《日本书纪》,都是采用司马迁所奠定的纪传体。汉文学直接的模拟对象是中国文学,《孝经》《文选》《千字文》等传入周边各国,而这些国家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也受到中国学界的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具有继承性,那些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今天仍然在不断被翻译、重写,并成为学者常谈常新的话题。 读书报:从日本的“支那学”“东洋学”到今天的中国学,都是日本近代学术的产物,而中国学者对那些受西方学术影响较明显或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产生的成果还不太熟悉。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王晓平:日本研究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它接受西方的影响,采用的论述模式甚至语言都带有西方的特点,但中国学的很多著作也有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就是它也受到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影响,又沿袭了日本学人从小处做足大文章的规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日本汉字研究专家白川静,对中国神话的看法就很给人启发。当然现在日本的中国学界也在不断变化,日本的汉学像20世纪初那样的大家不容易产生了,中国学也存在困境。但是从整体来说,我们还需要深入去做一些了解和介绍工作,这样才能与之展开有效的交流与对话。 读书报:您谈到不仅要认识如《西游记》这样的中国古典名著与日本文化的内在关联,也必须跳出“旧学”的窠臼,探究它们的“世界性因缘”。能否具体谈谈? 王晓平:《西游记》等中国文学经典不光是中国人喜欢,越南、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等很早也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改写。这种改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本土故事汉化”,就是把他们本国的故事按照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和处理方式来写;另一种是“汉土故事本土化”,把中国故事改换背景,变成发生在本土的故事。他们对中国文学的阐释,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我们有必要好好看看,那些我们珍视的中国元素在这些再创造的作品中哪些保鲜了,哪些缺失了,哪些变身了,那些走味了,各国的重写有哪些共性和特点,这对于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会大有启发的。“知同、明异、互读、共赏”,这样,中国文学就可能在世界获得更多粉丝。 读书报:您对日本的诗经学有颇深的研究。在您看来,在异质文化的激荡交会之中,作为中国传统经典的《诗经》,在日本有何吸收与创造? 王晓平:日本现存的中国典籍古写本资料中,以《诗经》和《论语》最多。由于《诗经》兼属于经学和文学范畴,在日本受到儒者和学习词章的两方面人的重视。它被改写成日本的民族诗歌和歌和俳句,一些儒者为了把《诗经》介绍给普通日本人,还把《诗经》改写成散文或短剧,同时利用传入日本的唐宋以前的《诗经》写本来作考证。日本近代以来对于《诗经》的研究,主要受文化人类学者葛兰言的影响,出现了一批有现代意识的研究成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拙著《日本诗经学史》《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以及我主编的多卷本《日本诗经写本刻本汇编》,就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07月22日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