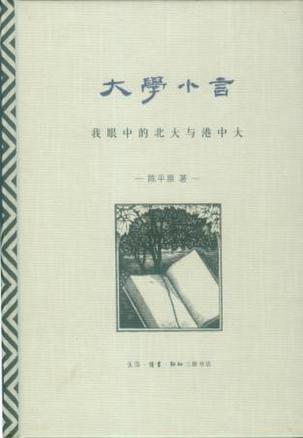 本文摘自《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和港中大》 陈平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7月刊行 今年5月间,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令,参与修订“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简介”和“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会场上,我虽也殚精竭虑,积极发言,却没有多少“神圣感”。因为我知道,这些专家们字斟句酌、仔细推敲的文字,也就是“文字”而已—既不被重视,也无法落实。 说来惭愧,作为北京大学第一批文学博士,我本人深深得益于中国学位制度的建立。也正因此,最近十年,因缘凑合,我撰写过好几篇谈论中国学位制度以及如何培养研究生的文章,如《“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年12期)、《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5日)、《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8期)、《上什么课,课怎么上》(《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2期)、《训练、才情与舞台》(《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3日)等。话是说了不少,可你如果追问,中国博士的水平靠谱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无论哪个国家培养的博士,都有特别出色的,也有拆烂污的,关键是总体水平如何。在没有拿到过硬的数字之前,不好乱说。更何况,我是“土博士”,说低了自贬身价,说高了又成了自我标榜。 让我很受刺激的,是前几年读到的两篇洋博士的文章。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薛涌在2007年1月29日《东方早报》上发表《博士教育到“减灶”时候了》,直指中国大学根本就不适合于培养博士。此文日后成为薛著《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第五章“中国高等教育批判”的一节,题为“博士教育应该外包”。报纸文字有删节,故以下引文出自薛著。“中国的博士生数目,已经世界第一。但博士教育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害多益少。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根本不适宜培养博士。所以我建议:关掉绝大部分的博士课程,借助国外大学培养博士,集中国内的资源把本科生教育搞好”;“博士课程,是西方几百年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晶,不是想学就能学的”(292页)。 另一篇是《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参见《科学时报》2007年10月2日),作者乃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王鸿飞。这原本是一篇博客文章,贴在“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基金委主管,由具有五十年媒体经验的中国科学报社主办”的科学网(ScienceNet.cn)上,随即引起很大关注。王文称:“简单地说,以我在Columbia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所在的研究所和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内地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鉴于大家对99%或97%的估算的异议很大,但对90%异议不大,所以把标题改为: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读科学网上的争辩文字,竟然有不少人认为王文在理,只是不该说得那么透彻、那么决绝。 我不同意两位洋博士如此悲观的大判断,但承认中国的博士培养问题多多,听听些“盛世危言”不无好处。王鸿飞的博文本就是针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将要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新闻而发的,称“早就该加紧整顿了”。具体承担此调查任务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带领的课题组,三年后终于拿出了两项重要成果:《中国博士质量报告》(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陈洪捷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很可惜,二者的珠联璧合、联袂登台,并没有消除我对“中国博士”质量明显下降的疑虑。 陈洪捷等著《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分五章,其第二章“中国博士质量的实证分析”称:“课题组向289所博士培养单位发放了大量问卷,回收有效学生问卷20666份,导师问卷9928份。”(80页)依据这些问卷,课题组选择了课程体系、培养环节和能力素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博士生自身和导师对我国当前博士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是较好的,总得分超过了70分。”(89页)为了祝贺《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出版,课题组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光明日报》还专门刊发了相关报道。以下引录的陈洪捷教授答记者问,皆出自于此:“对于我国博士培养的质疑,媒体的报道或个人的意见虽然都有根据,但许多是以个案覆盖全局。这样的报道和说法容易误导大众,使大家误以为我国的博士教育一团糟”;“中国的博士培养质量整体上是乐观的。我们对9928名博士生导师的问卷调查表明,接近50%的博士生导师认为我国博士毕业生在‘学位论文质量’、‘科研能力’方面的质量是‘提高’的。另有40%多的博士生导师认为我国博士毕业生的‘学位论文质量’、‘科研能力’是‘持平’的。”(参见刊于《光明日报》2011年1月6日的李志伟《“中国博士整体质量是有保障的”—访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陈洪捷》、靳晓燕《大部分导师认为: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乐观》) 我不知道中国教授及其指导的博士生的自我评价(假定抽样合理、填表认真),能否抵挡住人们对于中国博士质量低下的责难。即便就像研究者所称,90%的博士生导师认为中国博士教育水平或“提高”或“持平”,也没有回答两位美国博士的质疑,即相对于美国三流大学,“中国博士”到底行不行。 其实,“对于我国博士培养的质疑”,并非只是媒体的捕风捉影,也不仅仅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最初关注这个问题,是因读到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发表在2005年4月7日《文汇报》上的《关注博士生培养的过度教育现象》。文中提及中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超常规增长:“2000年全国博士生招生数为25142人,2004年博士生计划招生总规模已经达到53096人”;“美国博士教育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十多年来,全美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一直保持在4万人左右。我国2004年博士生招生数已经达到5.3万余人,比2000年增加2.8万人。再考虑到我国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近乎‘零淘汰率’,预计我国博士学位年授予数量将会接近美国。”岂止是接近,很快我们就超越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博士生招生数量居然可以四年翻一番。 大概正是因为王校长等人的大力呼吁,才有了2007年的全国博士质量大调查。很可惜,此项大张旗鼓开展的调查,结论竟然是“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乐观”。从1978年中国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到如今每年二十多万在校博士生,“中国的博士培养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腾飞式的发展”,这确实值得骄傲。可我还记得这么一条消息—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现任复旦大学校长)曾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透露:中国有本科授予权的高校700多所,美国1000多所;而中国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则只有253所。为何如此?因为“我国目前培养的博士生有一半的就业去向是做公务员”,故需求十分旺盛(参见《全球第一:中国博士培养规模势不可挡》,《科学时报》2008年5月13日;《中国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去当公务员》,《东方早报》2008年4月30日)。正因“博士们的职业选择并不是人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作科研”,其水平高低,你就不太好用传统标准(比如学术业绩)来衡量了。这一很有“中国特色”的转变,确实让人措手不及。在美国,“除了学术领域外,一般很少有工作需要博士学位”;因此,美国聪明的大学生大部分不会读博士课程,总统、州长、议员、总裁中挂着博士头衔的也很少(参见薛涌《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296—297页)。而我们的情况则相反,若真的有一半“中国博士”不在学界而在官场,这的确让人啼笑皆非。 这也就难怪,虽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中国的博士教育还是在大踏步前进。手头没有今年全国博士招生总数,但看看各大学情况,也能明白大致趋向。我见到的是2011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前十名分别是:浙江大学1559,北京大学1526,武汉大学1355,吉林大学1275,华中科技大学1244,清华大学1231,上海交通大学1185,复旦大学1132,中山大学1057,四川大学997。据上述王大中文,美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两所,其中培养规模最大的是UC-Berkeley,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约750人(《关注博士生培养的过度教育现象》)。换句话说,中国大学博士生招收数量排名第十的,也比美国排名第一的多(不能想象四川大学每年有250名博士生被淘汰)。 有感于此,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2009年2月26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大声疾呼“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且主张“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理由是:“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各大学之所以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来赢取博士学位授予权,就因为这其中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校长们无法抵挡如此巨大的诱惑。 观察教育部近年决策的大趋势,是逐渐放松管制—最近一项举措是允许民办高校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参见《民办高校可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2日)。政府若真下决心“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自然是大好事;但民办高校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短期内希望渺茫。倒是各地众多公立大学持之以恒的“争创博士点”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更值得关注。 半年前,我在《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16日)中提及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梦想,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锲而不舍的努力,使得中国大学终于能够培养各行各业的博士,年轻人不一定非出去留学不可了。后面有这么一句:“表面上,这个梦想我们早已实现了,如今每年中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世界第一—质量有无保证、是否‘过度开发’,则另当别论。”本文的写作,正是为了回应此伏笔。 以我对中国社会及中国政治的了解,王大中先生委婉的劝说—“促进博士生教育的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没有任何效果;刘道玉先生猛烈的抨击—“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更是无法实行。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大学里的博士点及博士生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教育部愿意且能够做到的,只是控制“增长速度”。因此,我倾向于改良主义立场,抱怨之余,提若干“建设性意见”: 第一,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也就是说,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目前中国的“博士学位”属于国家,而无论教育部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监管到位,长此以往,“中国博士”的声誉只能越来越低。在学位授予权方面,教育部不妨守住底线,基本放开,允许各大学进入竞技场,参与搏杀与竞争。若干年后,那些博士学位基本没人要的大学,就会反过来努力办好本科教育。 第二,正因为我们是国家学位,无法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并共同颁发学位。改为大学学位后,中国各大学乃至各院系,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与国外著名大学结成同盟,迅速提升自家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中国有好教授,但数量远远不够;而众多“不合格的教授”正大批量地生产“不合格的博士”,现有的体制又根本卡不住。这些“不合格的博士”放出去,很快就会占据要津,形成一时之风气,阻塞学术发展。引进外来的制度及资源,可以让我们把路走得更顺一点。 第三,因为是大学学位,允许各大学每年通过授予名誉博士方式,报答那些为人类、为中国或为本校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商人以及政治家—香港各大学就是这么做的。这比让大批官员或商人装模作样地走进校园,瞒天过海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要好得多。学生们很精明,一看你校长及教授为权势及金钱而“开闸放水”,即便嘴上不说,也都从此失去了对于学问的敬畏之心。依我浅见,为了纯洁校园,多颁几个名誉博士问题不大。至于说靠提高招生门槛、严格论文评审来保证质量,那都是说给外行人听的。今天中国的大学校长及教授中,愿意结交权贵及富豪的,比比皆是。只有从制度上彻底杜绝官员读博(除非脱产),才可能解决“真的假文凭”问题;否则,单靠个别有担当的院系领导来扛,根本扛不住。 第四,目前中国的博士培养,有资格考试、匿名评审、公开答辩等制度设计,表面上层层设防,很严格,可实际上守不住。教授们之所以“心太软”,放任不合格的博士生毕业,一是没有合适的退出机制,学生已取得了硕士学位,又多念了几年博士课程,若资格考试或论文答辩不过关,真的无处可退;二是各校普遍要求不严,竞相放低门槛,你若鹤立鸡群,只能耽误自己的学生;三是教授缺乏经验—我说的是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者,至于习惯徇私舞弊或本就不合格的,另当别论。指导博士生,本没什么了不起;但教书毕竟是一门职业,需要某些技巧,没经验的就是做不好。这方面,教育部可以有所作为,如为新选拔的博士生导师或新设点的大学的教授们开设专门的培训班—如果嫌“培训班”不好听,不妨叫“经验交流会”。此举起码可以让那些愿意学习的博士生导师及其学生,少走一点弯路。同时,呼吁各大学的校长为教授们保留一点颜面,不要再将“教授”、“博导”当礼品胡乱赠送了。读《南都周刊》2012年第48期(12月17日)刊登的《学者王立军》(主笔季天琴),看一个初中学历的转业军人,通过自考与成教获取了中专与大专文凭后,如何因官职提升,相继成为29所大学不同专业的兼职教授甚至博士生导师,你就明白今日中国大学的乱象。 第五,建议若干著名大学结盟,确定相对统一的学制。目前北京大学培养硕士、博士的标准年限是三年、四年,而国内不少大学的学制是二年、三年。同样才华的学生,念五年与念七年,效果肯定不一样。理科生不愿意学制太长,是担心导师扣着不放,要其帮助做实验;人文学没这个问题,应允许不同院系采取灵活姿态。在我看来,读人文学的博士,确实需要更多的时间熏陶与沉淀。 最后一条建议,牵涉教育主管部门:目前各大学在岗的中年教师,许多已有教授职称了。若非常出色,任其自由发展;若不太出色,也可在职进修—没必要回去补拿博士学位。这本来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过些年就自然解决了;现在各大学招聘的年轻教师,全都是博士。今年春天开始的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在确定指标体系时,我强烈要求删去“教师中博士比例”这一条,最后实现了。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祛魅”,也不要“污名化”,认清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对于希望进入学界的人来说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12年11月24日初稿,12月20日修订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