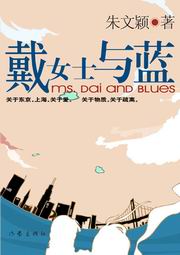 朱文颖的长篇小说《戴女士与蓝》是一部相当正规的小说,“正规”这种说法可能让人费解,什么叫正规?什么叫不正规?这是就小说的主题、叙述方式、人物、情节与细节而言,它没有什么出格的东西,不是
一部叛逆性的前卫作品,或者是一些展示女性的怪异经验奇文野史。作为一位人所众知的女性作家,朱文颖甚至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一个男人的视角,用男性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来讲述故事,显然,女性的经验被有意地克服和掩盖了。一个伪装的男性的视角,一个女性书写的男性故事,并且是男性关于自我的故事——这些由记忆、反思、辨识等构成的故事,它真正远离所谓的女性主义。这也是一次告别的写作,一次写作的成长史的新纪元。 朱文颖的长篇小说《戴女士与蓝》是一部相当正规的小说,“正规”这种说法可能让人费解,什么叫正规?什么叫不正规?这是就小说的主题、叙述方式、人物、情节与细节而言,它没有什么出格的东西,不是
一部叛逆性的前卫作品,或者是一些展示女性的怪异经验奇文野史。作为一位人所众知的女性作家,朱文颖甚至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一个男人的视角,用男性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来讲述故事,显然,女性的经验被有意地克服和掩盖了。一个伪装的男性的视角,一个女性书写的男性故事,并且是男性关于自我的故事——这些由记忆、反思、辨识等构成的故事,它真正远离所谓的女性主义。这也是一次告别的写作,一次写作的成长史的新纪元。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一个从日本打工多年回国的男子,在面对现在无忧无虑的女友时,不断回忆起在日本的生活,在日本与女性交往的故事。小说以现在的上海和日本二条线索为展开的二元结构,但大量的故事是关于日本的经历。小说中的“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国潮中靠借了一笔款到日本,但在那里只能靠干最低级的苦力谋生。先是打捞海洋馆里的鱼类留下的粪便,随后扮演起死去的鲸鱼。“我”的故事中包含着二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是在超市里打工与“我”同居的女子,另一个是在海洋馆里与“我”一起扮演鲸鱼“星期五”的女人。故事的落点在,那个与“我”天天在海洋馆里扮演鲸鱼的女人,始终未能除去面具见面。多年后,在上海邂逅戴女士,“我”认定这个已经成为健美教练的戴女士,就是当年在日本与“我”一起扮演鲸鱼“星期五”的那个女人。但这个戴女士根本不愿意承认过去的经历,我也无法断定。我陷入精神的困境,离开了现在的女友陈喜儿,结果陈喜儿自杀身亡。 这个故事是想观看,人在远离故土或“家”时的那种精神孤独,以及由此带来的爱情与忠诚问题。 这部转换成男性视角的小说,对男性性格和心理的把握相当出色。小说的主人公,也就是叙述人“我”,他在日本的那种艰辛和困苦,回国后的那种茫然和空虚,不能走出生活历史记忆的那种状态,这些都显示出朱文颖对小说情境和氛围的营造方面的技巧。事实上,男性视点并没有压抑住朱文颖的女性经验,女性的视点还是不可抑制地显现出来。小说写的那几个女性,那个在超市打工的女子,他们同病相怜的境况,颇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虽然是身体的共同需要把他们苟且在一起,但那种生存状态就显得凄楚动人。她的桌上就摆着一家三口的合影,她的丈夫站在照片中央,一家三口在照片中抱成一团,都在笑。然而,在日本,这个远离家的异国他乡,这个女子与“我”这个男人相遇,并没有多少爱,但就是需要,我“就在那遥远的笑声里解她的扣子,然后和她滚作一团……”那个女人后来做了暗娼,离开了“我”。这里可能涉及到爱与忠诚的问题,但这些观念性的命题,家庭伦理与道德在这里的绝对性如何确认呢?面对这种生存境遇,其意义就显得苍白。小说始终没有写出她的名字,她的顽强的生存能力,她的乐观精神,她的绝望都写得感人至深。那个陈喜儿也写得活灵活现,这个不知忧愁的年轻女孩属于现在中国的“新新人类”,她的生活像纸一样透明,也像纸一样脆弱。她的开朗,活泼,无所顾忌,她的拜物教式的消费态度,表达爱的率真,这些都被表现得非常动人。但她有她的认真,她总是认为“我”有日本有女人,这个女人迟早会来找他。这是她的隐忧。最后她跳楼自杀,却又让人觉得大可不必。朱文颖还是要寻找存在的破裂感,但这样的破裂方式似乎还可推敲。相比较起来,那个戴女士始终是个谜,她的形象并不清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有意制造谜局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她的形象被观念定格了,也被小说叙述的机制定格了,戴女士成为一个观念性的象征。 这部小说无疑非常吸引人,朱文颖很能讲故事,她的叙述细致,从容不迫;故事环环相扣,流畅而曲折,平静而有意味;对人物心理的把握非常恰切,每个人物都被勾勒得各具特征,可以看出朱文颖已经相当成熟的叙述工夫。她对小说形式,对叙述视角,以及对生存困境的那种表达,都显示出她作为一个小说家颇不一般的潜能。 为记忆的伤痛而写作,为可能被遗忘的过去而写作,为我们无法面对的历史而写作,这在当今中国汹涌澎湃的消费主义新浪潮的时代,显出一种落落寡合的忧郁之气,朱文颖这是在为一种历史作别,她有一种清醒和诚恳,她有能力为更有韧性的文学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