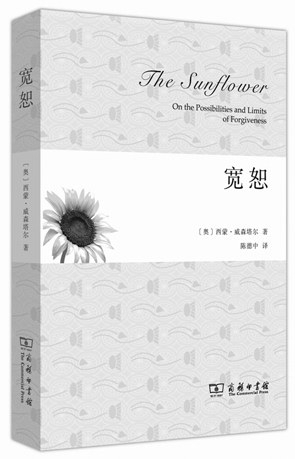 《宽恕》,[奥]西蒙·威森塔尔著,陈德中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第一版,30.00元 德国政府针对二战结束70周年而进行的活动与日本政府的表现形成对比,被国内媒体密集报道。多年来,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报道的定式。而1970年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谢罪更是成为一种象征,仿佛犹太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苦难因此而消解。然而人世间没有这样的“童话”。《宽恕》一书让我们认识到:德国政府的作为也许是宽恕与和解的开始,却远不是宽恕与和解的达成;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失去其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受的种种苦难,并不会因为政治领袖的下跪或发表的赎罪书而被抚平。 《宽恕》(原名为《向阳花:论宽恕的可能与限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向阳花”,讲述了作者西蒙·威森塔尔在二战时的一段亲身经历;第二部分“讨论文集”是32个人对威森塔尔在第一部分中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在进波兰里木堡集中营前曾经是建筑设计师的威森塔尔和集中营的同伴们来到已经是战备医院的自己的母校高等技术学校。一名修女将他带到了曾经的系主任办公室,那里已经成为病房——原来的摆设都不见了,只有一张白色的小床和一张小桌。床上躺着的人“头上裹满绷带,只露出了嘴巴,鼻子和耳朵”,他是21岁的党卫队员卡尔。他即将死去,一些经历折磨着他,他必须把它们讲出来,否则他无法死得安宁。 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卡尔他们将大约200个犹太人驱赶到一个不大的,只有三层的房屋。强壮一些的犹太人还被命令把汽油桶搬到顶楼。房门被锁上了,一挺机关枪被架在房子的对面。卡尔他们把打开保险栓的手榴弹从窗户扔进房子里。然后,他们端起来复枪,准备射击从火海中逃出来的犹太人。 卡尔看到:二楼的窗户后有一个身上正在燃烧的男人,他挟着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小孩儿,旁边站着一个女人,无疑是孩子的母亲。男人用一只手捂住孩子的眼睛然后跳了下来,女人也跟着跳了下来,还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下来……党卫队员们开始射击。 后来,卡尔身负重伤,躺在病床上的他一刻不停地回想起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恐怖事件,想着那燃烧的房子和从窗户跳下来的一家人,“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黑头发,黑眼睛”。他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得到他的宽恕。 在与卡尔独处的几个小时中,威森塔尔几度想要离开。但卡尔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离去。但威森塔尔始终无法做出卡尔所期许的宽恕,最终“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 第二天,威森塔尔再次来到战备医院,得知卡尔已经死了,临终前,让人把自己的东西转交给威森塔尔。威森塔尔拒绝了。 威森塔尔将这件事告诉了集中营里的伙伴。约塞克,一位有坚定信仰的犹太商人认为,威森塔尔没有权利去宽恕卡尔,尽管卡尔表现出了悔恨,但只是他应受惩罚的一小部分;他的朋友阿瑟,一位律师、剧作家认为,如果威森塔尔原谅他,会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的准天主教神父勃洛克认为,人只能宽恕一件针对自己而做出的罪行。 威森塔尔希望每一位读者能够设身处地回答:“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宽恕》出版后,成为许多大学、中学、讨论班有关“大屠杀”的课程的教材,激起了广泛的讨论。20年后,增补修订版出版,再次引发讨论的热潮。书中的回答也增至32个。从中可以看到公众对于“宽恕”问题跨越20年的思索、认识和分歧,也可以体验到20年的时间中,媒体、公众对于德国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罪行的态度的变化。 天主教徒伊瓦·弗赖希纳指出:“宽恕并不是基督徒的发明。我们的传统有很多是从犹太教继承过来的:充满爱心,仁慈宽厚的上帝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张开双臂,欢迎回头的罪人。”只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于宽恕的实践却存在很大分歧。宗教学教授伊瓦·弗赖希纳经常用《宽恕》作为关于“大屠杀”的课程的教材,他发现通常基督徒学生赞成宽恕,而犹太教徒学生则相反。本书中,几乎所有犹太教背景的回应者都赞同威森塔尔的做法,但基督教背景的回应者却不完全倾向于“宽恕”,有些回应者对基督徒的“廉价”的宽恕发出警示,并反思二战期间基督教会对于“大屠杀”所持的立场。 因为犹太人在二战中所经历的饥饿、屈辱、恐惧和绝望无法被再次体验,因此,读者很难评判威森塔尔在当时的环境和心理状态下应做出怎样的回应;对他的回应做出任何道德评判都是一种傲慢。除了政府出于政治考虑的“大赦”,是否宽恕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任何机构都无权对此做出统一的决定;同时,任何一个群体、民族以一种方式行事的尝试,无疑是剥夺了个体作为个人的因素。“大屠杀”幸存者心里治疗师安德烈·斯坦因说:“我们必须停止让生还者做出某种道德姿态。不宽恕既不凶残也不颓废。它是治疗和尊重我们的痛苦与悲伤的一种方法。” 二战结束不久,就有神父、慈善家和哲学家开始呼吁宽恕纳粹。盟军的基督教领袖和德军的基督教领袖在比特堡纳粹德国军人墓地集会互相宽恕。他们不仅宽恕了基督徒间的恶行,而且宽恕了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到比特堡德军公墓进行了凭吊。 然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纳粹罪犯都没有对自己的罪行表示愧疚,成千上万曾经参与屠杀的德国人重返家园,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大屠杀”的凶手消失了,“大屠杀”本身也被一些人称为“错误行为”。犹太人经常被问及:“是不是该到了‘你们犹太人’宽恕德国罪犯的时候了?是不是到了该忘记的时候了?” 然而,事情也有另一方面。约西·克莱因·哈勒维,是一名出生在战后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他竭力避免与德国人接触,也拒绝购买德国生产的产品。遇到德国人也会报以憎恶的表情,并非常高兴看到他们的狼狈不堪。作为一名媒体人,1989年,他到德国旅行并参观了一个以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命名的新教青年会。在和青年会的十几岁的年轻人交流中,他感到了他们对“大屠杀”的羞耻感。他并未因此而感到高兴,而是感到了复仇的空虚。“我事实上不希望让过去扭曲了他们的现在,不希望让奥斯维辛否定掉他们应得的尊严。”在德国旅行的经历促使约西·克莱因·哈勒维主张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和解。 《宽恕》并不是一本“新书”,但它是一本一直带给读者震撼,并引发读者思索的书。 对于中国读者,倾听另一个同样在二战中饱受摧残和杀戮的民族关于那段经历的故事和思索无疑可以映照我们的内心。书中所探讨的几乎每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都具有现实的意义。特别是抗日战争结束已经整整70周年,中日两国,两个民族关于那场战争还有若干问题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并未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降低,反而日益加大。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已渐渐故去,我们不仅面临对于史实的认定的问题,同时面临亲历者的后代如何相处的问题。 美国桂冠拉比哈罗德·S.库什纳认为,宽恕代表了“一种不再是受害者的感觉”。对于“大屠杀”的牺牲者及其后代来说,他们需要既能铭记先辈的苦难经历,又能无愁无恨地生活下去。对于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呢?今天,年轻人已经成为抵制日货、仇日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作家汉斯·哈伯说,纳粹制度的罪行,“使得我们走进了心灵的迷宫。我们必须找到走出迷宫的道路——不是为了凶手,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有这样一座心灵迷宫?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