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安妮·迪拉德,会难免想起梭罗。这是一股美国文学传统的“清流”:融于自然的生命省思,远离尘嚣。一个优秀作家,开始总是虔诚的“模仿者”,会在心中树立前辈典范。早在1968年,迪拉德就写了题为《瓦尔登湖与梭罗》的毕业论文。风格即人本身,这位女作家对写作方向如此确信,犹如她和梭罗有个“前世契约”。

安妮·迪拉德
正如蒙田早早过起了“退休生活”,一次严重的坠马事故,才让他思索肉体和灵魂的关系。1971年,一场致命的肺炎,也成就了迪拉德生命化的体验书写。她在“听客溪”生活了一年,以一本《听客溪的朝圣》摘得普利策奖,那一年她29岁。也许,只有切近死亡,才看到生命“妆台”的背面,不由多了一道目光,深刻起来。
尽管,迪拉德在听客溪的“朝圣之旅”与梭罗瓦尔登湖式“沉思”有很多相似。然而,我并不愿将迪拉德视为一个“女版梭罗”,一位“单纯的自然文学作家”。因为,迪拉德自己也很反感这种标签。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作家这种情绪是追求创作的独立自觉。但事实上,你也确实能看到迪拉德对前辈的超脱,一种刻意保持的距离。
有时,我会想这种“距离”是什么?答案就是:态度。如果说《听客溪的朝圣》是作家青年时的精神“野性”,《现世》一书就是人到中年的沉静省思,甚至入了几分“老境”。这像一边是水面的平静,一边是河底的暗涌。不过,迪拉德的态度倒是一以贯之:追问、审视、困惑和怀疑。

听客溪
你当然可以说,迪拉德拿了爱默生和梭罗的“衣钵”,但这并非重点所在。因为,这只是相似“题材”给你的错觉。在书写观念上,他们“趣舍万殊”。长久以来,我们对自然文学的认识都没有跳出一种思维惯性:认为其无非是“自然的礼赞”,“大地的散文”,表达了造物的伟大,人类的卑微;尘嚣的烦扰,自然的宁静。然而,这一系列对举的价值,似乎天然造成了社会-自然的二元对立。这绝不是什么纯粹和谐的“美文”,你甚至在每个毛孔里都能嗅出对世俗、庸众和凡尘的鄙夷厌弃。
在爱默生笔下,自然是富于象征意味的“道具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只能“反照”――专门让你瞥见世俗生活中“创造力的可怜”、“瞻前顾后的世故”、“郑重其事的烦琐”。同样,如果你认为,梭罗只是写出一个“离群索居者”的湖畔“闲暇录”,或许也没理解他的用心深曲。亚里士多德曾言,喜欢独居寂寞者,不是野兽就是圣哲。梭罗一直想做最初之人或最后之人,他爱的并不是孤独,而是“独享自然”的优越。“实际上,我倒是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还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小天地。”

爱默生
换言之,梭罗对自然文学的贡献在于一种眼光,其本质就是用宇宙视野取代社会语境,以人化的自然替代现实友邻。“独处的生活艺术”需要他把自然视作呼吸的空气,沉浸归化。你甚至感觉不到自然是一种“景观”,因为它本身就是无法洞察的生活。迪拉德也许承袭了他们的书写风格,但这并不意味她就是自然文学的传人。在我看,她只是将自然视为写作的“引言”、“序曲”、社会意识的“精神映象”。迪拉德并未在自然中陷落、陶醉,写出类似风景“小品文”的“廉价优美”。相反,《现世》一书始终超拔其上,把自然界镶嵌在深广的历史意识中,严丝合缝。在她那里,自然倒成了历史的“和音”。

梭罗
《现世》就像是《听客溪的朝圣》的“积淀”与“回响”。积淀不止是在思想内蕴上,也在文风运思上。迪拉德把观鸟、垂钓与听溪的博物学兴趣深化为一种“世界散文”的“平铺直叙”。你能发现,《现世》的雄心远远超出了自然主义:它要叩问善恶生死、质询宗教意义、打破时空限度、检视东西文明。在听客溪时的迪拉德,凌厉清冽,锐利的恣意。“我毫不畏惧上帝而冲了进去,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拥有一切该有的放逸,来与世间最伟大的主题交锋”,“喜好华丽的句子,并且总以为还不够华丽,直到做过了头。”写《现世》的迪拉德,中年醇厚,混元的力道——很多“天问”般的终极问题,在笔端,云淡风轻。
这种“轻”与“重”的参差美学,得益于迪拉德用“悲悯”写尽罪恶、不幸、悲惨和痛苦的分量。正如《听客溪的朝圣》里,作者将血与玫瑰(伤痛和艳丽)、静谧与狂暴、美景与哭泣、死亡与圣经等主题“对冲性拼接”,造就了作品最大的奇观:悖论力量。《现世》延续了这种风格,竟在如此浓烈的神学语境里(如“以色列”章节对上帝、灵魂、善恶的反思),表述了世俗化的此在价值——现世的意义。我们似乎对“迪拉德的自然”,逐渐有了新认识,这是一种近于万有在神论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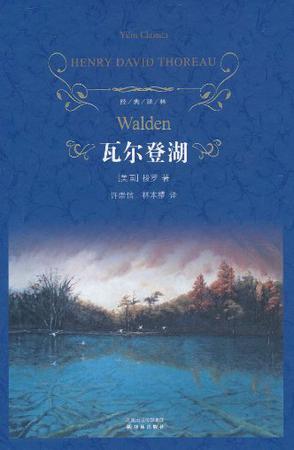
《瓦尔登湖》
在“诞生”的希望中,她却写了人类畸形的绝望,凄惨的男童女童说明了生存的代价。在“云”的浪漫优美中,画家康斯太勃尔进行着云的写生,纪录了妻子玛利亚的垂死时刻。在“中国”的主题里,作家将兵马俑正从壕坑里涌现的时刻,与整齐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无趣景象并置。土质人偶埋在黄土原料里,本身就隐喻了“人为”归于“自然”的大化。“数字”是对人类生存、灾难和死亡的数据罗列,也许会让你厌烦。但迪拉德就是用统计学的“流水账”,再现了一种难以呼吸的压迫。让人震颤的是,作家搜寻出了关于阿齐瓦拉比惨死于罗马人酷刑下的圣人事迹。这则故事,可以说是迪拉德强调“现世价值”的最强奏鸣,她向一切来世的彼岸意义都发出了彻底质疑。

安妮·迪拉德
罗马人用马刷剥下了阿齐瓦的皮肉,作家反讽地引用了阿齐瓦的名言:“一切都取决于善行的力量”。那么,“需要多少磅的善行才能再次令天平倾向善的那一边?”这个诘问本身就是一种残酷,作家说明了善恶并不遵循因果。神学只能给你一个蹩脚的“心理按摩”:“上帝惩罚善人在短暂现世中的微小罪行,而在永恒的来世褒奖他们;上帝奖赏恶人在短暂现世中的些许善行,而在永恒的来世惩罚他们。”迪拉德自己不信,“在我看来,它就像发生天灾时给出的各种敬畏上帝的精妙解释,不论怎样解释都无法抹去残酷的事实。”
有很多评论都注意到《现世》中的十个主题:诞生、沙、中国、云、数字、以色列、邂逅、思想家、邪恶和现时构成了并置杂糅的“复调”。然而,我并不认为可以按照主题进行分类“跳读”,读出十个平行的单线叙事。因为,这就像你把一个多声部的对位,活生生地拆成了不同声部的独奏,白白浪费了作家交织世界的才华和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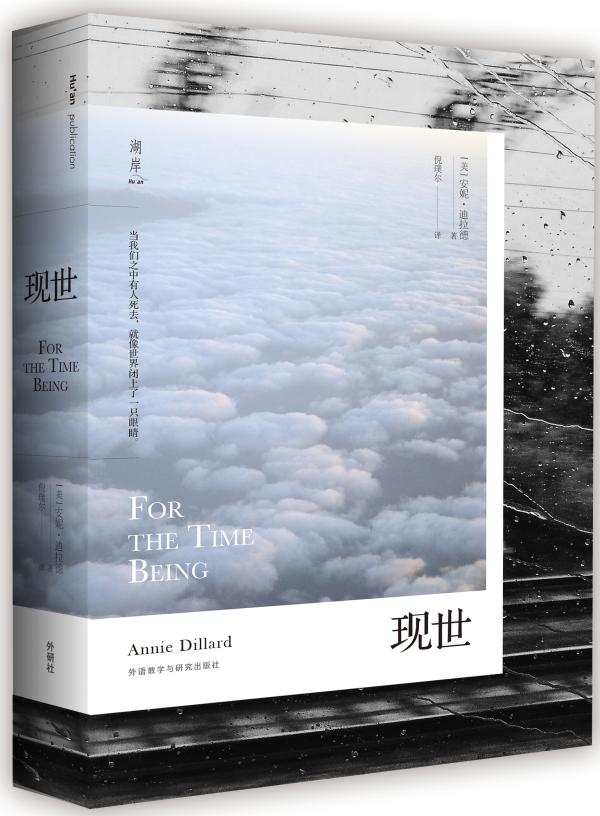
《现世》
一方面,中国与以色列两个主题就是一种“对话”关系,德日进在中国的神奇之旅又与他讲述生命哲学的著作形成了潜在呼应。另一方面,在迪拉德的书写次序里,你能看到一种流动韵律和回环结构,看似散漫的博物杂糅,却有“无法的章法”。如“云”和“沙”刚好是仰观俯察,描摹了物质的生成和人类“诞生”的双声。同时,她又参照自然之序,发现了历史、宗教、社会的“失调”、“悖逆”之处,揭示生命生存的代价(邪恶、丑陋和无奈),告诉你只有现时有意义,只有现世有价值。
在我看来,迪拉德和自然文学最为迥异的是:她从不写“牧歌”,不追求和谐的纯一,静谧的伟大。相反,她时刻质疑、拷问世界的秩序,做着类似尼采的事业:一个怀疑论者在重估一切价值。《现世》给你带来的根本就不是心灵慰藉的“鸡汤”,而是萦绕不绝的悲愤力量。那种断章一样的结构,箴言般的句子,就像神谕,气势撼人。迪拉德的妙处是写出了“优美的残酷”,面对她的段落,有时你根本不知是该欣赏陶醉还是忍痛心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