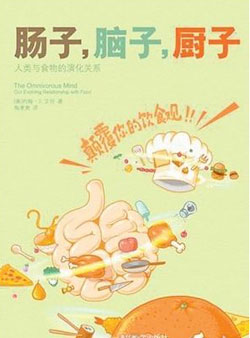 [美]约翰·艾伦著 陶凌寅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几乎所有人都很享受,抱着一大桶金黄发亮的爆米花坐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吃。如果我们满身是毛的祖先们“穿越”到今天,他们可能会选择抱一桶蟋蟀、蚱蜢或者甲壳虫。这个场景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恶心,但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人类学家约翰·艾伦在《肠子,脑子,厨子》这本书里不客气地告诉我们,人类对酥脆食品的天然喜爱极有可能在5000万年前就扎下了根——灵长目始祖很可能主要靠食虫为生,这些具有坚硬外骨骼的昆虫可是不用加工就能吃的最酥脆的荤菜了。 当第一批“大厨”出现,人类的酥脆食谱大大扩展了,烹饪使许多食物变得酥脆而且味道浓郁,并把这一偏好推到了饮食习惯的中心位置,至今依然如此——看看随处可见的薯片和炸鸡就知道了。 酥脆食物的魅力不仅限于“遗传”。邻座情侣的窃窃私语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堪其扰,但来自自己的咀嚼爆米花声非但不会影响我们的观影感受,反而越嚼越香。这种“选择性”的“充耳不闻”得益于神经感官系统的一个共性——习惯化,当感觉神经元持续地暴露在某刺激之下,就会习惯这种刺激,刺激越强烈、越罕见,就需要越多的时间才能习惯。因此我们不会觉得自己咀嚼爆米花的声音很恼人,反而会因为咀嚼酥脆的食物比咀嚼不脆的食物发出的声音更响、刺激更强烈而不容易吃腻。 在《肠子,脑子,厨子》这本自称“吃货研究所”的书里,艾伦以人类学、食物历史和作为厨师的经验为武器,透过精神上的味觉偏好这一展现人类生物学特征和文化历史的透镜,不仅关乎怎么吃、吃什么,更把食物嵌入一张“由各种认知关联构成的大网”中,探讨人类为什么喜欢这样吃。 艾伦认为每一个个体头脑中都存在着“食物理论”——这是一整套关于进食和看待食物的方式,是认知史、演化史和文化史以独特的方式交汇于每个个人的产物。“食物理论”在人从小与食物的接触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演化过程中的“集体无意识”在我们头脑中埋下了对酥脆、脂肪、甜食等口感的偏好,但具体到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吃,则与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关系更大。 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在收获稻谷后收获蚱蜢,用植物油煎炸,配以姜、蒜、辣椒等作料,这种土著居民眼中的无上美味却往往被西方人视为“不洁”。而美国感恩节家家必吃的火鸡则被新几内亚的卡拉姆人视为森林中的“类人”生物,捕杀了火鸡的猎手必须吃掉这只火鸡的心脏,以保证它的灵魂能够返回森林。 艾伦把饮食习惯这种同样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特性与语言类比,我们能迅速接受并熟练使用新生词汇,用第二语言取代母语则困难重重。我们在狩猎——采集的旧石器时代演化出的对脂肪和甜食的偏好欢呼雀跃着在农业社会得到了满足。看见有吸引力的食物,我们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去吃”按钮就会自动按下,而那个“停止”按钮还没有演化出来。于是人们发现,吃东西成为了一种习惯,伤心时吃、开心时吃、工作时吃、休闲时吃,越来越便利的网上购物网上订餐使人们获取食物的手段越来越方便,消耗的热量越来越少。 当“总想多吃一点儿”的基因遇到丰富的食物环境,日益增多的肥胖人口和糖尿病的流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归根结底,因为人类在一种环境中演化出的身体和心灵,被放置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艾伦如是说。 也有研究者指出,美国热量过剩的饮食环境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在时间上先于肥胖者比率的升高。他们认为美国近些年来的变化鼓励了更为放纵的饮食环境,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食的习惯使人出于享乐进食,而不仅仅是由于饥饿。“进食不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填饱精神”。 胖子们可能会感到绝望,要对抗的不仅是食物和自己那热爱食物的心,同时宣战的还有隔三差五的夜宵、推杯换盏的应酬、酒过三巡的兄弟情谊。“吃”字背后是一张演化、认知、文化交汇织成的大网,每一个难以控制自己食欲的吃货都是粘在这网上的小小虫子,想把网弄破太难,自己使劲扑腾扑腾翅膀飞走也许是逃脱的更好方式。(实习生 陈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