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这是崔立秋于20年前所写一篇文章,碍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者当时并没有将其发表。随着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流行音乐歌手鲍勃·迪伦,这篇《现代诗与流行音乐》又得以翻出,重新进入我们视野。
导语
10月13日晚,美国流行音乐歌手鲍勃·迪伦击败了呼声甚高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获得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现代诗与流行音乐的争论也随之甚嚣尘上。其实,诗歌与音乐自古以来便密不可分,诗、乐、舞三位一体。当代流行音乐更是被称为“现代歌诗”,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收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王朔称崔健是“中国最伟大的行吟诗人”,张新颖在《中国当代文化反抗与流变》一文中将崔健与北岛相提并论。如此说来,给世人留下无数经典音乐的鲍勃·迪伦获得本年底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无可非议了。
诗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远古时代的诗歌、音乐、舞蹈是三位一体的。《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者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是说远古时人们手持牛尾,载歌载舞。作为诗歌源头的《诗经》,在当时就是配乐、伴舞且歌咏的,颇同于今日的流行音乐。《墨子·公孟篇》记载:“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诗三百”即指《诗经》,因《诗经》凡三百零五篇而得名。)后来发展成熟的汉魏乐府、唐宋词、元明曲等也都是配乐而歌的,并且它们本身就起源于民间歌谣或市井杂唱。吉林大学的麻守中先生将这类诗歌称为“歌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行音乐就是“现代歌诗”。李景冰在《现代诗的状况与趋势》一文中,将流行歌曲纳入“广义的诗”的范畴;邹贤尧先生在《当代诗坛的流行景观》一文中,将流行歌曲称为“流行诗”。
通过对大量流行音乐的分析研究,笔者发现,曾经难登大雅之堂的流行音乐之所以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普遍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流行音乐自觉地向现代诗靠拢,逐渐摆脱了肤浅庸俗的境地。从外在形式方面看,流行音乐借鉴了现代诗的意象、象征、反讽、隐喻等表现手法,使自身呈现出更多的诗性色彩。崔健的“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就是用“红旗下的蛋”这一意象来象征在革命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那些失去了个性,没有了棱角的人们,虽然蛋没有棱角,经常被人滚来滚去,但它毕竟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反叛精神。齐秦则以那匹为了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在凄厉的北风中,紧咬冰冷的牙齿,走在无人旷野的“北方的狼”这一中心意象,表现出在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之中,有极少数人仍在执著地追求真、善、美,让我们透过寒冷的冬夜看到一丝温暖的火光。从内在精神方面看,流行音乐渗入了现代诗的生命哲学底蕴,表现出人文关怀的倾向,使自身日益摆脱了“平面文化”、“快餐文化”的肤浅困境,呈现出平淡中透真情,朴素中蕴华美,浅显中见深刻的一种至高境界。齐豫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梦中轻流的小河/流浪。”这就与海德格尔“人生就是飘泊”的命题相契合,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那种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费翔在《故乡的云》中唱到:“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请为我抚平创痕/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请为我抚平创痕。”以身心疲惫的游子形象,揭示出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的现代人那种对“家园”的强烈渴望之情。此外,张雨生的《大海》、王杰的《英雄泪》、郑智化的《水手》、田震的《野花》、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等等,都表现出很深厚的生命哲学底蕴和浓郁的诗性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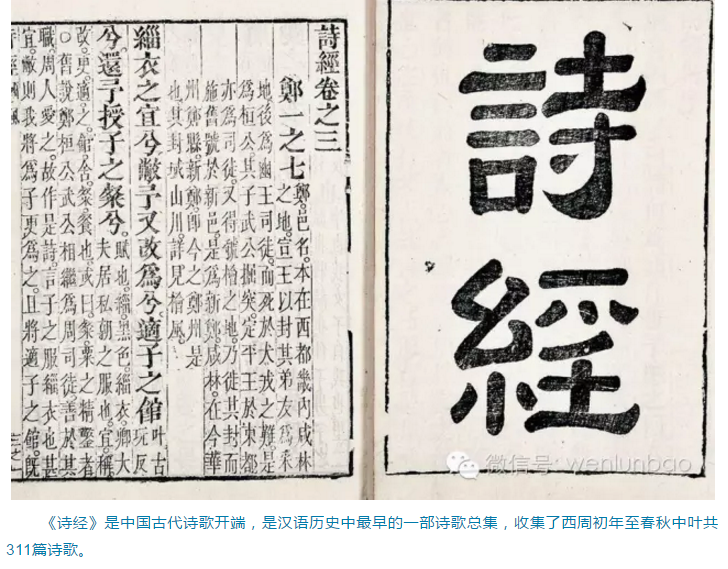
这里我想特别谈一下摇滚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崔健为首的摇滚乐开始着陆中国,并以其粗犷奔放的旋律,歌手声嘶力竭的呐喊,以及歌词本身蕴涵的深邃的思想和极强的生命能量猛烈地激荡着听众的灵魂。摇滚乐的这些特色与现代诗所高蹈的“自由、圣洁、高迈”不谋而合,因此,摇滚乐受到文学批评家和诗歌理论家的高度重视。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收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王朔称崔健是“中国最伟大的行吟诗人”。张新颖在《中国当代文化反抗与流变》一文中将崔健与北岛相提并论:如果说八十年代初的北岛表达了“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中期的崔健则把这个人塑造成“走过来/走过去/却找不到根据地”的彷徨者形象。在九十年代的摇滚乐坛上,陈超先生最欣赏歌手郑钧,他认为郑钧的歌颇具文化哲学底蕴与诗性色彩,其所表达的对人文精神的关怀与思索丝毫不亚于今天最优秀的现代诗。“回到拉萨/回到布达拉/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净/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我美丽的雪莲花”。纯净美丽圣洁的布达拉宫与庸俗不堪的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一种张力关系,在这种紧张和对抗中,歌手通过对布达拉的肯定,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追寻,确认了自身“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的身份,并以此身份坚决捍卫着“人类的精神家园”。除崔健和郑钧外,唐朝、黑豹、Beyond、零点等摇滚乐队同样优秀、同样出色,他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大量经典的“现代歌诗”。
与流行音乐自觉地向现代诗靠拢恰好相反,现代诗却日益讲求语言内在的旋律,努力营造着纯语言的乌托邦,自觉退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现代诗越来越讲究技巧,将之作为语言在话语空间的相互追逐和不断翻滚,诸多意象的并置,造成诗歌的诘屈聱牙,晦涩难懂。“第三代”诗人的核心人物于坚有一首在诗歌界很有影响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从看不见的某处 /乌鸦用脚趾踢开秋天的云块/潜入我眼睛上垂着风和光的天空/乌鸦的符号/黑夜修女熬制的硫酸/嘶嘶地洞穿鸟群的床垫/坠落在我内心的树枝。”这首诗如果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很难欣赏得了,更何况是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观念的中国读者来说了。
现代诗人往往在自己的作品中营造着一个他人无法进入的独立世界,建造着一个诗歌的王国,塑造着诗人个人的国王。虽然说“私人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并以其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楔入艺术的本质。但是诗歌自古以来就是大众的喉舌,人们以之表达感情,交流思想,甚至进行政治外交活动,因此才有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很多人写的现代诗根本就不是诗歌,人们都读不懂(这个“私人化写作”语境下的“不懂”,与那些因语境缺失而读不懂的古代优秀诗歌有着本质的不同),无法进入诗人的世界,不能进行对话交流,那这种诗歌存在的价值何在呢?反观那些优秀的现代诗歌,朦胧但不晦涩,讲究意境深远又不故弄玄虚,抒发个体情感的同时又实现着对“小我”的超越与升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北岛的《墓志铭》、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等,就是通过个人情感体验的描述,传达出某些在人们内心深出处相通的普遍而永恒的东西,因此,它们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广为流传。

有些现代诗缺乏历史的厚重感与深层的文化底蕴,虽然能获得暂时的广泛流传,从长远看却未必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上世纪初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化两次大规模地登陆中国,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发生猛烈的撞击。由于经济的滞后,以及历史语境的变迁,传统文化虽然负隅顽抗,最终还是败下阵来,西方文化则以强势文化的高姿态征服了中国,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这种文化的断裂在诗歌界的影响尤其显著,中国的现代诗就象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一样不知何去何从,只能盲目地在几位洋叔叔之间奔波寻觅,现代诗人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度的焦虑感和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这种状况反映在他们的诗作中,就呈现出文化的消解。伊沙在《车过黄河》中写到:“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流远。”在这里,被“一泡尿”冲远的与其说是具体的黄河浊水,不如说是神话意义上的黄河圣水,连同其凝结着的历史,蕴涵着的文化。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这样写道:“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观赏大雁塔的意义不再是神圣而深厚的历史追寻,仅仅是再平常不过的风景游玩,在消解历史和文化的同时表达出诗人对日常直觉的绝对信赖。在这些诗中,诗人以调侃的语气,亵渎的态度消解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历史和文化。反观我国古代的诗歌传统却不是这样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些诗以其穿透历史的纵深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征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千古流传。
在现代诗自觉退出大众生活的这些年里,流行音乐身兼二职,一方面实现着自身的音乐价值,一方面又以现代歌诗的身份弥补着现代诗在大众审美需求中的缺席。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延续来说至关重要。然而,不管流行音乐如何向现代诗靠拢,它都无法取代诗歌在文坛上的特殊地位,它也无法完全满足大众对诗歌的渴望。因此,现代诗需要打碎个人的上帝和语言的乌托邦,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