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兆南,江苏海安人,原名钱俊梅,曾用名水无痕。创作200万字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曾在《天涯》《作品》等刊物上发表若干字。田野走访者,面向土地,无尽卑微。
这是一篇针对一本书进行的专访稿,
也是为了致敬一位匍匐在大地深处默默的创作者。
采访:向度文化
受访作家:钱兆南
问:当初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按常理讲,它应该是“出力不讨好”的。
答:是的。这是一本吃力不讨好的书,直面现实的写法,怎么说都是伤人伤已的,但是它没有丝毫的距离感,保留了真相。这等于把一个炸弹抱在自己怀里,随时会引爆。
读多了软弱无骨的字后,很希望整点有血性的东西出来。如果说写这本书机缘的话:那就是天意。只有在摒除所有功利心后,自然流淌于笔端的文字,方显生命品质的真性,与一切无关。
在行走了许多年后,到2013年的时候,手头上积累了一些资料,才觉得与这本书的缘起自然来到。这年下半年,辞掉了远郊的工作,带着孩子回到乡村的腹地,一边陪孩子读书,一边开始走访。经常走很远的路都难遇到一个人,荒凉,孤单。天黑下来的时候,一个人像天上流放到人间的星斗,孤单地在田野深处无力地闪烁着。
安顿好孩子,抽空回村里看母亲,母亲总希望我能陪她说说话,而自己的心里火急火燎要往更远的村庄去,总是找理由出去冲,经常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麦田里。母亲和邻居们说:这丫头,到了家,魂却落在外头,怎么就不归家呢。
最理解和最不理解我的是母亲,她一个人守着几亩地,一个庭院,几十只鸡和四只猫。母亲并不知道我要做的事。我越怕她担心,她越是不放心。她怕我在路上遇到歹人,怕我骑车不小心跌到沟渠里,怕我走得太远会迷路。母亲说现在村里有些人越来越不好,什么丧德的事都做得出来。是的,这个一切以金钱利益为主体的社会,村庄想回到从前的单纯,太难。
问:说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答:在这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正式把它定名为《清凌凌的河上》。取这样的名字是有私心的,因为我太喜欢门前的那条小河,小时候呆坐河边,清澈的水无端地把自己的魂吸走,开始神游天外。
写完几万字后,也没考虑太多,一时手痒贴在新散文观察论坛上面,想听听更多人的意见,结果下面的留言一下子翻了好几页。绳子说:这可不好,你没有撕开来写。说实话,绳子对这本书的影响是最大的,他在不停地指导我如何深入,最重要的是不要刻意去过滤真相,至今仍没达到他的要求,出现的偏差总是难免的。河南信阳的平子1994老师说:小朋友,这太短了点,如果再扩写到10万字,你回头看看,就不同了。于是,我果断地把几个章节删除干净。让心沉到海底,继续开始行走,拍摄,询问。这一走又是三年。拍坏了两个相机,两个手机,雨天行走中,腿摔伤过一次。38度的高温在水稻田中行走,去看万顷良田中的九十九间半民居时,热得中暑。在回来的公交车狂吐不止。在江北和江南甚至更远的地方坚持走。
许多同道的写作者们都在善意的提醒我,这么拼命,力用尽了,心会碎的。如果以小说的形式书写,要省多少力气,不值得。尽管如此,一分钟的闪念也没有动摇过,就这么一门心思扑了进去,远离人群,越走越远。如果说行文用情太深的话,那只是因为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血腥太多的缘故。
行走和书写的过程是艰难的。最难写的是《在乡村与城市流浪的水花》这一章节。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坐在电脑面前,也去过麦田中央,远郊的废墟上,一坐就是半天。白天黑夜中,魂和水花一直在一起,已分不出彼此。经常半夜惊醒,遥望星辰,睡意全无。这个社会,像水花这样绝决的人已不多,她属于稀有品种。她是一个内求的人,而现实世界中的人习惯了外求、轻视内求的人。
庄辜笑声读过这个中篇,对这个人物有深刻的了解与理解。他说:水花这章最好,充满了生命的汁液,令人尊敬。为此,我第一次去西安时,为见到这位极富才华的年轻人而错过看兵马俑。我们从在车站第一次见面,到傍晚他帮我买好去机场的大巴车票,我们一直讲个不停。我们在鸠摩罗什的铜像前合影。庄辜笑声说,他很喜欢水花这个人物,事实上,他和水花都是偶然间独立于世的天外来客,像一颗滑向天际的流星,才华的光亮终将被这个时代埋没。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慧根的通灵者。水花注定不属于大众,对她除了理解与尊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评判她。
问:据说这本书的出版历经挫折和磨难,现在终于出来了,心情很激动吧?
答:是的。9月18日这天,从省城传来书出厂的消息。和编辑老师隔空交流这本书又是大半年。听编辑说书刚出来时,心顿时“咚”的一声,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当目光穿透书的绿色的封面,感觉这是一场自田野上吹来的绿色的风,庄严,肃穆。这风把心吹透。此时,和书中的水花同样感到了“回到大地的肚子里去。”这一刻时间是静止的。感恩于两位同样是写作者的编辑老师,是他们成全了这本书。尽管删除改动蛮大,但深深理解,所有的删改都有理由,无法展开言说。
在激动了5分钟后,心很快恢复了平静。各地的师友们一直在期待着这本书。这是自己的第一本书,或许是最后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在乡村行走8年之久,耗去大量的精力,终是值得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这本书似乎是从天而降,又害怕它随时消失,更多的是感恩所有帮助过它成长的师友们。书里的每个人重新开始在脑子里活起来,他们每个人像田埂边会移动的草一样,一起跑过来和我说话。
要说这本书从成稿到今天仍可能存在的挫折,的确不少。从桃花盛开一直等到大地冰封,才知道这本书唯一无法出版的理由是:太真。后来无休止的删改使得心一次次的支离破碎。如果书的骨血都被放光了,留下一具惨白的残骸有何用?在不愿意妥协的情况下,自行撤稿,心死如灰。那段时间,有次在回家的途中,尽然忘记了家在哪里。于是,一次次走向荒野,并坚信那里一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等待自己。
想要让灰白的心起死回生的方法、并注入新的活力的办法有许多种。
去寻找另一个生命场,成了不二的选择。到废墟中去寻找。废墟中看似无路可走,如发心去走,条条是通途。比如工地现场,是最大的场。去年底,省城下了一场30年不遇的鹅毛大雪。那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结束了在工地打工的日子,闲在家中养病。意外赶上去省城参加一个学习班,与学员们一起交流时忍不住说到自己这本小书,引起了几位高校评论家的兴趣,会上议论种种不一。十天的学习结束,各奔东西。不曾想,这本书又巧遇上贵人。正是腊月初,这本书又从冬天开始了新的航程。
有时候想,这本书是从二十四节气的掌心里长出来的,冥冥中注定要让自己坚定地付出,然后带着它自己的使命继续去孤单地漂泊。书中有几个人已去了天堂。希望他们在天堂里不要受在人世上的苦,尤其是细兰和梅兰。
书中有一章《阿军的困惑》中的主角阿军,他是一位三农专家,在对三农政策的解读上,土地的归宿问题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在对三农政策的认知上,他提供给我近7万字的政策文件,多次面对面解惑。因为种种原因可惜这章全部拿掉了。所幸的是,这章节的万余字在今年《作品》杂志第三期全文刊出,而大量血拆现场在杂志中拿掉的,在书中得以还原。还有附录中的三千字全部删除,这三千字,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对土地的反馈信息。
正如久阴必阳,阴阳需要平衡,这才是万物的正解。9月19日,天阴,闷得喘不过气来。决定去做一回草民,让纸页中的每个人物重回芳草地。午后出门时,天空中飘起了雨。离开城市,到远郊找了块废墟边缘地带的菜地去割草。手中崭新的镰刀在等着我开启它的人生。郊外的这片荒地,周边的农民勉强种了点菜。今年的夏天热得发了狂,野草和庄稼混在一起苦熬。由于肥料和雨水不足,豇豆、大椒、扁豆、南瓜纠缠在一起,瘦巴巴的,缩手缩脚,一副倒霉相,像极村里的人。
在这里,满是青草的味道。一本书的命运,可能都不如一根草、一株扁豆。

钱兆南在割草/2017年9月
问: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义为“田野写作者”?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草根作家”?
答:极少有人看得见野草们卑微中的尊贵。(这也是写作者个人简介里的一句:“面向土地,无尽卑微。”的原因所在。)它们只要落下一粒种子,融入泥土,死了也还可以重生。书呢,在时光中流转,一场飓风就能把它吹得无影无踪。
再思:一个姓草的人,让这本书从草里长出来,听天由命为宜。
在荒地上割草,挥汗如雨,周身通畅。草丛里,蚊子当道;草根下面,虫子当道。这世上如果少了草的存在,泥土会有多凄清。我们都是草的子民。经过一夏的煎熬,蔬菜在杂草丛里活得苟延残喘。时近秋分,夏季作物彻底退场,下一季的农作物开始播种。蔬菜们的时代如台上台下的人:台上,你方唱罢;台下,我方登场,时令一到,天地间必将重新洗牌。
一本好的书,更应该是从泥土里长出来,应该有新鲜的血液不舍昼夜地流淌。否则,任何人都有枪毙它的念头。但一本书一定会驻进写作者的血脉里,在血管里生根发芽。
这是一个姓草的人,写给有具有草性人的书,哪怕它能以秒的速度存在过。
晚秋的野草里有一股衰败味,那是腐朽之味。草里什么都有,有金子,有垃圾,不同的虫子像大街上的人一样,横冲直撞,各行其道。衰草里面有扁豆、豇豆和南瓜的根,镰刀没长眼睛,握镰的手一松,一棵活生生的南瓜的根给割断。想起书中的逝者们,他们同样是被时代的镰刀所伤,但不是误伤。如同作者是公堂之上的判官,这相当于误杀一条人命。南瓜不会说话,死就死了,等待明年重生。那,人呢?
草丛里的蜗牛钙化的壳子,灰白。爬墙虎游到杂草里。杂草纠缠在一起,像人与人纠缠在一起,乱象环生,又荣辱与共。
大片的土地上杂草铺天盖地,这样的景象有时候让观者感到绝望。许多圈养在钢筋水泥中的文明世界中的人,呼吸着科技带来的危废,导致血流的速度慢慢变慢,直至停止流淌。而大地深处的蝈蝈正在草丛中吟唱,无数的种子正准备破土。如果他们能够走向那些因为拆迁,因为不得不抛荒的土地,埋头割草,不再仰天歌唱,大地上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还有四天就是秋分,大地将进入新的轮回。在除过草的土地上松土,平整,洒上菠菜种子,可惜竟然无法找到一点肥料。学着母亲的样子,把除下来的杂草,团成一小把一小把,挖坑埋进泥土里当绿肥用。
黄天厚土,庄稼在上,草在下,万年久长。
盘古开天地起,这世界肯定是先有了草,然后才长出了人。到底人是草变的,还是草是人变的,无法追问。在城市还没出现的时候,大地上一定只有草,所有的庄稼都是草。草越盛,庄稼没底气。谨以这段文字祭奠长眠在草底下的先知们。
问: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是不是以后的写作仍要以土地为核心与书写对象?
答:是的。将继续以跪拜的姿势书写土地上的人和事。但不急于求成,用虔诚的心去等待每一个机缘的出现,然后紧随其后,一切顺其自然为好。这世上的许多事都是分裂的,一个写作者的思想,也会在特定的时期内分叉。那些分叉的思想,犹如乡村的四分五裂的田埂,再怎么纷乱,但每条田埂都通向回家的路。
附录:
土豆-如东:为了种田的事,每次回家都要跟父母亲吼,他们才听。现在不种田了,下午摸摸长牌,蛮好的。地是国家的,都可以私下买卖。我们那有人要在别人的地里建房,一亩地就卖1万多。
雨滴一海安:我家就剩七分地,为了家中的田,我每次回家哭,眼泪鼻涕一大把,我和老公劝父母都没有用,父母说田在那不种,人家会骂。为了种田跟我妈吵过,我妈妈还哭还生气,我也没辙。那腰再劳累就得瘫,虽然都是请人打药水啥的,总归多少还是要做。现在好了,感谢承包人,我妈那腰算是保住了。我现在烦不了这些,不种田就好,又不能卖,将来拆迁补偿也就那样,就算值几十万也没有我妈妈重要,更何况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只要不种田我不要钱都可以。
水无痕 :小明老师,我在写一篇关于土地的小书,想在全国范围内了解点真实情况。想知道你们那边土地的情况,你家地如何给别人种的?
河南驻马店小明 :可以问我,我们家还有不少田,太了解我们那边的情况。今年种玉米的时候我妈身体不舒服,暂时包给人家种,就给别人种一年,以后还是我们自己种好。
水无痕 :河南地区是否有抛荒的土地?有没有被征用的地?
河南驻马店小明 :没有,我们这是农村,不靠近城市,我们这边的地很多人都想承包的。 包个几百亩地,也不少赚钱。我们家13亩地,收麦子的时候我跟我哥哥去田里就行了。父母年龄大了,不想让他们种,他们又舍不得给别人,所以就给他们个规矩,种上就不管了,到时候我们回家收。现在管理也都方便了,我家种地更方便,种上除了上上肥料,都不管了。那个打药,都雇人,其他的就靠天收。去年大丰收,一亩1200到1300。我爸说,从种地都没见过这么丰收过。
水无痕 :嗯,天下父母心相同的,他们与土地有感情。 望天收还长这么好,证明土质好,风调雨顺,你们这一季算是逮住了。这在江苏地区长得最好的,也不过如此。
河南驻马店小明 :嗯, 平时也基本800-1000 的产量,我们那边旱了可以浇水的。 小麦1块1左右,现在几乎没人种油菜了,种油菜,不能用机器收,所以现在人种的少了。
水无痕 : 今年报纸上有一个新闻,河南地区的,小麦收上来卖不掉,你们那有这回事吗?
河南驻马店小明 :去年小麦大丰收,收的多了。其实说起质量这话题,年年都是那个质量,如果说真是大的质量问题的话,是有点不现实,只能说,提高了标准或者是想为低价收购造势,不可尽信。
水无痕 :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
河南驻马店小明: 我们那边一个人才1亩多地,算是人口密集地区。不种田的地方,有几种情况:1、外面赚钱;2、地势不适合机械化耕种。老百姓是最基层的群体,还是很无奈的。我帮同学家收过,很累。俺年年干农活。
嗯,没土地我们也活不了。
水无痕: 对于种田,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河南驻马店小明 :不愿意。一个是越来越不值钱,再就是家里种田,都要回去收,地少的话,来回折腾一次,来去一趟的路费够买一堆粮了。
水无痕 : 你在城里多少年了?如果哪天父母实在种不到了田了,你会放弃自己家的地吗?如不放弃,又怎样去处理这些田呢?
河南驻马店小明 :是啊,除非是为了看看父母,不然根本不会去种地。在城里19年了,如果实在种不了了,不会放弃的,这是父母的念想。每年种田的时候回去,平时的打药啥的要村里的人帮忙了,给他们钱,父母是第一位的。有时候累得都不想干了。太痛苦了。感觉就是在苦熬,特别是要变天的时候,那个赶啊,心急如焚。非常的无助。
水无痕 :如果你不放弃这些田,又能怎样,荒着?
河南驻马店小明 : 选择继续种,一直种到父母不在,到时候就包给别人,以后没人包了,就会进入市场流通,我们那边现在已经给田地办了户口了。
水无痕:有空的话能说一个你种田时觉得最恨、最痛苦的细节给我听听吗?
河南驻马店小明 :有一年中午的时候,那个时候收割机还非常的少,大都是小拖拉机上装个小收割机,自己再用人力车拉到晒场里。中午的时候,麦秆被晒的很干,这个时候麦秆很光滑,装到车子上特别容易滑落,刚装好车子,还没来得及用绳索捆绑好,一阵大风刮来,一下子都散架了,这个时候感觉特别痛苦。最麻木的时候就是拉着人力车一趟一趟的往晒场运麦子,埋着头,已经没有了思想,只顾着走啊走。还有一次,晚上爸爸的朋友,他们家有拖拉机,趁着晚上帮我们家拉麦子,最后一趟大概凌晨2点多,我太困了,一下子从车子上滑落下来了,幸好人一点事没有。
水无痕 :你们的收割机是自己家买,还是租借?
河南驻马店小明:我们家没收割机。有专门买收割机给别人收麦子做这生意的大收割机,以前的时候我们家连牲口都买不起,全部人力。
水无痕 :嗯,收一亩田需要多少钱?
河南驻马店小明:今年是45块,我们村里有家买了两台。
(小明,1974年生,河南驻马店人,在外打工19年,每年回家帮父母收割。)
山西大同陈年:村里人都不种地,我不知以后我们吃什么。我姥姥村,都是水浇地,人们也不种。我爷爷那边是山地,更不种了。我从小在矿上长大,对村里的事,知道得很少,只是看到现在叔叔们都不种地了。他们打工,下小煤窑,给别人盖房子,这就是全部的收入。我三叔六十多岁了,还是下窑。我们山西都是以煤养家。煤炭资源马上就没有了,他们靠什么生活 ,这真是问题。
陈年 :所有的人都在撒谎,每年都是粮食大丰收。在网上看到云南以前的铁矿,人去屋空,只剩下一些老人还在,年青人去外面打工,留下的靠贩毒、卖淫生活。
水无痕:水浇地是什么地,是不是要靠浇水才能生长庄稼的地?
陈年 :就是能浇上水,也就是小平原吧。也不是靠浇水才能活,就是不用靠天吃饭,天旱了能浇水保苗。我爷爷那边的地在山上,只能靠天。
水无痕 :这样的水浇地造成的水资源浪费也厉害,一亩玉米要多少水?
陈年:不知道,我没有在村里生活过。所以我姥姥村算是富村子。
水无痕:小亮你好,想了解一下邯郸那边的土地情况。
河北邯郸小亮 : 好多地被占了,强征,一亩地六万,先从邯郸开始,几十万几百万往外卖,几百人拆迁啊征地啊,建没有质量保障的小区或者修路。失地的农民有的住小区了,还是干原来的活,没事做的村民人大多是给村里人盖房子,给开发商盖房子,有些人买了车。不交养老保险,都是自己交。有的开发商跑了,村民们用砖头把门堵了,把里面装修一下,住进去,房子就成自己的。这里三年大变样,要成为经济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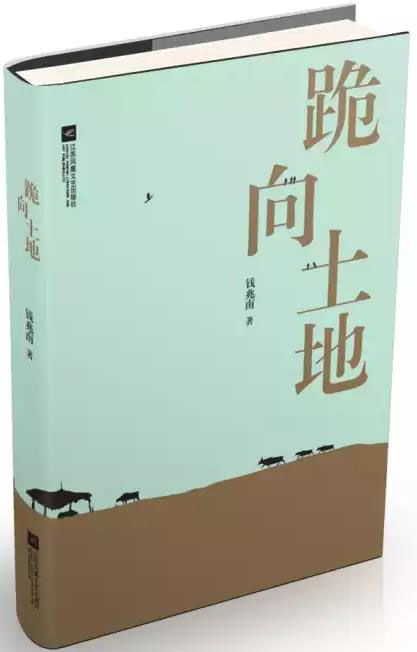
这是一本写给大地母亲的书,八十多岁的母亲还在村里种几亩地。这些年亲眼目睹母亲和乡民们的欣喜和忧伤,见证他们背井离乡后动荡不安的生活时,我还不是一个勇士,不得不承认再坚挺的文字也难以拯救时代变迁的进程,对当下正在进行着或意欲执行着的事件无法去逆转,只能站在田岸边悲欣交集。有人告诉我说,总需要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有的善与恶从土地开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公正与不公正,越是不公的时代越渴望有一种侠义来支撑。
自 序
我在城市和乡村间流浪数十载,年年归乡,蹲在田头,把一块块泥坷垃捏碎,原野上飘来的麦香灌满心怀。在不同的季节里,撒下种子,企盼天上的雨水和浩浩荡荡的季风给田野带来丰收的喜讯。
尚在村里守着几亩地的老母亲,双手早老如树根,掌纹被年年如斯的黑土生生割断,找不到一条完整的纹路,从四十岁起半头的白发,到如今八十岁满头的苍苍白发,风霜的刀刃将她的脸雕刻成一枚风干了的枯树叶子,犹如墙根下失去水分的干萝卜。这些,除了在文字中入骨入髓的感慨外,我别无他法。这些年亲眼目睹乡亲们的欣喜和忧伤,见证他们背井离乡后动荡不安的生活时,我还不是一个勇士,不得不承认再坚挺的文字也难以拯救时代变迁的进程,对当下正在进行着或意欲执行着的事件无法去逆转,只能站在田岸边悲欣交集。
每次时代变革,总需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公正与不公正,越是不公的时代越渴望有一种侠义来支撑。可乡村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有的善与恶都从土地开始。村里人经常说句老话:天大的事也大不过房产和土地,什么都能忍让,但地不能让、房不能让,为了土地问题,村干部哪怕有一次的处事不公,乡邻们也会怒气冲天,大打出手,以命相搏。许多恶因造成的恶果,不断循环,形成惯性。
在我国人均土地零点七九亩,与法国的人均二十亩、美国的人均一百亩无法相比,我国的区区十八亿亩耕地真的少得可怜。国土资源部规定,不仅要守住这18亿亩耕地的硬性规定不能破,还要充分发挥利用好这十八亿亩耕地。面临农村的耕地空置、乡村空巢、产业空心的现象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城市的拥挤已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城市的建设用地越来越少,为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建成大面积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优化区域土地利用布局而提出了“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实现农地集中、居住集聚、用地集约“三集中”,效益集显的一项系列工程。打破城乡二元格局,遵循“耕地面积不减少、建设用地不增加、农民利益不受损、国土规章不违背”的四项原则。采用增减挂钩法(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以缓解城市用地矛盾。
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拆难,归还难,资金难,项目落户难,土地流转遇到大难,新的违规用地出现,城镇建设用地占用了一部分土壤肥力高的优质耕地,通过整理农村建设用地补充的耕地有些是土壤条件差的劣质土地,补充的土地质量低下,无法产出,加大了复垦的巨额成本,使大片的土地陷入岑寂状态。
我的家就住在那条清凌凌的河边。
拆迁后村庄里的树集体失踪,河塘断流。没有树,鸟把家搬走了;没有河的地方,再优良的种子无法发芽生根;没有炊烟的地方,家也没了。
每年回乡都会到河东河西走走,听乡亲们说村里的事,一坐就是半天,他们是村子里的活地图。老人们说,这里的每寸土里都埋着我们家族里的先人们,到田里做农活,当靠近一座坟的时候,我们连说话都很注意,一不高声,二不妄言,地底下的先人们竖着耳朵听着呢,千万别以为他们听不到,无论你们以后走多远,你们不能和自己的血地生分了。
死无葬身之地的华父(节选)
泥土和人的大脑一样,会记忆许多东西,养分,空气,植物,水质,包括人对它的情感。
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来就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
华父肝癌晚期依赖打杜冷丁的时候,天天把《圣经》上的这段话放在牙床上嚼豆子一样磨上N遍也不厌烦。华父是从得了这个病后迷上《圣经》的,书上的有些话他似懂非懂,唯独对这段话烂熟于心。
华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夹在中间最不讨巧。分田到户的时候孩子们还小,只能分到一点生活田,分不到劳力田,家里的田比别人家要少得多。等六个孩子的羽毛都长齐,浑身有力气种田时,华一家三亩生活田打的粮食已填不饱六张饥饿的嘴巴。华的两姐一妹早早嫁出门,省出三张吃饭的嘴。三个儿子只有一处宅基地,盖不成屋,华父决定留头尾两儿子在家,各分一间屋给他们成家,老两口住门朝西的厢房。只能让中间段子老二“嫁”到别人家做倒插门女婿。
华不愿意做人家的上门女婿,看着娘老子红红的烂眼泡子,尽管心不甘,咬咬牙,心一狠也就乖乖地去过端人家饭碗受人家管的日子。
华说,如果不是强势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万顷良田,父不会这么早就过世,什么道路做成“回字型”框架,“王家型”亲水风光带,“哑铃型”集中居住区,这些与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要一提到父亲的死,华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带着寒气,一个字一个字从牙齿缝里蹦出来。
可是,现在田不集中耕种,又能怎样?
父在听到整个村拆迁的消息,嘴巴开始“哑”了,他选择了把那些想要说又说不出来的话硬生生地吞到肚子里。日头心到在里用脚步子当尺在自家田头量面积;夜心坐在院子里看月亮。风一吹,太阳光下的麦田就旋出一圈圈涡,那股风一直旋到他的脚心。他们家的这块田是村里百里挑一的好地,每块土疙瘩都用手捏得碎碎的,一棵杂草也没有。只要一闭上眼睛,田里的土香味直冲头脑,葬在田中央的祖宗亡人们跑到他眼前,在他耳朵边喋喋不休,让他白天黑夜都头昏脑涨,眼白被红血丝填满。华父夜里在露水的天井里坐得太久,受足了寒气,就开始感冒发烧,眼泪鼻涕直掉,后来低烧半个月不退,老伴说是受凉了,喝点红糖生姜茶就没事,一直当成伤风感冒在治,直到后来四肢使不上劲,跟瘫巴子似的,家里人才反应过来,到县医院一查:是那种把人打进十八层地狱的恶病,癌!
得了癌的华父没舍得拿卖稻子的票子去化疗延长寿命,回家后还是习惯到田头转,他对家里人说,自己的日子怕是挨不到收麦场吧,就算是挨不到,死了能葬到自家麦田里也不冤。
华的太爷是大地主时,亲戚们向他借钱,他把票子卷紧塞进芦竹管藏进泥墙缝里;冬天舍不得用草烧锅,冻芋头放太阳底下晒化了再吃,天再冷也穿蒲草编的木底鞋,到死没穿过一双布鞋。泥墙缝里的票子全部买了田。土改时太爷的十几亩田和小青砖瓦屋全部归公,太爷也因此变成半痴子。一家几口人分了两间土坯屋,太爷六十岁不到就戴着地主的高帽子入了大集体的土地。
华的爷爷在生产队挑粪担子挣工分,忙活大半辈子把土坯屋换成砖茅草(外墙红砖,内墙土坯,屋顶盖麦秸秆)。麦还没到开镰的时候,米缸已经底朝天。下半夜正是瞌睡如山倒的时候,华经常半夜被母亲摇醒,华跟在母亲后面,双臂环抱着自己冷兮兮的身子,走在朦胧的月色下,踩着自己的影子去生产队田里揪蚕豆角子、青麦穗。走到田边,露水里饱实实的豆角子在月光下闪光,瞌睡顿时跑了一半,稀里糊涂揪上一气,耳朵竖起来听,远处的狗叫依稀。个把小时就能揪一篮子豆角子,分不清叶子和果实,母亲让他送回家再跑几趟,多弄几篮子藏到床肚底下慢慢吃。蚕豆壳子怕人看见,直接扔进大河沉下去,从来不敢炒蚕豆,炒的蚕豆会有香味,只能水煮着吃。有的村干部的鼻子比狗还灵光,一闻一个准,逮到了要被挂牌子开批斗会,全家人会抬不起头来。但也有睁一只眼、聋半只耳朵的好村干部,就是看到听到闻到了咳嗽几声也就拉倒。等到麦场到了,饥饿总算告一段落。
队里的保青员(麦田巡察员,专门看护是否有人偷庄稼)第二天到田里看,小脚印叠着大脚印。华一家到年关不仅分不到粮,还要倒贴。那年代,全村人从大到小几乎个个是贼,想着法儿偷地里的庄稼。哪一夜不偷,第二天就饿肚子。夜里看不见,一部分庄稼被脚和篮子扑断,等到庄稼正式好开镰收割之时,大部分只能收空秆子,果实有一大半在半熟的时候就进了村里人的肚子里。
华爷爷只偷祖上的那块地,偷得比别人细心,下脚特别轻,舍不得踩坏苗,偷黄豆棵子连根拔,叶子和豆荚混在猪草里切碎了煮熟喂猪,豆米人吃。有次夜里偷庄稼给队长逮到了,队长罚了他家半年的粮食,保青员被罚了一个月的工分。
华爷爷逢人就说:这本来就是我家的田……
队长听了揪他的耳朵:你再说,把篮子套你颈上到社场上开斗争大会,示众。听到这话,华爷爷从此屁都不敢放一个,再不敢说那块田是自己家的。
华父也当过生产队的保青员,在他保青时,队里的贼越来越多,后来队长撤了他的职,让他和社员一起挑粪担子。华父天生雀盲眼,白天看东西一层雾,晚上点了灯也看不见,等于睁眼瞎子。队长动了恻隐之心才照顾他保青,对于村里这帮比麻雀还机灵的孩子,队长没考虑到华父的雀盲眼根本无法胜任保青员一职,连一帮孩子都弄不住。
村民们自觉地和华父搞好关系,就是被他逮到了睁一只眼闭只眼就算了,华父做保青员成了“群贼”的保护伞,队长没办法请他下台。
华父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八零年分田到户至今,一脚踏进天堂,总算不要夜里起来偷庄稼,年底不要再看队长的脸色分粮。华父老两口跟小儿子过,熬了几十年才有能力把原来几间七架梁瓦屋翻建。从乡信用合作社取出三十一万花票子时,华父的手抖擞了起码一小时,心跳的频率不低于当年在夜里偷蚕豆。为了建两层小洋楼,华父不分白天黑夜到远处去找有粘性的好泥,好把新地基垫得高点,再高点。摸黑推泥,华父掉进路边的水渠里,脚踝粉碎性骨折也没好好休息半天,苦撑了四个月剥皮抽筋的日子,两层六上六下的小洋楼竣工,六个孩子每人两间,四间厢房,圈一个大院子做谷子晒场,留一小块地种点果树和花草。刚建好的两层楼还没来得及刷涂料,华父听到拆迁的风声慌忙歇工,村头的大喇叭里天天播拆迁的消息,华父从那以后天天睡不着觉。
华父觉得这次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劲大,不仅是征了耕地,整个村子要一锅端,大扫荡一样。土改时收了地,到改革开放分了地,现在又收地,只是原来的分与收,地还是地,村还是村,还是农民在地上拾掇,天天能看得见地,现在征了地,到死也见不着地了。国家定的基本国策三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才过几年安生日子?眼睛一眨,公鸡变母鸭,全变了。
华父逢人就说,只有懒的人,没有懒的地,只要舍得出力气,田里总会有得收,如今田被没收了,等于手和脚被剁掉。没手没脚的人不就是个废人嘛,坐吃山空等死。
华父和几个子女说:你老子死了也不是农民了,只能到天上去种地。
这个村在雅周镇杭窑那边是最大的村。后来更名为东楼村。东楼村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三十个小队,每个小队一百五十人左右。每天上门来谈的人走一批来一批,华父牙齿咬得“格嘣嘣”响,死活就不同意搬出才盖好的楼房,直到后来没力气咬牙切齿为止。全家老小把他连哄带骗抬到几十年前就入赘到外乡的华家,等着阳寿耗尽的时刻。父告诉几个子女:农村人以种田为主,无田怎么生活,城里人吃根青菜叶子都要去买。自己有田,一分钱不拿饿不死。尽管种田不划算,得看天,旱涝无法保收,可是田是自己的,一季长得不好,下季可以翻本,田要是收了去,连翻本的机会也没了。
看到父亲这般苦熬,华实在不忍,硬是掏出几万把父亲送上手术台,希望医生能给个说法。华父劳累了一辈子的胸腔已被癌细胞迅速占领,已无法下刀,怎么打开又怎么缝合上。医生告诉子女们,想吃想喝什么都随他的愿,想到哪走走让子女陪着。要是到了疼得吃不消的时候喊村里的赤脚医生到家里打杜冷丁。反正晚期,横竖要去阎王老爷那报到,省得糟蹋钱。这么多年卖粮的钱留给老伴养老,给六个子女减轻点负担。华父最大的愿望是:能死在自己家里就好。最后的几个月,华父除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不下田,就是半夜醒了也摸到自家田里去看看,走不多远的路就气喘,胸腔里的疼像刀子在剜一样。老伴骂他贱骨头,和泥巴打了一辈子交道,身子骨都到了这步田地,还巴着泥不肯松手。
华父卧床不起,水米不进,看见别人往嘴里送吃食时,眼珠子发绿,自己一口也咽不下去。华父还能说话的时候让家人给他准备棺材,唯一的要求:死都要死在自家田里,必须葬进祖坟,如若不然,到了阴间心也不甘。
大儿子说:“人死如灯灭,老宅被挖地三尺,扒皮抽筋,挖掘机都碾了十八遍了,这辈子也回不去;田已经不跟自己家人姓,自己说了不算数,就是有了棺材总不能葬到天上去。祖坟都迁到公墓,上面一次性补贴三百,现在三万块放在眼前都弄不回一点地。”华说:“我是人家的上门女婿,一个女婿只能是半个子,这是人家的家,田里只能葬岳父母,灵堂都不能设在家里,更别说墓地。”自从拆迁后,拿了拆迁款的老三像只从田里出逃的大鸟,满天飞着找麻将搭子,泡在牌桌上人瘦毛长,两眼输得发红,二十四小时不归家,华父对小儿子已无话可说。三个姑娘嫁出门如泼出去的水,丈夫家的老人在世,更是进不了她们家。华父死活不愿意进公墓,说在世时大房子住惯了,死了住那个巴掌大的地方,魂不得安生。从中央到地方都兴入土为安,凭什么种田的人就不能入土?最后还是老伴一把鼻涕一把泪苦劝,说儿女们都有自己的难处,不是不想答应他的最后一点要求。华父闭口不再提棺材的事,念《圣经》上的那句话更加频繁,嘴丫子两边念得泛起白沫也停不下来,儿女们说他着了魔,想入土为安的心思太盛,归期比医生估计的时间起码提前了一个多月。华父最后实在念不动了,跟子女们说:等他死了后,把那本翻得边角起毛的《圣经》烧给他带到那边去。一周后断了汤水,脚一蹬,咽了气,两眼睁得像没光的灯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