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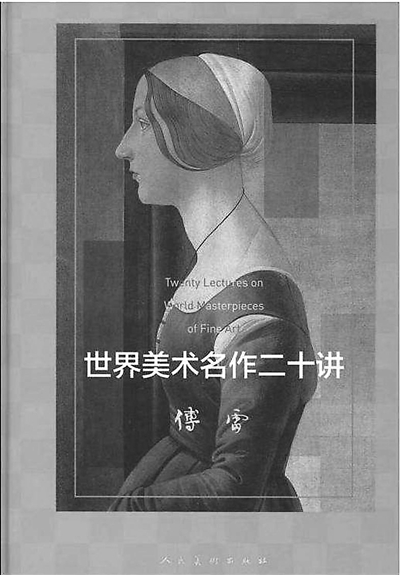

傅雷先生的美术讲稿谈的都是鼎鼎大名,生怕与西方美术史的权威错位,而陈丹青的美术史生怕与任何美术史对位。远看像是美术名著欣赏教育课,近看却是美术史的边角料翻身课。被美术史近乎开除了的名单掉了个个儿,成了录取通知书。
晚清的倾颓落后,使西学东渐远迈前古,民国以来,翻译与介绍外来文艺不绝如缕,译介兴旺、学术昌盛。这段历史的因果对现在的你我有如太平洋对岸的蝴蝶翅膀亭亭扇动,单就绘画而言,我特选了时间相隔近百年的中国美术界的两枚贝壳,来看看美术如何发生在中国。
第一枚来自傅雷。缘起是年初,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书,读罢甚喜,推荐给众友。
回看傅雷,知学海无涯而常惴惴默默、孜孜矻矻,一个意气风发的民国少年出去,一座贯通中西的文明大桥回来。他带回来的欧洲文明一度使他留学的巴黎成了中国人心目中艺术与浪漫的代名词,国人想认识欧洲,就可以先去访访傅雷的文字。这二十课讲稿中提到的艺术家不多,以点带面,纲举目张:乔托、多纳泰罗、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贝尔尼尼、伦勃朗、普桑及几位英法画家等,挑讲了美术史上的重镇关卡。以一种力求扼要“启蒙”的逻辑,以及兴中华之现代美术的愿景,所述皆名家杰构,从学问、人品、操守修养、所涉时代环境,谈史论理,以示听众艺术之因果,种下一片兴旺的愿种。美术,作为人类审美之延伸,并非刚需,可人不是走兽,一群美盲创造的世界会何等自掣自肘呢?傅雷先生留给我们的这二十课,不仅仅是指出了欧洲那一堆作品与知识,更是把人类关于美最高的境界从此延伸到中华民众的唾手可得之处,为你兴魂动魄,帮助诸位成为更完整的人。
时隔近九十年,第二枚贝壳来自画家陈丹青。
读完傅雷的书之后,我的第一个联想念及陈丹青“局部”系列视频的出版:《陌生的经验——陈丹青艺术讲稿》,成书时陈丹青年62岁(傅雷的艺术讲稿成于26岁),前后共十六课,每课千字,与傅雷“经典美术史”的立足完全不同的是,陈丹青“身在曹营心在汉”,统统借题发挥,弦外有音,入于过去谈出现在,常常使人得鱼忘筌。古、今、中、西,信手拈来,仿佛历史被抽走了时间与空间的序列,成了随时待命奉调的兵将。
书名起“陌生的经验”,是一桩一石多鸟的“陌生”,逼人铭记的“陌生”:
就陈丹青先生自己而言,作为写作的《陌生的经验》是独特的,因为是作《局部》系列视频所备的讲稿,我们听一集二十分钟的课,先生大概要花费半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准备,在历史的缝隙中抽丝插针,直到定稿交付了,再录制数个钟头。拍摄罢,先生最大心得竟然是对演员职业心生崇高的敬意,从画家到“演员”,此为陌生的经验之一。但就内容,虽然先生熟识中西古今的美术,但老来仍有“艳遇”,他把布法马可的《死亡的胜利》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曾说:“去年我闯进墓园,意外看见一幅从未见过的巨大壁画,当场魂灵出窍。文艺复兴的大部分名作,我自以为知道,怎么这等伟大的画,从来不知道呢?这就是无知的好处……你完全不知道一位画家,忽然撞见了,更是大快乐。那种惊讶、欢喜,等于变回小孩子……艺术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是本能,是骚动,是崭新的感受力,直白地说,其实,是可贵的无知。”从先生对“无知”的有知,对“陌生”的熟悉里,仿佛倒立着一座金字塔,塔尖立在《死亡的胜利》上,而所有的上层却一丝不苟地建筑与歌颂“陌生与无知”,照顾美术史势利眼下的炮灰。即便是那些美术史上鼎鼎有名的作品,先生却就其引我们朝向陌生的角度,他借他自己的陌生,谈了他的熟悉,借了我们的熟悉,谈出我们的陌生。此为陌生的经验之二。
就读者而言,尤其是文艺青年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陌生,更像是一种稀缺的惊喜。虽然我们顶着一个嘈杂的市场,但是从立意构思到表达技巧,作为画家与作家的陈丹青谈艺术,远远超越BBC在内的许多文艺节目,当然他会说这是导演谢梦茜的功劳。诚然,许多读者“不知盘中餐”,又何妨这样陌生的经验出现在历史的街口,且它必将成为中华美术历史中绕不过去的山头。史航在序中记到:“生于今世,麻木最易,敏感最难。海量信息冲刷一切,世界前所未有的透明,守着搜索引擎。给我十秒钟,什么都查得到。然而查到也就是查到了,哪有什么惊喜可言,铭记更是奢谈。下次再用再查,永远可依探囊取物,也永远两手空空……再度艺术史,再看到这些艺术家被标签化,我们仍只能袖手旁观吗?”换做古人一日三省必加问:今天,我“陌生”了吗?以上作陌生的经验第三。
就美术史本身而言,不论是谈法或是取材,恐怕更是陌生得肝儿颤。傅雷先生的美术讲稿谈的都是鼎鼎大名,生怕与西方美术史的权威错位,而陈丹青的美术史生怕与任何美术史对位。远看像是美术名著欣赏教育课,近看却是美术史的边角料翻身课。被美术史近乎开除了的名单掉了个个儿,成了录取通知书。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布法马可的《死亡的胜利》、蒋兆和的《流民图》、巴齐耶、瓦拉东母子、民国女画家关紫兰、丘堤,徐扬、卡帕奇奥、苏里科夫、安吉利科……好一副耶稣的心肠:天堂里住着的非但不是在世显赫的财主,却是受苦的乞丐拉撒路;世人看来,好人才能上天堂,然而天堂最后的居民却是一帮祈求怜恤和宽恕的罪人。美术史的图景俨然成了反转片,甚至鼎鼎大名的梵高先生,从千百幅大名鼎鼎的作品里,陈先生精心为其挑选了一张名不见经传的油画草稿,封了个“憨王”,谈了令小心维护美术史威权的观众们“不敢听”的“未完成”,直至编织了美术与商贾的社会关系流变之网。这样貌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点,直到今天还会有很多人表示看不懂,不了解。善哉,这就是陈丹青羡慕的状态,想要的效果。这是第四个陌生。
当然,还不止这些陌生。所有的宗旨都没有变,一切的陌生都是为了恢复观众读者的应该的熟悉——对艺术的“直觉”。如果你是职业画家,他告诉你,不要害怕权威:一切对新意的屠杀,不正是“正确”和“现成”的功劳吗?如果你是路人看客,他提醒你,不要迷信权威,虽然你不能指鹿为马,但至少你可以在诚实中积累进步。对权威的爱与怕,是需要保持平衡的,面对大师,你不能只是磕头,但也不意味着飞扬跋扈。当然,大多时候我们需要导游,尤其是美术这样的深水迷宫,许多人会转得一头雾水,所有问号汇成一句话:怎么办?面对不确定的信息,需要有确定的信息来安慰不安。陈先生在《陌生的经验》后记的结尾引用蒙田的话:
“人类的所有不安,就是回到家里也静不下来。”
又说,他所提到的那些艺术家们,真正赋予了他讲稿的价值,“他们的伟大,他们的好,远远超过了他的讲述。”
前半句看起来点了观众,其实说出了艺术家;后半句提了艺术家,其实给观众塞了锦囊。
将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陈丹青《陌生的经验》两枚艺术海岸上的贝壳放在一起,不是为图艺海拾贝凑出两位来增加什么效应,为当下的萧条的美术博些眷顾或同情;也不仅因为他们都出于上海,这个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从地缘的角度看百年来文艺传播深入的程度;不仅要比较、突出傅雷的恪守学术与陈丹青的超越学术,也不仅是提醒爱好美术的人去深挖这两座宝库;也不是逼着大家成为傅雷或者陈丹青,去归正美术史的纲纪或是成为寻找千里马的伯乐。我相信有心的人,总会铁杵成针、水到渠成。
总之,借引刚才的两句话,还是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的:
“伟大的艺术家可以安静下来,优秀的观众可以常常惊觉艺术家的伟大。”这就是美术存活在历史中的纲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