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樱桃青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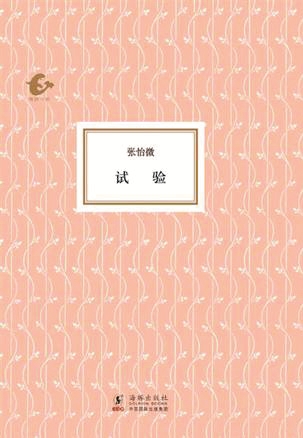
《试验》 海豚出版社 2014年

《细民盛宴》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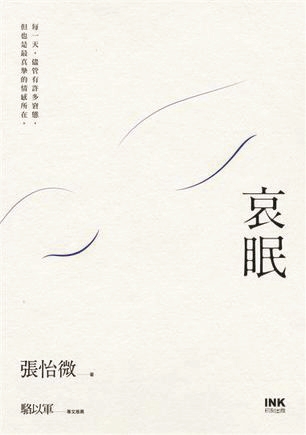
《哀眠》 INK印刻文学 2015年
提及“80后”一代作家,人们的眼光似乎总是会被最具争议性和代表性的韩寒、郭敬明所吸引,而对于同样“受惠”于那个时代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显声于《萌芽》杂志,并从此崭露头角的张怡微来说,她的写作与成名之路似乎更低调而稳实。
从上海复旦大学的学士到硕士,后又成长为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张怡微一路经受着文学教育的滋养,曾跟随王安忆等名师学习写作,一度用勤勉的创作侍奉自己的文学之梦与生活。而从2004年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开始,到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1987年出生的张怡微所获奖项遍及两岸三地,甚至一度被称为“奖项猎人”。
岁月悠悠有如车轮辗过,恍然间,这个在许多人眼里还贴着少年成名标签的女孩,也已步入了而立之年。无论是曾经的青春文学,还是张怡微后来所热衷和书写的“世情小说”,她的文字里总有一股“老成之气”,一种对于冷暖人情和伦理世情的描绘与钩沉。与许多“80后”作家惯常的私人化写作不同,张怡微的写作总是探寻城市的历史深处。祖父辈的生存状态,城市空间里的人情世事、人心变迁成为她冷眼观察的对象,而时间上的回忆和追溯也让她的作品增加了厚度和深度。
近些年,张怡微更是开启了一个关于“家族试验”的写作,探索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故事,从海豚出版社的《试验》,印刻出版社的《哀眠》,到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小说《细民盛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现代人及家庭的伤痛与宽容、失落与满足、记忆与遗忘,都在她笔下缓缓流露。借着访谈,我们得以走入这位青年作家细腻的文学世界。
谈老师
王安忆的教导是很严格的写实训练
晶报:你在大三时就开始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之后的写作也渐渐告别青春题材,但在很多人印象中,你可能还是当年刚获奖不久的那个小女孩,你介意别人称你为青春文学作家吗?
张怡微:完全不介意呀,《樱桃青衣》这本书里一半的小说都是在《萌芽》发表的。年轻的时候热爱写作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五四文学很青春,伤痕文学也是书写青春。现在别人问我简历上写“作家”可以吗,我都说加一个“青年”可以吗?我觉得挺高兴的,对于别人觉得我还很青春这件事(笑)。
晶报:台湾求学时你靠着自己写作的稿费、奖金养活自己,这段经历在你的许多散文里也多有提及,你是怎么看待这段时光的?
张怡微:写了很多烂东西,这是无疑的,我在台湾读博士第一年的时候,一个月可能写三四十篇专栏。此外还要上课、写论文、发论文,投稿文学比赛等等。现在唯一的感受是,终于摆脱了当时那种糟糕的生活。不过也不是全都糟糕,那段经历的好处是因为没有办法考虑太多,几乎什么都写,因此也关注了很多不同的领域。那几年我写得的最长久的专栏是在《东方早报》的《上海经济评论》,这逼迫我关注了大量文学以外的世界,关注社科的文献,以至于我现在的确对文学以外的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很感谢我的编辑,会那么大胆跟我邀稿。
晶报:你在大陆就学时就上过不少写作课,比如王安忆的,而在台湾时上过一学期的创作课,这些写作课程对你有什么影响?
张怡微:王安忆老师给我的教导是非常严格的写实训练,她给我提意见的时候,会说这个小说人物的年龄你算错了吧。时间上她会问得非常细,这个人是多少年来的上海,当时上海是什么样的时地,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她是跟谁一起来的,当时有没有政策、空间容许这个人物自由来去,等等。她自己也会比照着历史地理推策小说发生的情况。比如她曾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仔细比照过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分析小说中人物的来历、家乡背景。一般人读一个小说,看到不熟悉的地名,常常都是跳过去的。王安忆老师有她“看”世界或者说看小说的方法。
在台湾上创作课,一是在描绘庶民生活的方面,我听了很多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又找到了不少看世界的角度。二是在汉语的风貌上,我的确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层次。比方在对语词本身的想象力方面,因为台湾文学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非常大胆地建设汉字所能够呈现意象的潜能,这点对我启发很大。
谈“家族试验”
素描生活是一种非常基础的训练
晶报:你对于世情小说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张怡微:我不知道怎么来说这件事,实际上看小说本身就是很私人化的,发自个人的爱好。像我很喜欢《三言二拍》,也很喜欢李渔的《十二楼》,韦尔蒂、特雷弗,他们肯定有一些共性,比方对于烟火人间的关注,对于世相人心的解读。包括我自己博士论文做的是明代《西游记》续书,后来也因此写了一个关于《西游记》原著的随笔《情关西游》,也是以类似的方向进入到古典文本当中,希望能够重新看一看是不是有更贴近人情世理的读法。
晶报:为什么会想开启这样一个“家族试验”的写作系列?
张怡微:2014年我在海豚出版社出过一个单行本小说《试验》,里面收了两个小说。《试验》比较典型写的是老中青三代不是一家人却以一家人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过年的时候也一起吃团圆饭。当时我就想找一些类似的故事,一群接近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命运最终以一家人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缘于有这个想法,所以才去寻找故事,《樱桃青衣》里就写到了过继、无后、失独、老年人再婚等等。这些故事里,有些“家族试验”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有些成功了一小会儿,有些失败了反而令人怅然若失。
晶报:在你的故事中,有很多非原生家庭却拥有“不是滋味的团圆”的饭局,比如《细民盛宴》里,袁佳乔经历了八次大大小小的家宴,你为什么会花大笔墨描绘中国家庭饭桌上的场景,是否与你自身经历有关?
张怡微:“去吃饭”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件很重要的事。我的确是单亲家庭的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讨厌吃饭,或者我吃过的团圆饭都是不愉快的。写小说是一种经验的魔术,也就是说所有的经验材料都是日常生活中撷取的,但这些材料却可以推理至一个抽象的、感知层面的可能性。
至于“饮食”就非常非常复杂了,一方面食欲与情欲相互勾连,另一方面比如《饮食男女》电影中,谁占有厨房其实是一种家庭内部话语权的展现。社会学意义上,厨房不是客厅,是更加真实的生活环境,而不是展示性的整洁、温馨。电影《过年》也很精彩,团圆饭因家庭成员内部的各怀鬼胎,最终一地狼藉,那还都是真正的一家人。不过,没有血缘关系的呢,也不一定就真的隔阂。我们常常会觉得,有时对家里人无话可说,亲人们总是很友好地误解你,但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一方,可能又很谈得来,这是生活本身的魔力。
晶报:不只是“家族试验”,在你的很多故事里,都有悲喜剧的意味在其中,你自己在文章中也有提到这种“反差的实验”,比如“一次糟糕的婚礼”,或“一次令人忍俊不禁的葬礼”。诸如此类的母题训练,与你所受过的写作训练有关吗?
张怡微:对,我前几年写过很多类似的练习,主要是素描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基础的训练。实际上无论是小说《乐观者的女儿》“你要在该哭的时候哭”;还是韩剧《请回答1988》中德善奶奶过世,家里人居然都表现得谈笑风生;还是《情书》里渡边博子参加藤井树的周年祭发现所有人都已经不悲伤了,只有她内心的疑惑和感伤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但这种反差的呈现是很常见的,它是一个经典的场景练习。
谈婚姻
婚姻是两个人的阴暗面在相处
晶报:《樱桃青衣》取自唐传奇中的梦幻母题,为什么会想到以这个故事命名?
张怡微:“樱桃青衣”是唐传奇,它跟《枕中记》、黄粱一梦、南柯一梦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和“蕉叶覆鹿”的意象也类似,就是一个士子在梦境中经历荣华富贵之后又醒来,感觉到大起大落后的荒凉。因为我当时在研究《西游记》,发现《西游记》中所有的梦都指向死亡,我在《情关西游》中有详细谈到这一点,这和唐代传奇中关于“梦”的指向反而很不一样,黄粱一梦并不指向死亡。另一方面,“樱桃青衣”中涉及梦的内容又是极其世俗化的,香车美女、富贵功名、游宴欢会,倒也是很有意思。
晶报: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有这么一句话:“樱桃青衣”是听心里的时间说话,蕉叶覆鹿是创造的本质。似乎也暗示着你对小说创作的感受。
张怡微:小说是一种魔术,一种剪裁经验。我有一个朋友是卖鞋子的,她的客户会跟她反映,穿你的鞋子我脚疼。她脚疼这件事是真的,但小说不是描述这种经验。小说需要的是把一个人的生活情貌,所有的经验素材重新整理拼接,指向“你疼吗”,或者“你应该不疼”,或者“可能疼却又要忍耐”,它指向的东西都是不确凿的,充满了可能性。那为什么是变戏法呢?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假的,却还要看,说明这中间有比真假更重要的东西,扮演的趣味、玄虚的创化。我喜欢这种创造的快乐。
晶报:在《樱桃青衣》里,多次出现“表情包”这个意象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度桥》一文中,这无疑是网络社交形式带给人们交流方式的一种冲击,你是否对“表情包”有深刻的体会?
张怡微:我最近对社会和传播学研究兴趣非常大,很想写《新垣结衣今天笑了吗》诸如此类的故事。不仅是表情包,还有弹幕、二次元、手办、爱豆、猫文化……所有次文化繁荣的背后都有社交的困境,有人与人沟通的困境,有人与真实社会的联结趋弱的现状。我们如果没有进入到类似精神的世界里,是难以理解这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年轻人)在网络社交上倾注了大量真实的时间、感情和金钱,甚至十分依赖虚拟平台。现实生活不过是他们复刻自己内心景观的呈现。
晶报:在你的许多故事中,体现着这个时代女性对于婚姻的一种或抗拒、或忧虑、或不安,这是否也暗合着你对婚姻的看法?
张怡微: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写小说需要持有一种情绪稳定的偏见。我既然知道这是偏见,显然会和真实生活区隔开来。总而言之婚姻是两个人的阴暗面在相处,所以不是看你最好一面和他最好一面合不合,而是看你的阴暗面和他的阴暗面合不合。所以先要毫不作弊、恬不知耻地知道自己的阴暗面,其次要有办法发现对方遮蔽得很好的部分。但一般来说这样的事想不清楚的。嫁错了也没关系,大部分人都嫁错的,可以改。
谈写作
我挺幸运的,至少还在做喜欢的事
晶报:你说过,写作于这个时代作为一种精细的劳动,虽然“珍稀”,却有许多依然坚持“耕作”的写作者。感觉你身为这其中的一员对此挺感恩。
张怡微: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至少我还在做喜欢的事,现在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还能把阅读经验和写作经验分享给更年轻一点的写作者,这种角色的转化让我想起许多影响过我的人。
晶报:在《我自己的陌生人》里你曾提到作家于这个时代的一种“不适”——当作家本身就等于选择了一种不孝。似乎这也曾是你的心结。这么多年来,你是如何自我和解的?
张怡微:我父母都是工人。我本来觉得我自己养活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不跟家里人拿钱,我就是一个挺好的女儿了。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工人家庭对于爱读书的孩子都是过分包容和宠爱的,家长们即使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觉得读书总是对的、总是好的,你脾气差一点,也会让让你。我觉得我是过了三十岁,才意识到自己的选择给身边的人所造成的压力。有些事没法和解,只能从现在开始好好对待身边的人吧。
晶报:你曾坦承自己不是一个“整齐”的作者。写作17年,在这条路上,你走到哪一步了?
张怡微:我写过很多无病呻吟的书,也写过很多强说愁的书,后来假装写了很多严肃的书,到现在终于反省自己浪费了太多纸。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只能说未来写得更好一点。我不算写得有多好,但也是很认真在学习写作,有一些基本的经验,成熟说不上来,但我想我算是一个成熟的读者了。
晶报: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有遇到瓶颈期的时候吗?怎么克服?
张怡微:面对瓶颈也不会有别的办法,除了多写。写作没有捷径,所有的经验都需要不断巩固。我一个月会有三万字的产出,不管有没有发表。我目前有两个“情关西游”专栏,有一个写“通俗文艺”的公号,还有一些散文,方便我不断给阅读归类,也当备备课。
晶报:《樱桃青衣》算是你“家族试验”的收官之作吗?接下来有什么规划?
张怡微:是的,我想写一点新的故事,也会继续做古典小说的研究。去年入围了台北文学奖金奖,今年已经提交了一个小长篇《台北runaway》;明年上半年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修订后的博士论文《蛇足之辨》,讲到了明末清初的三部《西游记》续书,下半年还会出一本通俗文学散论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