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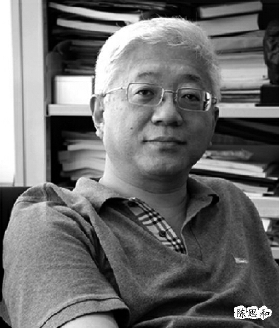
编者按:
陈思和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对文艺理论及当代文学现象有着细腻而深入的研究。本报记者日前就当代文学现象、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发生、如何推动当代文艺繁荣以及文艺评论所应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陈教授。
深刻的记忆
与好作品联系在一起
学术周刊:陈教授,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超过30年了,可以说见证了当代文学起起落落的漫长经历。回顾您的文学批评历程,有没有令您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
陈思和:其实,30多年的光阴,文学史上只是一瞬间。有时候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某部文学史著作里不过一两页的篇幅就概述过去了。但是20世纪的文学是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开端,这个发轫期来得非常猛烈,辞旧布新,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在未来的文学史上,这100年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但是它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留下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很多思考,会引起未来学术界的长期讨论。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接受教育的学生,后来留校任教,研究现代文学。当时的文学创作尚处在“伤痕文学”的草创阶段,但已经起步。社会正在走向改革开放。文学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迅速反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有魅力之处。我被这样的文学深深吸引住了,所以从学术研究中转移注意力,转向当代文学批评。
在考入大学前,我曾经在一家图书馆做过书评工作,但正式介入当代文学批评的,是在1978年8月。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控诉了“文革”给青年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我与卢新华关系很好,我们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还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有一点缘分的。我发表评论文章,肯定了《伤痕》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这以后,我与当下的文学创作发生了30多年的交集,文学评论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除了“伤痕文学”外,对我来说,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有过几次:一次是1984年底在杭州参加会议,讨论“寻根文学”。那时候也没有“寻根”一说,是当时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这篇小说,贾平凹发表了《商州初录》,阿城发表了《棋王》等,这些新小说不是按照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写作的,却展示了隐藏在生活底层的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这些奇异的文化现象介入创作以后,在小说美学上产生冲击力,形成新的美学视野。这个时候西方文论也开始大量被译介进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又一次发生交汇,我觉得自己的学术视野被打开了。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找到了一条介入当下文学创作的路径。
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张炜创作了《九月寓言》,在“寻根文学”基础上更加推进了一步。他把民间传说、野地趣味、魔幻手法、当代情怀都熔为一炉,小说文本里处处散发出奇异火苗,传统的文学批评原则与措辞无法解读这样稀奇古怪但又是自然天成的文本。如果说,寻根文学产生的新的小说美学还是粗糙、人工的,那么《九月寓言》形成了炉火纯青的小说美学。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小说美学的革命,需要有一套新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词汇,才能真正解读这样的作品,以推动文学创作的创新。结合解读《九月寓言》《心灵史》《长恨歌》等作品,我开始立说“民间”的批评观念和文学史观,进而形成了一套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言说。
再有一次就是新世纪以后的长篇小说井喷现象。新世纪之初,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莫言的《生死疲劳》《蛙》等一大批作品,当然这些作品有的当时是有争论的。抛开这些不说,我们从这里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经过“寻根文学”、“民间”书写,又回到了作家创作,并发挥出批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的创作方法,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有着区别,它们融合了许多新的艺术元素。我把贾平凹的创作归为一种“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把余华的创作归纳为“怪诞”现实主义。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一路里,王安忆、方方、林白都是代表性的作家;在“怪诞”一路,还有一位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阎连科。莫言也属于“怪诞”一路的现实主义作家。是这批作家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推向了艺术的高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作为这一高峰形成的标志。
作为文学评论者,我的深刻记忆都是与好作品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好的文学作品刺激批评家的观念更新与理论创新,批评家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反过来也会帮助作家的创作。
跟踪当代文艺的发展
学术周刊:我发现您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经历很有意思:几乎每隔十年会遇到一批新的作品,然后从中获得了某种启示,使您在理论上获得一次提升。这种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似乎咬得很紧,也很罕见。您觉得从新世纪初到现在又过去十多年了,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文学创新的爆发期了?
陈思和:这个现在说还早。我在刚才的描述中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所关注的,或者说,我所见证的当代文学的历程,基本上都局限在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我所跟踪研究的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等,基本上都是50年代生人,最迟是在6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如余华、苏童等。我眼中的文学史,是这一代人的文学史。如果你去采访比我更年长的前辈批评家,他们的关注点可能与我就不一样,他们眼中的当代文学史,与我描绘的文学史也是不一样的。由此我提出过“要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家”的观点。因为同时代的作家与批评家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他们的很多思想观点都比较接近,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但局限也同时存在。批评家对于隔代的文学创新未必就那么敏感。说到这里,我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我所见证的文学,是我们这代作家批评家从青涩到成熟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对这30多年的文学比较理解,看的也比较清楚。往后,因为观察不够,我还不太好说。刚才说到从世纪初到现在差不多也有十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十来年中间,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依然在创作道路上发表重要作品,尤其是贾平凹和王安忆,几乎每一两年就会有重要作品诞生,他们依然是主流文坛的中心话题。但接下去呢?我想,是要有新一代的作家继续在创作,继续发展和繁荣当代文学的。目前70后作家几乎是一个过渡。我更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网络文学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已经拥有很多粉丝,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但是他们的成长与前几代作家的培养模式完全不同,资本渗透到文化市场以后,文学生产机制和作家培养机制都发生了变化,文学的评价机制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这些问题,目前在文学领域似乎重视不够,因为一批资深作家还在发挥中流砥柱的影响。但是在其他艺术领域———譬如影视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有不少报道揭露,影视领域乱象丛生,票房、排名、获奖等评价机制甚至可以被金钱收买,资本的力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严肃的艺术劳动受到排斥,被边缘化,而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蔓延,受众吐槽……可是,我想,如果需要的话,资本仍然可以迅速制造出它所“需要”神话。关于这一切新出现的问题和现象,理论界没有很好地关注,也没有直面人生地呼吁和揭露,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我们缺乏自觉面对资本渗透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勇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所形成的传统,如何在今天的新形势新环境和新媒体下让文艺保持活力,继续发挥出积极的进步的力量,这是一个新课题。
期待文学艺术的繁荣
学术周刊:您觉得在新的形势下,当代文学的繁荣需要怎样的条件?作家、文艺评论家还应付出怎么样的努力?
陈思和:如何才是文学的“繁荣”?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我说的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从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文学繁荣的标志,首先是要在短时期内涌现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为什么是“一大批”而不是个别的卓越人才?记得我以前读丹纳的《英国文学史》,里面有论述莎士比亚的部分,原话记不住了,大致的意思是:莎士比亚时代绝不是只有一个莎士比亚是大师,而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在群峦之巅,才有莎士比亚这座真正的高峰。我想任何时代都一样,只长出一棵大树,不能称作繁荣茂盛,只有大片的森林覆盖,才能被称作自然资源丰富。自然生态如何,文化生态也一样的。我所经历的文学记忆中,伤痕文学时代,寻根文学时代,上世纪90年代走向民间,新世纪初长篇小说的井喷,都是有一批坚实的作品出现,有一大群作家诞生。我说的“一大群作家的诞生”,并不是说他们只是自然形态地生存和工作,而是指他们的创作在一个短时期内突然被社会所关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而且有较持久的影响力。譬如当年的阿城、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等等,他们大多数属于知青作家(知青作家是更大的群体),但“寻根文学”把他们从知青作家群体里一下子“分化”出来,迅速建构起新的符号系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强大的艺术再生能力,对以后的新写实、民间……等等写作运动都有实际的影响。我想,你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我所说的“一大群作家的诞生”,这是证明当代文学繁荣的首要标志。
其次,创作繁荣要建构新的美学范式,建构一种新的话语符号系统。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是改变了一种范式。原来的知青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伤痕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展来的,题材也比较局限,而“寻根文学”虽然写的也有知青故事,但创作方法、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境界阔大多了。
其三,文化繁荣是整体性的,不会仅仅局限在文学创作领域。标志着创作繁荣的新的文化现象会成为一种思潮,要有整体性的推动力量,在影视、绘画以及其他文学种类、文化思潮中同时出现反响。文化现象都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背后是一个整体力量的爆发和创新突破,这样才会有繁荣,才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