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最初知道双雪涛是因为《平原上的摩西》,但这里面的作品,大都是他在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之后写下的了。用他的话来讲,在这些作品中,他开始更关注一些细微的东西,努力去写得更漂亮、更加具有文学性。对于这种变化,双雪涛并不排斥,在这一点上,他和他钟爱的作家村上春树有些相似,他们更倾向于将小说作为一种职业,而非将人生变为小说。
但《聋哑时代》有些特别,它更像是一个少年有些急切的自白,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也让人不断联想起作者本人。发生在父母那一辈中的崩溃和重组,在崩溃以及压抑中被忽视的青春,顺着这两条脉络,一场对上个世纪末个人经验的漫长回溯被完成了。双雪涛说,自己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了。我偏爱这部作品,也许是因为它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一部小说。
双雪涛本身也喜欢写人,或者说,他小说的核心就是人,一个个孤零零的、能够被清晰描述的人,这些单个的人本身是一团矛盾、一团情感,与另外的人相遇,又牵扯出新的矛盾、新的情感和新的孤独,人是一切的起点,又是一切的终点。
嘉宾介绍:双雪涛,1983年生于沈阳,小说家。出版长篇小说《翅鬼》、《天吾手记》、《聋哑时代》,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等。

短篇小说本身是一个比喻
搜狐文化:最近在看《聋哑时代》,其实里面每个人可能都是单独的故事,但最后放在一起,故事倒不重要了,比如说《安娜》,它也被单拎出来发表过,那长篇在你看来和短篇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在写一部长篇的时候,你更关心什么?
双雪涛:《聋哑时代》其实是2011年写的,但是没有人给我出版,就一直存着。后来我把它寄到了《收获》,有个编辑叫走走就给我打电话,说写的挺有意思的,看能不能发表。当时应该有12万多字吧,《收获》的版面很紧张,后来就说能不能改成中短篇,我才把里面的《安娜》和《我的朋友安德烈》单独改了,改了之后觉得蛮爽的,于是从2012年到2013年一下就写了十几个中短篇。
《聋哑时代》当时是当做一部长篇小说来写的,写完之后,感觉它的结构还是有取巧的地方,因为它是按照人物一个一个出来的,像《史记》的列传,本身并不特别需要恢弘的构思,把人物写好就可以了,所以它还是没有太满足我内心对长篇的野心。它有点像活页,版型里面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能够改出一两个中短篇。
我觉得中短篇还是需要有很好的艺术感觉,尤其是短篇小说,它跟诗歌有相近的地方,本身是一个比喻,它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实验性,你自己对于诗性的看法在短篇小说也会体现出来。中篇小说的维度和体量都要大一点,需要有更大的故事量来支撑。在长篇小说里,就更需要一个特别强劲的核心了。这个核心摆在那儿,你可以在这个核心里面自由地发挥,可能里面出现的人物都是相互对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声音,每个人都不一样,很散漫,但只要有一个强劲的东西支撑着你,长篇小说就能写下来。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最近也在琢磨长篇小说的问题,我还想写更长的,而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喜欢精细作业的人,有点矛盾,写长篇小说对我来说,需要耗时耗神的练,需要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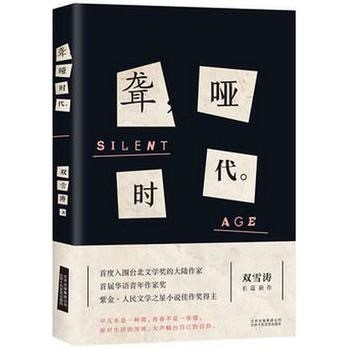
小说就是关于人的
搜狐文化:人物是你觉得表达那个时代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吗?
双雪涛:对。一想到那个时代,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很多人,尤其是同学。我要写的人在脑袋里都长出来了,那怎么把他们组装在一起?当时没有太细想,就先来一个序,摸一摸感觉,写完后我觉得要按照人物来做。本来写了八个人,现在发表的是七个,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物和其他人不太协调就删掉了。我作为叙述者来讲这些人的故事,相当于是我叙述别人,同时又通过别人来叙述我,是一种相对交互的方式。主要是我这个人就喜欢写人。
搜狐文化:为什么?
双雪涛:小说就是关于人的,如果讲一个思想或者阐释一个理论,对我来说有点大,写一个个体对我来说意义更大。
搜狐文化:你对你描写的那个时代是有观点的,之前你也谈到过一些关于时代正义的问题,那这些观点会影响你的人物塑造吗?或者说,在选取人物之前,你就想好了要通过他们来表达一些看法吗?
双雪涛: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其实我的观点我自己在写之前都没有强烈的感觉到,但是写的时候就清晰起来了,我对这个大背景,对所谓学校作为一个社会的隐喻,对于个体的压制和改造,我肯定有整体的认识,然后我才能写这个,但这种认识是很杂乱的。我一边写,这些观点就一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力量。
职业作家不可能永远去写自己的生活
搜狐文化:你原来也说过,之后可能再也写不出来这种东西了。为什么?
双雪涛:那时候有的地方写的挺幼稚的,但也挺真诚的。说白了一个作家,老是掏心掏肺去写,累死了。我记得这本书应该是从夏天一直写到了冬天,持续了五六个月,白天上班晚上写,然后我开着窗户外面下雪了自己都没有感觉。我感觉就是沉浸在里面了,人也变瘦了,抽了好多烟。我得把我认为被埋没掉了,被忽略掉了,被遗忘的历史和个体写出来,当时写这个小说有种责任感,是替我自己发声,也是替我那些朋友、儿时的玩伴们发声。但是写了这么多年之后,就更会去关注一些细微的东西,一些技巧,努力去写的更漂亮,更有文学性,真挚感会下降,这个是我会去努力平衡的东西。
搜狐文化:你觉得这种转变好吗?
双雪涛:我觉得一个职业作家一定得面对这个东西,不可能永远去写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心声全拿出来说,一个作家最开始走上写作道路的时候会这么干。但是,当它一点点变成更职业化的写作后,这种转变可以保护自己的力量,写得更久。
另外,我觉得这种转变也有好处,你能把你的感觉变成一个更有深度的文本,它里头包含的层次更多,真挚的东西会直接地去打动你,但细微的话就没有那么狠,那么直接,那么决绝,可能层次丰富一点,也挺有意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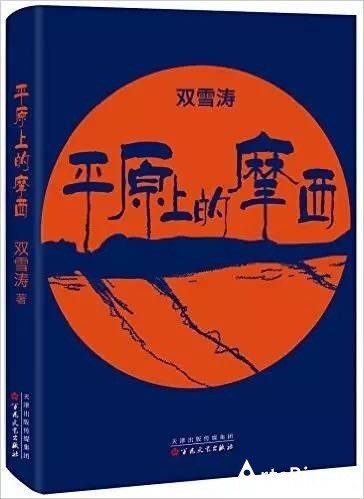
《聋哑时代》的爱情其实是一种强烈的压抑
搜狐文化:《聋哑时代》当中的女生,我感觉有两类,一类是和爱情有关的,像艾小男、安娜,包括吴迪,另一些和爱情关系不大的,像于和美、隋飞飞。你当初是想要用爱情作为一个区别,来表达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吗?爱情意味着什么?
双雪涛:真没有,你的总结挺有意思的,我自己都没有发现。吴迪、艾小男和安娜都是独立的作为一个人物去描写的,那些其他人物就是从侧面写的。可能在我心里也会把有爱情,或者跟爱情有关的人物当做重要人物吧,可能是一种下意识。
搜狐文化:给我的感觉是,爱情让她们活起来了,它是一个可以让人脱离体制的东西。
双雪涛:对,一种光芒吧,它其实是一种自由的向往,而且有时候都变成某种信仰了,在这种幻觉下,有可能会把对方想得特别好,特别完美。它其实是一种强烈的压抑,推动让你一定要找一个出口去表达。尤其是对艾小男的爱,“我”是特别特别沉浸在里面的。
搜狐文化:有点神化的感觉。
双雪涛:对,绝对不是世俗那种爱。那种爱是不求回报的,跳到教室里给她去整理书桌就好了,完全不求回报,就像对上帝的那种。
搜狐文化:那李默与安娜之间,也可以理解为爱情吗?
双雪涛:怎么讲呢?这段感情其实是一种很难定义的东西。这里面有一种欲望,两个孤独的人去相互温暖,也有一种安娜作为一个要溺水的人想要得到别人的救助,然后李默想去施救然后失败,因为这个人还是会堕落的,这两个人其实都是社会里不同程度的一个孤零零的人。他们在大学里遇到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安娜一直记着李默,他对她的意义我觉得是一种善良和温暖,李默是一个劳苦大众阶级的人,他看起来善良和温暖,而里面是冷漠和自私的。这里头的爱情比与艾小男的爱情要复杂。
搜狐文化:我觉得要成人化一点,所以发生在大学里面。
双雪涛:对,是发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世俗化但又不是那么真世俗的,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上一代人有时候越努力越容易失败
搜狐文化:《聋哑时代》的开头写的是崩溃,父母那一代稳定生活崩溃了,然后你们后来一代其实或多或少都生活在那种崩溃之中,但是你后来在父母那保留了一种比较完整的东西,相较于李默和艾小男的爱情,李默的父母他们一辈子在一起,我觉得在末尾其实表达了另外一种爱情吧,你对那一代人有很多敬重在里面的。
双雪涛:我觉得那一代人,有些看起来更笨拙的东西,其实可能是很可贵的东西。在我父母那一代,有很多夫妻关系也不好,也有真的是相濡以沫的。小说里的父母的爱情其实是我对爱情的一种美好想象,其实是很难的,都会吵架,都会有问题,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家如果是条件不好,往下走的话,一定会有很多摩擦。我在小说里面把它剥离出来,把它变成一个童话一样的东西,这也不是一种美化,因为核心是两个人一直在支持对方,在支撑这个家,这个小家比世界上任何事都重要,一定要把这个小家维护好,给孩子好的教育,要有家的样子,父母要有父母的样子,这个是很明确的,当然也时有摩擦,这些问题只是小小的噪音,真正核心的东西还是相互支撑,绝对不放弃。
我觉得最可悲的是,在我父母那一代,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勤勤恳恳的努力,但是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就是会变成一个失败者。因为有时候命运是一只大手,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那代人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脑筋不是那么灵活,说的好听一点就是,非常本分,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非常的僵化。这个东西就导致,越努力工作,有的时候会越失败。
搜狐文化:失败和成功,你自己对这两者的解读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成功的人生?
双雪涛:在我小时候我认为成功就是牛逼,就是有钱,然后有地位。搞来搞去,搞到现在,有很多感觉是变化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可怕,就是这个世界是对失败者很冷酷的。所以,至少从我个人来说,我希望人能活的有那么一点尊严,这个尊严跟成功是两码事,是一种心理感觉。你得穿干净的衣服,你每天需要去洗澡,你得有好的医疗环境,你要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学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通过一些世俗的东西去保障。如果没有这个世俗的成功,每天都会消耗在一些琐事里头,要为一些零钱去奔波。但是,从客观上说,像卡佛这些作家,每天也是在奔波。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说,一个作家不宜被那些琐事消耗和埋没。
搜狐文化:但是他没办法。
双雪涛:对,他是没有办法。卡佛在成名之前,应该算是一个社会的蓝领失败者,一个酗酒者。在美国有这样一类的作家,但是在中国,这一类人很难活下来,会杀死你。对我来说,我心里对成功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我对自己有的保障和尊严比较在意,我希望能保证我心态平和的去创作。
幽默不是调皮也不是杂耍,而是本能
搜狐文化:幽默是你的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风格,有些人是特别怕特别正经地去说一件事,因为那样就太沉重了,有时候幽默会带来一种冷漠,但你的反而让我感觉有一种比较温柔的东西在,你怎么理解你小说中的这种幽默?
双雪涛:首先我觉得自己是爱耍嘴皮子那类的,幽默不是调皮也不是杂耍,是一种本能,它是一种表达方式,在这个小说里我写的一些看起来有点幽默的句子,它本身是有信息的,有我想说的东西在里面,而不是为了耍一个花活,来一个空翻,一个倒立。它在我心里是本能的反应,因为我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的,性格就这样,也愿意说一些反讽的东西,也愿意去做一些语言游戏。
另外,这个小说本身的大环境还是沉重的,所谓的反讽和幽默的表达我觉得对这个小说是有益的。但是呢,在我写完之后,我的整体叙述也没有伤害到这部小说沉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还是恰当的。
搜狐文化:包括你有时候会加入一些稍微有一点魔幻的场景,像那个历史老师,她从窗户出去,你写的是“飞出去”,这给人一种突然和现实拉开了一定距离的感觉。
双雪涛:对,是的。我也喜欢这种东西,喜欢跳一下、飞一下,这都是我在小说里干的,而且这是只有在文学里能做,所以应该珍惜。
要是仔细观察,你能找出一个正常人吗?
搜狐文化:聊聊东北吧,你写的故事很多都发生在东北,东北原来是很繁荣的,现在渐渐有些没落了,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失落和疲惫,你自己对东北的感觉是怎样的?
双雪涛:东北是繁荣或者破败,其实就一个概念,这是我的家。沈阳是一个移民很多的城市,我爷爷是北京人,我姥爷是山东人,我自己的家是两个移民家庭组成的,我父母都是在沈阳长大,我是第三代。真正有几个纯正东北人呢?我觉得很难讲,我个人不算是一个三代以上的东北人,但是我在这儿长大,大学去了长春待了几年,基本上没有离开东北。但是2015年以后,我出来了,包括明年和后年都要在北京待着,因为有距离,我可能能比以前更好地感知东北。
我的感觉是,我认识那些东北人没有被好好的讲出去,包括这这两本小说里出现这些东北人,我觉得是以前没有被书写的,所以我愿意去写一下,我觉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尊严,这种东西是独特的,他们到底是好人、坏人、落魄者、成功者,这个对我不重要。
我刚刚在地铁上看纪德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我觉得好,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狄更斯去比较,狄更斯脑子里有个价值序列的,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没有这个序列,他对人物的看法就是你是行善多一点还是作恶多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当然,狄更斯也会去打破他的序列,比如坏人成功好人落魄,然后又翻转过来,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在另一个维度去想问题善,善恶、尊严、谦卑……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是我会去考虑东北人的角度,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还是一个卑贱的人,是一个恶人还是义人,这都是很难定义的,不要给他分序列。比如说,其实很多工人很有那种威严正义的感觉,但我们一直以来对工人劳动者形象固化了,已经丧失去写这个人的动力了,其实他们有一种庄严。
搜狐文化:我之前看评论,很多人在谈到你的小说时,会说你喜欢写“奇人”,有点剑走偏锋的感觉,你怎么看这种说法,这种选择是否也代表了你在人身上比较在乎的一些东西?
双雪涛:要是仔细观察,你能够找出一个正常人吗?我觉得很难。什么叫正常,什么叫普通?你只要细致去揣摩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每个人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我觉得小说千万要去重视个体,不要努力去归纳和理论化。我觉得什么典型人物就是扯淡,他是不是典型,能不能代表别人,这是另一码事,这是另一种世界观,我的世界观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就有意义,值得一写。
搜狐文化:所以我觉得写小说其实也是在打破语言的惯性,就是标签把人归类为群体,但是小说要把人重新找出来。
双雪涛:对,我们经常说一些有代表的人象征着什么,这本身有点问题,这是不是文学的其中之意?文学是一个特别私人的东西。我觉得个体比集体高一些,就文学关注的视点来说高一些,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更有整体意识,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可能他会觉得我想的不对。

语言的微调会保持作家的兴奋度
搜狐文化:你写《翅鬼》等小说的时候,和写《平原上的摩西》以及《聋哑时代》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小说家可能他会形成他自己的一种语气,你认为语言应该去匹配故事吗?或者说,你那时候还没有找到一种自己的语气?
双雪涛:《翅鬼》我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就是当时我认为最舒服的语言,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简洁的语言,也不是特别华丽,虽然写的题材比较特殊一点,但它其实奠定了我对语言的想法。
然后在写《聋哑时代》的时候,里头长句子比较多,一种内心的自省比较多。这就说明那时候我是有很多想要倾诉、想要表达的,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看法。到了《平原上的摩西》,就一点点开始比较有语言的轮廓了,这个轮廓大概就是一种我自己用的比较舒服的书面语,它杂糅了一些我以前阅读的经验,整体的感觉还是偏硬一点,比较偏中文,不是翻译体的那种,我会把一些口语的东西书面化表达一下。我下一本小说集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语言的稳定性在增加,自己的腔调也在增加。
另一方面,比如《平原上的摩西》和《聋哑时代》与东北有关,它匹配的语言就是这样的语言,我未来可能也会用一种新的语言去写一个我没有写过的题材,但是语言的根和基础是不会变了,它只能在上边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比如说,我写的东西是更书面化的,更文字游戏的,更拼贴式的,更知识分子类的,所以会减少口语,减少对话和动作的推进,整体语言的节奏和根基我觉得很难会因为一个小说的变化整体地去变动,因为你的骨头已经长在那,上面摆出的姿势可能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如果语言有微调的话,我觉得会保持作家的兴奋度,这个是挺重要的。
搜狐文化:最开始会模仿别的作家的语气吗?或者说无意识地会跟随一些人?
双雪涛:我开始写的时候,喜欢余华的范儿,但是余华根本上是一个翻译体,而且他是一个南方人,他语言的节奏是那个劲儿,我用起来蹩脚,当时写的小说没有发表过,就是自己写着玩的,感觉感觉,但是不是那个味。然后阿城、张爱玲这些,在语言上非常有特点的、非常有造诣的作家,是我反复看的,因为语言是指导着你去干这个活的基础材料。再后来一段时间特别迷村上春树,也写了一两个好像村上的作品,但是也别扭,村上吸收了很多西方的翻译品,他的腔调太轻了,而且非常的都市化,跟我这个东西的硬度还是不一样。我写了一两个不行,不得劲,所以自己的路得自己走。
文学达尔文主义会把作家逼疯
搜狐文化:写作的时候害怕什么?
双雪涛:我的思维里会比较追求效率和实际,会想我能不能写得更好,能不能超越现在的,有时候会有这种焦虑,这种焦虑是必要的,是激励你不停在前进。但另一方面我有一种杂耍艺人的心态,就是演砸又如何,自己开心也很不错。这两者还有点矛盾,很难讲哪个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搜狐文化:文学的进步性成立吗?写了这么多,你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
双雪涛:我觉得这种文学达尔文主义挺吓人的,很多作家都是被这个东西给逼疯的。我觉得一个作家经常会去考虑我是为别人工作还是为自己工作,这是个要点,就是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是你看起来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两个事不一样。对我来说,一方面我希望我的作品写出来之后会让别人或者舆论觉得好,比原来还要好,因为一个人不虚伪的话,他一定会有这样的希望,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真诚很重要。就比如《聋哑时代》和《平原上的摩西》,都是用真诚去写的,包括我新写的《北方化为乌有》也是,我的能力就在这里。我能吃俩馒头,不是说非得装作要吃10个馒头撑死自己。所以说我现在吃俩馒头,我就把这俩馒头吃好,然后真诚的把吃的过程写出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搜狐文化:你和自己写出来的小说的关系是什么?
双雪涛:我觉得我在创造这些小说,这些小说也在创造过我,就是这么个不停交互的过程。我觉得写小说会让我变得更好一点,作为一个人来说更好一点。如果我能更好一点,没准还能写出更好的小说,就是这么一个不停推动的过程。现在看来写作是我人生的引擎,它推动我去学习,去探索。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我在28岁从来没写过东西。
搜狐文化:从来没想过?
双雪涛:从来没想过,之前就在银行上班,干了五年。我有很多的作家朋友都是在14、15岁就想当作家,这个真是有志青年。我这种就属于阴差阳错被弄到这条路上,如果没有台湾的那个比赛我也不会去写小说,而且那个比赛是很偶然看到的,所以我是个幸运儿。干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我想象不了没有这个该怎么办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