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杰出访问学者、印度作家高希:
小说家可以对历史想象产生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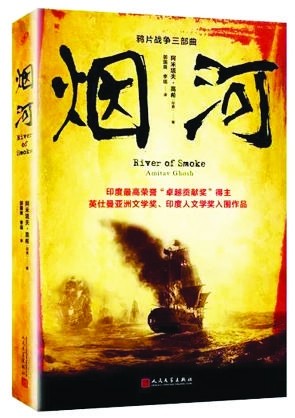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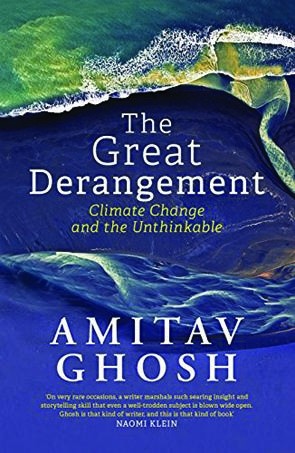
印度作家高希和他关于气候变化的新作《精神大错乱》


19世纪初的十三行
一个古吉拉特来的穷小子,作为入赘女婿攀上富亲戚,却在那里处处低人一等,于是独自扬帆来中国做鸦片生意,想要闯出一片天地。他知道“鸦片这东西,一般吸上就再也停不下”,他知道“幸运的是,这生意现在孟买这里还没让英国人垄断”,更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由我们掌控”,担心“不抓住眼前的机会,就跟不上这世界”,于是成为广泛种植罂粟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和大量进口鸦片的中国之间,又一个鸦片商。
帕西商人巴拉姆这么有危机感,是因为亲眼见到岳父曾经叱咤的领域正是这么被一步步消灭的:
英国人如果发现孟买造的船比他们自己造的更好、更便宜后的反应是:只要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大谈贸易自由化——但他们同时却想尽办法迫使东印度公司和皇家海军无法从我们这儿购订船只。接着,他们又制定了一些新法,让那些海外贸易中使用的印度造船只比其他地方的都要昂贵。……其他所有的买卖和手艺也都会是一样的。
巴拉姆并非不知道鸦片害人,但这种负疚感没有给这位生意人造成什么负担。一次航行恰好经过圣赫勒拿岛,巴拉姆于是觐见了囚禁岛上的拿破仑。拿破仑问他,觉得卖鸦片是恶的吗?巴拉姆一时语塞,不知所措。不过他马上开动脑筋,给出了一个印度式的回答:
鸦片就像风和潮汐,我没有力量左右它的行进方向。乘着这阵风开船的人,不能够简单地说它是善还是恶。要看他如何处理周围的事情——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下人——才能正确地评判他。这是我的信条。
这位用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却仍然被命运左右的巴拉姆,就是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朱鹭号三部曲”第二部《烟河》的一位主角。在小说末尾,林则徐禁烟,巴拉姆悉数上缴了自己用全部身家囤积的鸦片货物之后,他看着在广州十三行的广场上玩曲棍球的侄子,这位初来乍到、一无所知、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内心不禁升起强烈的妒忌感”,他问身边的亚美尼亚伙伴:
当他们创造未来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扎迪大哥?你觉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在这儿赚到的钱、我们得到的教训、我们亲眼目睹的一切吗?他们还会记得他们的未来的代价是靠牺牲百万中国人性命吗?
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扎迪大哥?难道只是为了这个:让这些家伙可以讲英语、戴着他们的帽子、穿着他们的裤子、玩曲棍球?
在高希描绘的19世纪混乱有生气、跨越大洋的贸易世界里,更大的推动力来自更无情、并且装备了一套人生哲学的商人。他们觉得要怪就怪人性,对人性的利用是无可指责的。书中有位英国商人伯纳姆,曾冷冰冰地表示对命丧鸦片的大烟鬼没有丝毫良心不安,“因为那些自己沉迷鸦片的人,并不是我亲手将他们处死。而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无所不能的力量:是自由、市场、自由精神,正是我们神的旨意。”执行神的旨意,让这种货品源源流入、随处可得,让白银外流,眼看着一个国家被吞噬。在给自己赦免道德罪恶之外,还有人连非法走私的罪都给自己免去了——十三行的首领、苏格兰人渣甸(创办渣甸洋行,后改名怡和洋行)这样慷慨陈词:“我们不是走私犯,各位!是清朝政府,是清朝的官员在走私、纵容默许,甚至鼓励走私,而不是我们;看看东印度公司:是啊,所有走私犯科以及走私犯的生身父亲就是东印度公司!”
广州十三行里的故事早已堙没不传——这些建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完全消失,成了仅仅留在绘画和文字里的一块外贸飞地。而在印度——十三行最多数居民的来源地,也不太有人记得他们曾被宗主国英国强制大面积种植过罂粟了。
在谈到高希作品时,印度裔美籍历史学者杜赞奇说,高希重建出殖民地人们的生存境况,“他的历史想象捕捉到了来自全球的力量形塑这种境况的过程”。在三部曲中,“他向我们展示了‘发展’是如何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这一战争,必须承认,“是多个国家(尤其是印度)的不同族群参与的结果”。高希挖掘出如今不可见的共性和连接,揭示出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曾经“通过物质的和超越道德的污流”相联。这些塑造了今天人们身份与意识的历史乱流不该被忘记。与此同时,如今,“学术性的历史学已经过于窄化、专业化,无法唤起公众阅读中的历史参与感”,高希这类作家担负起了这一职责。
除了小说,高希也写作非虚构作品,以他就读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期间所作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已经成为世界不少大学的指定教学用书。
近日,高希在上海纽约大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谈论他的小说、对英语写作的看法,以及被他称为“精神大错乱”的环境问题。
19世纪的印度洋贸易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文汇报: “朱鹭号三部曲”聚焦印度与中国的鸦片贸易,杜赞奇曾说您为此做的调查研究比很多学者都多,可以请您详细谈谈为这部书做的准备吗?
高希:三部曲描绘的是19世纪的印度洋贸易世界,以及其中人们的活动。开头部分讲的是印度人如何在毛里求斯、南非、斐济等地方生活和工作。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是位印度女性,她失去了她的土地和丈夫,后来奔赴毛里求斯。19世纪有很多印度人离开印度,在别的地方扎根定居。
我开始写的时候发现,19世纪印度洋最重要的贸易品之一是鸦片。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印度发往中国的。然后我就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了——也许是因为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我开始对鸦片在哪里种植、由谁种植、在这些种植者身上发生了什么,大感兴趣。这之后就引发出整个鸦片战争的叙事,而鸦片战争是亚洲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件。
为了写作,我在毛里求斯的档案馆里待过一段时间,阅读在那里能找到的所有材料。我也去了广州,走访那里的博物馆以及和鸦片战争相关的遗迹;还有英国、美国和印度的图书馆。这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过程。
文汇报: 三部曲里的人物,像帕西商人巴拉姆、没落王公尼尔、苏格兰植物学家费彻尔、在印度长大的法国植物学家之女波莱特等等,他们都有原型吗?
高希:这些人物都有原型,是可以这么说,虽然他们不是建立在任何特定的人物之上,一个人物实际上会有很多原型。有很多像费彻尔一样的植物学家,有很多像巴拉姆一样的商人……虽然这些人物都是虚构的,但这些事件都确实发生过。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就是那些居住在那个世界,做着那些事情的人……
文汇报: 那么像在《烟河》里,有关巴拉姆见到拿破仑那一段,也是如此吗?对已经消失的广东十三行做这样细致的描写,是为了强化小说的历史感吗?
高希:实际上书中与拿破仑的会面,是以我接触到的历史材料为基础的。这是一位旅行者的记录,他那时候正巧在那艘停靠圣赫勒拿的船上。这位商人的旅行日志是我在图书馆偶遇的,然后就构思出了整个故事。这位商人对拿破仑的描述,我都原原本本写在书里了:他的衣着,他说的每件事,那场对话……所有的。
关于十三行,我是在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曾经存在这么一个国际性的、四海为家者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有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欧洲人,他们都深层互动,交换着思想、商品,交换所有东西。这些都曾真实发生在广州的这片贸易飞地上。于是我越来越着迷,我想知道,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是什么感觉,参与到其中是什么感觉。
这片飞地后来什么都没剩下,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叙述了解它。不过幸运的是,关于它有很多绘画作品、很多文字叙述,这让我在尝试建造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时劲道十足。
文汇报: 如您所说,写作过程中用到很多历史文献和报告,那么如何在历史和想象之间做到平衡呢?
高希:文献、历史、研究,这些都只是背景。而在一部历史小说中,真正重要的部分和其他任何小说中一样,也就是人,是故事。
作为一个作家,你永远不能忘记,在读你小说的那个人不是因为想要读历史,他们是为了人物和故事而读它。所以你总得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
在三部曲里,做到这一点甚至要比写其他历史阶段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实际上只有非常少的人才知道这么一段历史。
印度和中国都饱受鸦片贸易之苦
文汇报: 您也写论文,小说和论文写作有何不同?小说最难写的是哪部分?
高希:和写论文区别非常大,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写小说有很多难处。对我来说,最难的部分是开头。开头最花时间了。我会重写,再重写。因为一开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故事会不会顺利进展下去,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而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开头,就会陷入停滞。最糟糕的是你往后写啊写,然后总是会被迫返回来,修订开头,这里修修那里修修。我不觉得说会有某个特定的时刻,你觉得“喔,肯定会成功”。写小说就像一头扎进黑暗里,你只能屏住呼吸,纵身一跃。
文汇报: 您说到在印度,鸦片贸易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
高希:鸦片贸易对印度、对中国在那么多方面都是一场灾难。而对英国、美国,却是收益颇丰。利益都被英美拿去,而印度和中国饱受其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这场战争在中国被人们牢记,在印度差不多是被完全遗忘。不过现在情况有所改变:我的小说出版后,人们现在对鸦片战争有了新的关注。我想我的作品确实在这方面起到了作用。
文汇报: 在鸦片种植和贸易方面,您认为当时的印度人应该致力于理解他们的行为对中国的影响吗?还是说,大部分历史当事人很可能只有在事后才会明白?
高希:不只是印度人参与了鸦片贸易。毕竟整个贸易体系是英国建立的,美国人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很多中国人也参与其中。很多后来扎根香港的商人就是从鸦片贸易中发家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反思这段历史。
历史和历史小说一直是相互绑定、齐头并进的
文汇报: 您曾经提到,去念人类学的博士完全是偶然。那您在念书的时候最喜欢的课程和领域是什么?学术训练对您的小说写作是否有帮助?
高希:实际上我在埃及的田野调查是很有趣的,但写论文就没那么有趣了。数据收集还是很有收获的,但写论文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我大学的专业是历史,觉得历史很有趣,也学了人类学。这些对我的写作有帮助吗?当然,不过我也做了很多其他事情。我当过记者,我做过人类学研究。但我想对我现在的写作帮助最大的是我当记者的经历,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从很基础部分做起的。那时候很年轻,19、20岁的样子。我们什么都学,包括怎么排字,怎么校对。然后我开始像你们一样做采访报道了。对我来说,新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
文汇报: 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
高希:我从小男孩的时候就喜欢读小说了。如果你喜欢读,总有一天你会想要写。我就是这样。我写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路写过来,然后有一天,大概是25岁的时候,我坐下来开始写我的第一本小说。
文汇报: 您在致谢中也提到了一些中国学者。鸦片战争史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研究领域,您可知晓一些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
高希:不幸的是我不会中文,所以很显然我在学术上的知识是受限的。当然我已经试着去读所有已经翻译过来的研究成果了。我在致谢中提到了很多中国学者,其中一位在鸦片战争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中国学者就生活在印度。我在做学生的时候认识了这位老师,谭中。他写的那部关于鸦片战争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
文汇报: 杜赞奇说学术性的历史学已经过于窄化、专业化,不再能扮演唤起人们道德、人道主义感的角色,不再能给人以历史的参与感,因此需要您这样的作家所作的历史叙述。您的作品和学院派的历史学是怎样一种关系?
高希:我觉得历史和历史小说一直是相互绑定、齐头并进的。两者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关系。对学生来说,历史小说引人入胜,会给他们建立一种对过去的感觉。
对于一段多语的历史经验,无论用什么语言来写都会有限制
文汇报: 很多后殖民国家的作家在写作英语小说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很多人都是“无疆界作家”:写作题材广泛,在多元文化中生活,有多样的经历。但有时候他们对用英语写作也有矛盾的态度。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他曾经说英语不是一门非洲语言,是精英的、而非本土的母语语言,因此自觉放弃了用英语写作。您对这一作家群体怎么看?
高希:有趣的是,瓦·提昂戈后来还是回到了用英语写作。英语当然是一门欧洲语言,但我觉得写作非洲或印度的时候用英语,在有坏处的同时也有很多好处。这会让你对正在处理的问题感觉更加敏锐,让你在很多方面不得不面对语言的问题。
比如说“朱鹭号三部曲”里,这三本书都不是只关于印度,或只关于中国,只关于毛里求斯的。而是关于那个跨国的世界,一个曾经存在、对中国和印度都有深远影响的世界。那么该用什么语言来写它呢?可以用许许多多语言来写。
不过,无论用什么语言来写,都是会有限制的。我书写的主题实际上没法用一种自然语言写成,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就是多语的。整个经验就是多语言的,不可能只从一种单一的语言的角度来写。这和单单只写中国的一个村庄,或者肯尼亚的、印度的一个村庄还是不一样的。在那里你可能只需要处理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即便你只写一座印度城市,这座城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种语言。因此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正如瓦·提昂戈他自己发现的一样,你不能说这是肯尼亚所以我就用那一种语言写作。世界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
文汇报: 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只有当一部小说是用英语写或译成了英语,它才算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否则人们不会看到它。
高希:确实,如果一部小说翻译成英语就会让书的流通发生巨大改变,让世界有机会来了解你这本书。但有趣的是,一旦被翻译,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我前两天站在成都一家书店的书架前,很有意思,那里有一个印度作家的专架。那里有我本来用英语写作的小说,也有从其他语言翻译到英语的书。它们都在一个书架上。而一旦有了翻译以后,就没有很大区别了。
当然我们总是喜欢说翻译中丢失的部分,但也该多谈谈从中获益的部分。有时候如果一个翻译版本好的话,可会大不一样。我自己也做大量的翻译。很挑战,也很有趣。
文汇报: 您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翁达杰,在《安尼尔的鬼魂》里塑造了一位斯里兰卡碑铭学家帕里帕纳,这位广受尊敬的学者在研究后期越来越把多年的翻译与田野经验同想象混在一起,沉醉于他构建出来的世界。看起来似乎是转向了“诗性真实”,而非“历史真实”。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多多少少让我们联想到您的写作经历,其中是否有相似的地方呢?
高希:我觉得翁达杰在《安尼尔的鬼魂》里是想要看历史真实与历史想象能够有怎样的重合,有时候是有可怕危险的重合。
不过,如果想想写作了《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他创造了他自己的对俄国历史的叙述,而他的叙述变得异常具有影响力,即便对历史学家都是这样。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小说都左右了俄国历史的写作倾向。所以,像托尔斯泰这样的小说家,是可以对历史想象产生深远影响的。
英国人想要自由贸易,希望整个世界都转而信仰消费主义
文汇报: 可否谈谈您最近的写作计划?
高希:我刚完成了一部关于气候变化与文学的书,《精神大错乱》(The Great Derangement)。我想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一直探索这个主题。
文汇报: 您能解释一下写环境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用“精神大错乱”这个词吗?
高希: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气候变化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海平面的上升,这已经导致沿海越来越频发的洪水。这些洪水已经开始影响到许多地方,包括许多大城市,如美国的迈阿密、印度的孟买。而如果你去这些城市,你会发现最高大、最昂贵、最新的建筑,实际上比其他楼都更靠近海。人们明明知道这些建筑在未来数十年会被洪水侵扰,还是花了大把的钱搬进去。或许因为这是身份地位或者其他什么的象征吧。反正人们就是把自己放进了一个注定会被伤害,甚至把自己弄死的境地。这不叫精神错乱,又叫什么呢?
当然这是打个比方。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我们周围的环境越危险,我们对此就显得越视而不见、越健忘。
文汇报: 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议题的?
高希:我是在写作《饿潮》(The Hungry Tide)的时候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这本书是关于印度的红树林的,有一种海豚会生活在这种红树林的水域里。我16岁就开始写这本书,在“朱鹭号三部曲”之前。
写《饿潮》的时候,我看到周围所有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大片陆地正被淹没至水下,海平面上升已经发生,人们正失去他们的土地,因为盐正一步步深入侵蚀碱化土壤。一场大灾难已经发生。而从某种意义上,这都可以回溯到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
英国人想要的是自由贸易,他们希望整个世界都转而信仰某种资本主义式的消费主义。现在全世界都转向了这种消费主义。我们也看到结果了。有趣的是,19世纪早期的很多中国思想家早就看清楚了,鸦片正是在这个方面煽风点火。而到了20世纪晚期,这场使人“改宗”消费主义的运动已经取得了成功。
文汇报: 也就是说“精神大错乱”持续了200年?
高希:气候变化真的是一件大事,而它包含许多部分。让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气候变化呈现的方式——不是一种经济危机,或是一个历史危机,而是想象力的危机。
我给你举个例子,新书发布的时候我正好在德里。德里那时候正经历49摄氏度的高温,历史最高纪录。我见到了一群像你们一样年轻的记者。我问他们:你们中可有谁写过关于热浪的文章吗?没有。因为,关于热浪,你能写出些什么呢?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没有一个人看到。我们没法谈论它,我们不知道可以就此讲出什么故事。你怎么来给一个关于热浪的故事起头呢?即便它会杀死你爱的人,你会怎么讲述它呢?
所以,问题就在于一些东西阻挠了现代人的想象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