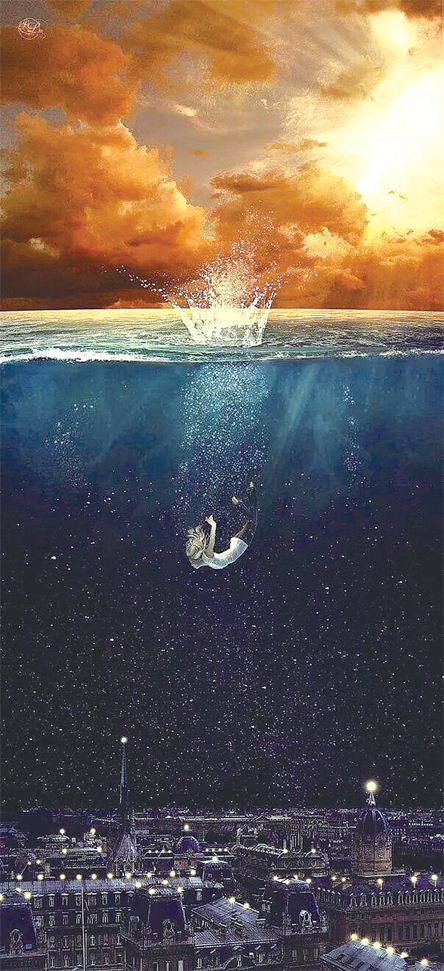
“风景”不仅是一种现代性叙事,也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重要表现,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风景”可以说是最适合表现中华美学精神的话语载体。风景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风景一直都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客体,文学中的风景话语作为文化想象的方式,不仅是景观的再现,也是思想意识的媒介或载体。在“十七年”文学中,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作家在自然风景中寄托了宏大理想,把中国传统的托物言志的方法论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风景并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华传统风景美学日渐受到重视,陈村认为风景描写是判别一个小说家真伪的重要标志,他把风景描写看作是小说家必备的素质。曹文轩在《小说门》中大力倡导风景美学,认为小说家与自然风景血肉相联,强调《红楼梦》为风景描写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经验,他把文学中“风景之发现”追溯到中国古代小说,着重突出了“风景”在小说叙事中的重要作用。曹文轩从《红楼梦》中寻找“风景之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阿来、周涛、马丽华等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众多各具特色的风景,风景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着中华风景美学的发展与转型。在《红高粱家族》的开篇和结尾,莫言描绘了壮丽的高粱风景,表现了浓厚的神秘特征,他强调这种风景是“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莫言使高粱风景成为主体精神和历史精神的象征,提高了高粱在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境界和象征意蕴。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等小说中,张承志描绘了内蒙草原一年四季的风景变迁,草原风景在小说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张承志强调草原是“母亲”的代名词。在《北方的河》中,张承志描绘了神秘辽阔的北方地域,勾画了雄伟壮丽的大河风景,他强调黄河是“父亲”的代名词。张承志把自然风景看作是母亲和父亲,看作是生命和文明的起源,风景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主体精神的象征;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步阶段,伤痕与反思文学成为文坛主流,而张承志以独特的草原风景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美学风貌;张承志对自然风景的重视与描绘,体现了风景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期作家的风景话语大都以乡村、城市、高原、草原、沙漠、森林等为主要对象。作为感官的对象,新时期作家的风景话语展开了颇具诱惑力的空间,呈现视觉体验和想象力的乐趣。作为审美的对象,新时期作家的风景话语往往以“奇异的风光”给新时期文学带来独特的地方风情,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美学风貌;作为文化的对象,新时期作家的风景话语大都以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丰富了风景的内涵与价值;作为精神的对象,新时期作家大都以独特的“野性的思维”展现对世界的想象与追求。新时期作家的风景话语不仅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的生活方式和状态,也体现了当代世界的存在方式和状态。汪曾祺、张炜、扎西达娃、吉狄马加、陈村、叶广芩、席慕容、刘亮程、谢宗玉等作家描绘了各具特色的风景,展示了牧歌风景、荒原风景、神圣的风景、权力性风景、史诗性风景和哲理性风景等风景话语的丰富内涵与意义。扎西达娃在《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中把记忆中的帕布乃冈山区比喻为“优美的田园风景画”,“优美的田园”是扎西达娃风景描绘和美学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他田园牧歌体写作的典型表现。张承志、席慕容、扎西达娃、吉狄马加的精细描绘和牧歌的勃勃生机源自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愉悦,为深受自然变化之影响的北方草原和西南高原的一切而感到愉悦。他们作品中的牧歌图景不只是静态、装饰性的背景,而应该是蕴含了理想与希望的人类生活方式。田园牧歌的风景美学是中国传统乡村主义世界观的重要表现,经由《诗经》到陶渊明再到王维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影响深远,陶渊明和王维的作品提升了中国传统乡村生活的审美经验。然而,中国传统乡村主义世界观在五四时期遭遇了巨大挑战,启蒙知识分子的精英叙事颠覆了传统乡村叙事的审美原则,田园风景美学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发生了严重分裂,汪曾祺、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体现了田园风景美学的复兴,而张承志和席慕容的北方高原风景与扎西达娃和吉狄马加的西南高原风景应该是对水乡风景和平原风景的恰到时机的补充。高原风景画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在张承志、席慕容、扎西达娃和吉狄马加等作家的作品中,草原与群山是高原风景画的典型标志,优美与神秘是高原风景画的重要特征。新时期文学中的田园牧歌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牧人唱的歌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悠远闲适的生活),新时期作家主要以“古老的民歌”、“童话的幻境”和“慈悲的牧场”三种形式实现了对牧歌体风景的描绘。在新时期文学中,荒原风景与牧歌风景对立并行,陈村、鬼子、王华等作家分别以“无垠的荒莽”“穷苦的绝境”和“虚幻的城市”构筑了一幅总体性的荒原图景,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生存智慧的探索以及对现实生存环境的思考。新时期作家以多种形式描绘了“神圣的风景”,他们主要以“永生的苍天”、“神圣的天堂”、“神圣的香巴拉”等图景表达了对生命精神的思索和对超越精神的追求以及对大自然的崇拜。风景权力化是20世纪末期风景研究转向的重要标志,人类的苦难与死亡一直隐藏在神圣风景的佛光之中,也一直隐藏在田园牧歌的表面之下,风景必然成为人类社会的象征元素,因此,风景也包含了权力的象征内涵。新时期作家也描绘了“权力性风景”,尤其是路遥、贾平凹、韩少功、扎西达娃、阿来、吉狄马加、叶广芩、张浩文、刘亮程、谢宗玉等作家通过描绘土地、村庄和住宅等风景,表现了风景的权力内涵和社会意义。史诗性风景是对历史、神话和英雄的回溯性想象与描绘,包括“温暖的记忆”“历史的烟云”和“创世纪诗篇”等图景,表达了对文化的礼赞、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对神话的信仰。哲理性风景是对人生奥秘、宇宙真理和历史规律的形而上思索与想象,包括“生命的碎片”“迷途的诗册”和“如歌的行板”等图景,表达对人生真谛、宇宙真理和历史本质的哲理性探索。风景不仅是作品的呈现,也是人类情感的依存,风景话语的不同类型代表了对生活和世界的不同想象与追求。新时期作家的风景话语具有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它体现了对人类家园世界思考的全面展开,启发了新时期文学对人类生存空间的表现。
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意识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风景叙事往往“没有特别明确的风景意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中国风景审美意识的起源上溯到《诗经》,尤其是《诗经》中的比兴手法是托物言志的基础,也是风景书写的方法论基础。在中华传统风景美学中,风景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是人类主体精神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中华传统风景美学的哲学基础。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风景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认识性装置,风景是作家情感与思想的投射;风景成为主观性话语,具有独立的审美意蕴和象征内涵;个体性、主观性和象征性是新时期文学的风景美学的共同特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时期文学创作可以在普遍性、客观性和辩证性等方面充分借鉴中国传统风景美学,充分理解中国传统风景美学的自然观念和宇宙意识,进一步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统一关系。风景是一个历史性概念,风景概念从艺术类型到存在方式再到空间形式的演变,从客观思路到主观思路的探索,都体现了人类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的不断发展。在当代社会,由于现代化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突,中华传统风景美学也将有助于对宇宙自然的理解以及对人类文化的多维思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