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潮流之外
http://www.newdu.com 2025/12/21 11:12:18 北京青年报 尚晓岚 参加讨论
 《独药师》中人物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倔强的性格有关。我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张炜
《独药师》中人物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倔强的性格有关。我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张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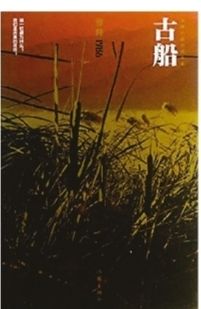 怎么过生活?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绝不是!你错就错在把它当成了一个人的事情。那些吃亏的人,都是因为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力气让你自己一个人过好生活,那样周围的人就会夺走你一个人的好生活。 ——张炜《古船》
怎么过生活?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绝不是!你错就错在把它当成了一个人的事情。那些吃亏的人,都是因为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力气让你自己一个人过好生活,那样周围的人就会夺走你一个人的好生活。 ——张炜《古船》
一个敏感的作家,会在时代潮流之外,发出预警。只是这个闪动的信号,人们往往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察觉。 数字的重量 据说,张炜有一个独特的写作习惯。重要的文稿,手写;不重要的文稿,电脑敲字。手写文稿中,用笔又有一个由重而轻的排序,依次是钢笔、签字笔、圆珠笔。那么,他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长篇《独药师》,在这个秩序鲜明的队列里站在什么位置呢? “写《独药师》,当然是用最好的稿纸,最好的钢笔。”张炜说,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那是6月15日,头一天他来到北京,晚上休息得不太好。15日一早,他去电台做节目,之后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专访,下午参加《独药师》的发布会,16日又是一连串的座谈。如此密集地参加新长篇的推介活动,对他而言是第一次。 迄今为止,张炜已经写了43年,1700多万字。每部长篇,都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搭建出来的。《独药师》的构思,18年前就已诞生。“一直不能写,是因为《你在高原》太长了,不把它脱手,就不能做别的。脱手后也不能马上写,得养足中气。这期间我写了点儿童作品,讲课产生了两本书,真正抡圆了写一个长篇,七年里第一次,就是《独药师》。”张炜说。 《你在高原》,10卷450万字,1988年动笔,2009年脱稿。虽然每卷可以独立成篇,虽然有评论界的推崇并加冕茅盾文学奖,但它的体量,还是吓退了许多读者。那么26万多字的《独药师》,据说是张炜“最好读”的一部小说,是不是包含着策略上的考量呢? 张炜岿然不动。“我觉得我的书都特别好读。我不太为没有文学阅读能力的读者写作,那不是我的考虑。我需要读者能进入语言的最小单位。”他说《独药师》要写一个好看的故事,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像音乐家一样找到自己小说的调性。追求高格调高难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没有难度的写作一般不会是很棒的作品。” 《独药师》写了两年,完成后又放了三年,张炜请一些“信得过的人”提意见。“强大的自信和接受挑剔相一致,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拥有的两种能力。”他反复打磨,把小说压掉了近10万字。“《独药师》的美学品格不同于《你在高原》的宽阔气象,它追求内敛和精炼,情节紧凑是由写法决定的,而不是出于妥协。” 时间在写作中流逝,数字包含着重量。张炜的语调轻松而沉稳,传达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自信。 恪守的界限 《独药师》面世后,很多媒体把注意力放在了“养生”上,这是纯文学很少碰触的一个题材,张炜说,碰它是“玩火”,写不好就是“自毁”。 张炜是龙口人,这座城市位于胶东半岛,临渤海,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蓬莱、龙口、莱州一带自古为方士聚集之地,有一种说法,那位骗了秦始皇的著名方士徐福,就是龙口人。渊源有自,养生和对长生术的追求是当地民间文化中的一股潜流。“民国以前,每个城镇村庄都有热衷于长生的人,各种流派,各种方法。”张炜没有见过这些“现代方士”,他查阅档案典籍,听老人讲故事,从中提取了一些“养生要义”,化入《独药师》的情节。不过他对这部分内容格外警惕,因为他觉得“狭义的文学”(纯文学)和“广义的文学”(通俗文学)必须界限分明。“写养生,写东方文化的神秘主义,对我来说非常冒险。必须动用我的文学历练和文学经验,包括个人的文学格调,得沉一下才敢碰,要不就写俗了。现在你会看到,它对小说诗性的核心没有伤害,严格恪守了狭义文学的美学原则。” 采访中张炜时常谈到这条文学的界限,多少让记者感到惊讶,似乎很少有作家固执于此了。“广义的文学也不是不好,但我的写作是离它越远越好。我怀疑有什么中间地带的文学。狭义的文学不能去接近广义的文学,否则必然引起品格的、各个方面的衰变。”张炜进一步说,“现在文学的问题在于,什么都要,而且用了一个很好的词来形容自己——雅俗共赏,哪有那么多好事?雅的东西赢得读者,要经历时间的缓慢教导和学院派的不断诠释。像《红楼梦》和鲁迅的作品,经典化以后,吸引很多人去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阅读门槛降低了。要读懂鲁迅等等还是困难的。雅俗共赏不能以发行量来证明,它常常是不存在的。” 文学的雅和俗,这个古老的话题似乎不合时宜。但是联想到张炜数十年来的写作,还有他在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发表的《抵抗的习惯》等一系列文章,就会隐约地明白,他要坚持的,他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 深刻的谨慎 《独药师》讲述了一个养生世家的故事,属于张炜惯写的家族小说,他认为传统文化的根基保留在大家族里。但它并不是一本“养生书”,因为与个体生命存续并置的,是革命的暴力和死亡;与养生世家的秘方丹药同在的,是教会医院的手术和药片;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共存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小说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清革命为背景,作为附录的“管家手记”一节,详述了革命的进程,铺陈着历史的底色,张炜说,“这部手记好比一片海洋,前边的故事只是一艘轮船。”主人公季昨非的爱欲磨砺、养生修炼、家族危难,搭载着故事之船,漂浮在变革时代的滔滔巨浪中。 山东半岛曾是革命党人与清廷激战之地。同盟会的北方支部设在烟台,主要活动地点就在龙口。张炜对故乡的历史显然非常熟悉。龙口旧称黄县,《独药师》中的季府养子、革命党人徐竟,原型是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徐镜心(很巧,徐氏真的写过一本《养生指要》),改良主义者王保鹤,原型是辛亥革命烈士王叔鹤,他们是张炜不折不扣的同乡。麒麟医院,原型是1902年创建于黄县的怀麟医院,中国最早的西方教会医院,医院中的角色也多有所本。季氏家族,则部分取材于南洋巨商、在烟台创立张裕葡萄酒业的张弼士,并融合了其他胶东富商的事迹。张炜说:“小说里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名字带着原来的音或字。原型就像个拴马桩,拴住我的心猿意马。” 20世纪革命的巨浪已然退潮,现在流行的,是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的推崇,对个体欲望的张扬,80年代以来的很多名作家,通过小说特别是家族小说建立起一套解构革命的历史叙述。张炜在这个潮流里吗?《独药师》令人印象深刻的,恰恰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在人物的描绘中,不易得出作者的“历史判断”。 “作者想要得出一个结论是很困难的,不是为了稳妥才回避判断。小说把最基本的客观性罗列出来,当然这种罗列作者不可能是毫无倾向、毫无察觉、茫然的、自然主义的,但是要极其小心地避免武断,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张炜说得不疾不徐,“比如改良和革命,到现在还在争论,二者都有其必要性,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取舍和运用,差异就太大了,广大人民所遭受的,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涉及到人类历史中过于复杂的一些问题,总是碰到悖论。所以作者和读者一样,在客观的现实存在面前,不要太武断。不是不敢,而是不能。这种谨慎是一种深刻,而非仅仅为了谨慎。” 那么,小说命名为“独药师”有何含义?张炜以书中人物为例做了阐释。“由于信仰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药师,觉得那一味‘独药’能够拯救社会和人生。陶文贝觉得独药师是基督,朱兰认为是佛陀,邱琪芝觉得是自己的长生秘术,季昨非认为是家族的养生传统,革命者徐竟说,唯一的药是革命,唯一的独药师是孙中山,改良者王保鹤不否认革命,但觉得教育和改良民众素质才是唯一的药方……直到今天,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独药和独药师,都在宣扬自己信奉的东西,它们各有其体系、著作、鼻祖、代表人物。我们经历的已经够多了,数字时代面对大量信息尤其不能武断,简单化会犯错误——不是犯世俗性的错误,而是犯了在真理面前的彻底性的错误。作者如果偏向哪一边,就是无知和偏颇。这一大堆问题我们用了几千年都没解决,一本书怎么能解决呢?这部小说如果能引起大家正视和思考这些问题,不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吗?” 的确,不要武断。然而面对诸多“独药”,我们终将做出选择。诸多不同的选择,又被“时”与“势”筛选,汇聚为历史的潮流。那些未被选中的,可能被遗忘,也可能在新的潮流中浮起。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分辨,自己是主动的清醒的选择,还是潮流的跟从者乃至盲从者? 这是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对此张炜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说:“我不是一个是非不辨、模棱两可的相对主义者。” 敏锐的预警 有学者说,张炜的写作,在8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社会思潮中有异质性,可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复旦大学的倪伟老师在《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一文中,认为张炜的早期小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展示了对农村状况的复杂思考。“当几乎所有人都在为承包责任制大唱赞歌的时候,张炜却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制度变化给农村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敏锐地觉察到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利益至上的原则一跃成为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的首要原则,导致了社会道德的窳败。”或许更令人难忘的是,在张炜完成于1986年的著名长篇《古船》中,主人公隋抱朴读《共产党宣言》的情节,这个私有制的反对者,反复地说,“我准备读一辈子”,“日子每到了关节上我就不停地读它”。而且,隋抱朴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和弟弟隋见素为夺回家族的粉丝大厂据为己有而“算账”的情节,总是紧邻着出现,构成一种争夺般的紧张。时代变迁,这一切在今天回望,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不过,张炜小说的核心关切显然并不在社会和制度的层面,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对道德理想的高扬,对残暴无耻的痛恨,对自私自利个人至上的否定,对信仰和个人获得真正自由的追寻。《独药师》的道德色彩没有那么鲜明,但也内在于这个脉络。“我觉得历史社会政治等等,它在最高的层面不可以逾越道德。”张炜所说的道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坏,而是带有终极意义的普遍法则,犹如康德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然后他谈到了信仰,“曾经有记者问我,是不是把文学当成信仰。我说那可不是,文学只是一个人诗意表达的热情和方式,跟信仰差远了。信仰是宗教范畴的,它跟定宇宙间规定一切的、不可超越的唯一法则。道德律包含在这个终极法则里。” 张炜相信这个“终极真理”的客观存在。“没能认识到不等于它不存在。我思考,探索,用向往和接近它的心情去生活,有很多愤怒也有一些欢乐。但始终要明白,真理是存在的,它是复杂庞大永恒的系统。电脑世界是0和1编码的系统,那为什么不想一想,宇宙中也有一些非常严密的,错一个码全错了的力量呢?” 我们这个纷乱的时代在被什么力量编码?道德重建能成为当今的“独药”吗?自90年代以来,张炜的“道德”诉求、对工业文明的疑虑,为他赢得了坚守精神高地、富有“人文精神”之类的赞誉,但也有人质疑他作品中“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就此,张炜回答说:“现代化破坏人的生存,是最不道德的一个过程。中国是农民的国家,农民们到城里去卖命,把他们的生命能量全部耗光,贡献给那些粗鄙的财富积累者,这不是最不道德最残酷的事情吗?”他不太在意这顶“反现代”的帽子,“我不写这些还写什么,我说的还远远不够。有些人过去批评我,这几年被雾霾闹的,就不太这么批我了。” 诚如张炜所说:“文学不是大字报,不是匿名信或控诉书,它是审美的,无论什么社会问题,真正的作家还是要把它文学化。”但同时,一个敏感的作家,会在时代潮流之外,发出预警。只是这个闪动的信号,人们往往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察觉。 生命的能量 面对记者的一个个问题,张炜从容作答,语速偶尔加快,面露笑容,但疲劳之色始终挥之不去。“昨晚没休息好只是一方面。我一直疲惫。”然而,他“一直疲惫”却写了一两千万字,这必然凝聚着劳动和力量。 话题转到了《独药师》中谈到的养生法门之一——“餐饮”,它指的不是吃喝,而是“目色”,“是指人的一生一世,如何用目光看取周边世界”。张炜用猫做了个比喻。他很爱猫,一直养猫。他说,猫总是懒洋洋的,没事儿就打瞌睡,但它的爆发力特别强,超乎寻常的迅捷,这样的生命力量就来自“目色”。张炜把“疲惫”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有人从小的习惯,看一切都是很淡的目光。把精力凝聚在心里,可以投放到最愿意做的事情上。两眼炯炯有神的人,大多数是没力量的,安静、谦卑、柔软、不击打别人的人,才是有力量的。我们看待一切,都不要用那种攫取的、咄咄逼人的目光。” 这些见解,或许也是齐国方士们一代代传下的道理?张炜的家乡是齐文化故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齐国都城临淄的风俗说:“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张炜写过一本论齐文化的书,叫《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他解释说:“恣,就是放纵;累,就是为物质和享乐所累。打个比方,整天跳舞,就是恣,跳完了爬不起来,就是累。” 齐人的性格,徐缓宽松,高谈阔论,好奢侈,爱享受,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忠厚诚朴的山东人,相差何其之远?张炜说:“今天的山东,论人口和面积,还是在鲁文化、儒家文化的笼罩之下。历代统治者都是以儒家文化为治国方针,压抑个性,而齐文化是讲个人的,包括乱力乱神、养生求仙在内。《独药师》也是要把齐文化的这股潜流挖掘出来。” 记者暗自琢磨,张炜的性格,是偏向齐人的舒缓阔达,还是偏向鲁人的厚重守礼?这大概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回答了。毕竟,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作家的途径,唯有其作品。 令人难忘的,还是张炜的自信和在文学上的自我期许:“经过43年文笔的磨练,我觉得还是比过去成熟了一点,也许可以做一些大活儿、很难的活儿。我对文学的知和爱变得深了。”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重走长征路”上的年轻人
- 下一篇:海子诗歌与中国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