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异托邦·后人类:中国科幻文学的“可见”与“不可见” ——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
http://www.newdu.com 2025/12/13 06:12:2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汪晓慧 参加讨论
关键词:先锋 异托邦 后人类 《中国科幻新浪潮》 编者按 在当代海外中国科幻研究中,宋明炜教授创造性运用的“新浪潮”(New Wave),已经成为具有导引性的关键词。借助这个术语照亮“中国新科幻”的“幽暗”之处的炫目辉光,论者在这个文类的深处发现了具有“先锋”“叛逆”“颠覆”等多种属性的暗能量,进而视之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延续。汪晓慧博士的这篇书评,很好地体现了“新浪潮”这个“认识装置”的威力。比起一板一眼的历史考述,一个包罗万象而又立意鲜明的概念,显然更能为当代中国科幻文学营造富有冲击力和吸引力的整体形象,更能引起到中流击水的学术豪情。但这只是起点。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以甚至超越主流文学的精神强度介入了社会历史,那么它们,以及它们的创造者,究竟以何种方式与后革命/后冷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历史发生了怎样的血肉关联?它们繁复各异甚至判然有别的技术观、人性论和世界想象,是在寂寞中自组织,听将令而齐齐杀出的伏兵,还是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高技术社会的精神分裂症候之隐喻?这股“新浪潮”与已经理所当然地消散并被忘却的“前浪”或“旧浪”之间,或者说,“中国新科幻”与“中国旧科幻”之间,是了无牵挂,还是藕断丝连,又或是,薪尽火传?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讨论。 科幻小说的复兴是中国文学迈入新世纪后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从文学体制边缘走向关注中心的过程中,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政治寓言的潜力逐渐显露,其间庞大、复杂、相互抵牾又相互勾连的诗学问题也浮出历史地表。作为国际科幻论坛中首屈一指的批评家和中国科幻海外传播的重要推手,宋明炜对中国科幻文学中的诗学问题保持着深刻关注与敏锐洞察,近十年来陆续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见证和记录了中国科幻文学再次勃兴的历时性过程。 宋明炜新著《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以下简称为《新浪潮》)收录其中二十篇影响较大的科幻论述,以“新浪潮”为关键词,直面既往科幻研究多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相对零散而缺少整体性创新的理论难题,从历史眼光和诗学维度切入科幻研究,开拓性地梳理和发掘作为“他者”的科幻小说在文学空间、现实言说和主体意识三个维度上建立的“新坐标系”及影响。从“新浪潮”出发,无论是科幻文学的自我认知,抑或是当代主流文坛对科幻这一文类的认识,都发生了重要而意味深长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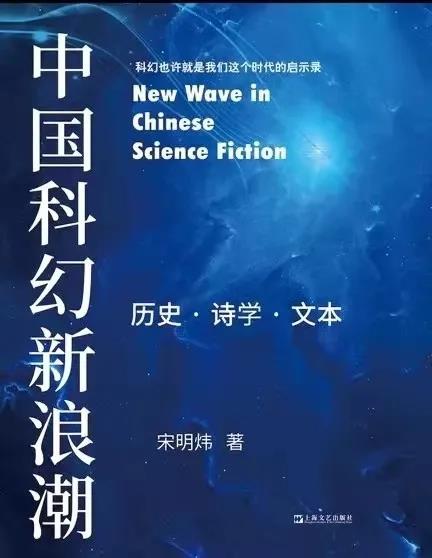 《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 一、“新浪潮”的内涵与特征 世纪末以降,社会经济与信息技术急遽发展,文化传媒方式多元分化,中国社会思潮转向的同时,主流现实主义文学却逐渐与社会现实脱节,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科幻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复兴。《三体》《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流浪地球》热映,使得中国科幻文学这支“寂寞的伏兵”1走进大众视野。不同于一些研究者将这场科幻热类比为英美科幻史上曾出现的“黄金时代”,宋明炜独辟蹊径地将科幻文学的第三次复兴形容为一场近似于超新星爆发般的“新浪潮”,着意研究当代科幻文学书写中反叛传统创作套路、标榜先锋前卫、揭露黑暗未知的叛逆一面。 2013年,宋明炜在《文学》杂志中首次提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这一说法2,以其指称科幻文学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突破。在其后的论述中,他不断夯实“新科幻”与“新浪潮”的理论细节和文本支撑,着重考察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异军突起现象中的诗学价值。宋著认为,中国科幻新浪潮萌芽于八十年代末,兴起于九十年代末,并在新世纪前十年逐渐发展成熟。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那一年,刘慈欣写下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中国2185》。尽管这部小说迄今为止并未公开发行,但它“以宏伟瑰丽的想象,将八十年代知识精英的理想,重现于‘另类历史’的构想之中”,成为新浪潮中不可忽视的起点。其后,韩松、王晋康、星河、潘海天、赵海虹、陈楸帆、夏笳等人延续扩展了这种带有严肃思考意味与先锋精神指向的精英式科幻写作,逐渐形成一股颠覆传统科幻文类成规的创作力量。尽管这些作家的创作旨趣、审美偏向、叙事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以暧昧复杂、不拘一格却都具有某种分明意指的笔触介入社会历史,呈现出与现实或对应或悖离的异托邦世界,由此构成新浪潮的核心特点和寓言维度。 借用“新浪潮”(New Wave)为论述的内在精神逻辑,难免会让研究者想起英美科幻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新浪潮”概念。但需指明的是,宋明炜所界定的“中国当代科幻新浪潮”实际上已经与“英美科幻新浪潮”产生较大区别。尽管这两者都指向某种打破传统、具有前卫色彩的人文科幻创作模式,但相较于后者以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和社会讽喻为核心的实验性叙事立场,中国科幻新浪潮则更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多元而外向的格局。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新浪潮科幻”是类型文学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试图自我突破所形成的迭代式内部革新;而在宋著所界定的中国科幻新浪潮中,类似的前卫先锋意识早已突破类型文学内部,它对话、继承、叛逆、超越的对象更多指向占据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传统及其中难以言说或被长久忽视的“异境”。 科幻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对于“现代性”的阐述。正如吴岩所说,“研究科幻文学如果不从‘现代性’着手,就不能真正接触它的内核”3。当代科幻作家继承鲁迅以来的“五四”启蒙思考和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先锋批判精神,立足于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而产生的本土化想象,自觉不自觉地在小说中融入社会问题和科学思维,借此返照社会现实,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这亦是中国当代科幻区别于西方科幻新浪潮最鲜明的特质之一。 在这股新浪潮中,刘慈欣、拉拉、宝树等作家笔下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技术颂歌倾向、宏大崇高的民族精神表达以及向史诗传统回归的新古典主义气质;韩松的写作风格具有强烈的先锋特质,文字晦涩曲折、意象破碎扭曲、人物形象混沌不清,在鬼魅混沌的隐喻中折射现实历史的种种镜像;更年轻的作家陈楸帆等人跨越西方新浪潮的写作阶段而则将关注点放在控制论、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相关话题上,创作了一系列兼具本土化想象和后人类意味的赛博朋克作品。西方科幻曾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被不同作家借鉴吸收,共时地出现在中国科幻新浪潮中,构成当代文学场域中一股多元庞杂、充满活力的潜流。 正如宋明炜强调的,当代科幻中所产生的先锋叙事和异质书写不仅是百年来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一股“新浪潮”,也“对中国文学的主流造成了冲击”,更应当被视作“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新浪潮”4。因此宋著中“新浪潮”一词或更应当取其字面引申义来理解,它指的是中国科幻文学从边缘走向主流、从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级影响。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宋明炜所建构的“中国科幻新浪潮”是一体两面的:在叙事层面,它指的是中国当代科幻在主题、内容、世界观等方面对既往文体的实验性颠覆;在思想层面,它包含从现代性、本土性和全球性角度出发的诗学探索,并最终提出关于当代科幻言说的三个核心议题。 二、“孤独者姿态”与“未完的革命” 《新浪潮》首先讨论的是新科幻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坐标”和“定位”问题。回顾中国科幻百年来的发展历程,由于政治倾向、社会思潮等诸种原因,尽管科幻文学曾数次繁荣,但其发展代际之间并无直接继承与接续关系,而是形成了如同断代史般的在精神上或有共通、但在文学书写上却各自独立的局面。当“中国科幻文学史从来都是断裂而非续接”的论段普遍流行,科幻作为“一支寂寞的伏兵”几乎成为被反复强调的确论,宋著却将当代科幻置于自“五四”至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考察:在解构科幻小说存在于文学谱系边缘的“孤独者”姿态之余,亦试图合法化重写科幻内部曾被文学霸权与政治潜意识刻意压制和遮蔽的启蒙意识和先锋精神。 尽管对于新科幻复兴的时间起点并无定论,但评论家们大多同意将其定位在1990年前后。5颇有意味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恰恰是当代主流文坛“最为沉寂”的时期之一。6“五四”以来所倡导的理性批判精神作为现代文学的核心命题被消解和搁置,宏伟的启蒙论述几乎销声匿迹。主流文学中的先锋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编,文学的地位也因此而迅速边缘化后,文学场域中“完美的真空”7却给予科幻文学萌发的机会。 启蒙主题在新世纪以科学和幻想的方式重新归来。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科幻作家群”(即“第三代”)及其后的“更新代”8直接汲取了从鲁迅到八十年代文学中的思想话语与批判姿态,以开放而新奇的姿态续接先锋精神。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指认与颠覆、对技术的重审与祛魅,那些带有严肃思考意味的科幻创作将新时期“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为特征的新愚昧,以及科学-政治拜物教带来的身心压迫”从潜流中拔擢至叙事层面,在技术背景和后现代维度中不断回应、展开和创造启蒙论述的新内涵。 吴岩认为,“从梁启超和鲁迅开始,中国的科幻文学发展出现了一个两极性的文化空间。”9在梁启超一极,未来畅想沿着科学上行而到达全新的形而上的哲理境界,譬如《新中国未来记》所描绘的诸种画面,体现了基于宏伟视野的乐观愿景;而在鲁迅一极,科幻作为一种思想和工具沿着社会等级下行,被纳入日常并渗透到生活的幽微细节之中,并以此抵达国人精神深处。显然,宋明炜将“新浪潮”的精神源头定位在鲁迅一极。他认为,新浪潮兴起,梁启超式的光荣与梦想虽然也在,但是“对于刘慈欣、韩松等作家来说,鲁迅代表了一种真正开启异世界的想象模式。”10 鲁迅及其精神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留下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和遗产,其笔下诸如“铁屋”“看客”“昏睡”以及“救火者”等一系列词汇在近百年文学书写中反复出现,其含义已经从隐喻上升到明喻层面。新生代科幻作家将鲁迅勾勒的中国视景加以延伸,以奇诡想象出入于虚拟的真实和写实的虚幻之中,探勘现实以外的幽暗渊薮。宋明炜认为韩松是对鲁迅有最自觉继承意识的科幻作家,他在小说中创造的隐喻总在有意无意回应百年前的文化命题。以韩松的《乘客与创造者》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铁屋内”的故事,并忠实地呼应着鲁迅的“呐喊”。小说中,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一架在永夜之中飞行的波音7X7,封闭空间中充斥着黑暗颓废、腐烂死亡的气息。技术抹去乘客们的记忆,飞机里的人忘记了自我身份,对于周遭一切熟视无睹,“这世界上一切都无所谓”。尽管“启蒙者”试图帮助乘客逃出牢笼,但绝大多数人依旧冷漠麻木,宁愿殉身火海。更为可怖的是,少数有清醒觉知的乘客最终跳下飞机逃生,早已在地面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群持枪士兵。 在鲁迅的铁屋叙事中,铁屋是有限的空间。惊起昏睡者,或有打破铁屋而闯出去的希望,仁人志士们坚信等候在铁屋之外的将会是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截然相反的事物。而在当代科幻叙事中,“铁屋”却失去边界感,铁屋内外空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变异的技术放大了桎梏,铁屋进化成层叠异形,主体从较小的囚笼内部逃离,却奔赴进入更广阔的铁屋,导致绝望之外还是绝望。这一切无不彰显着科幻写作者焦虑的潜话语:技术进步与精神解放之间并不直接对应。走出“铁屋”后,启蒙话语在现代科技和后人类语境中非但远未终结,反而化为深入宇宙肌理的无物之阵,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悖谬与迷茫。新浪潮科幻作家在技术文明背景下重审“五四”文学革命,这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遗民态度相较于先辈却更为矛盾,甚至充满质疑的虚无。恰如鲁迅所说,“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见中看见无所有”,新浪潮中,一面是对启蒙话语被遮蔽后导致的未完成状态的怀疑、忧虑和悲哀,另一面是对光明、希望和自我意识归复的极端渴求——这种分裂、焦虑与不确定恰恰是鲁迅留下的精神遗产,也是重审启蒙价值与现代性的第一步。 如宋著中所言,如何界定科幻与现代文学传统之间既断裂又续接的关系,是“我们如何理解科幻的想象模式为文学带来的新奇的冲击力”11的关键。质言之,在“新浪潮”的论述框架内,无论是策略性地把鲁迅提到中国科幻的时间轴上,抑或是提出“《狂人日记》是科幻小说吗?”之类的问题12,其实并非为得到某种确定答案,而是试图在习以为常的文学史论述中重新定位科幻这一被遮蔽的“孤独者”,同时彰显科幻文学对先锋精神与未完成之文学革命的续接与突破。 三、从“现实一种”到“异托邦想象” 科幻文学与现实言说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新浪潮》试图阐释的另一关键诗学论题。宋明炜认为,科幻小说看似是具有强烈未来式、距离现实最远的文类,实则却与现实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它的写作对象看似是不存在的事物,但却通过构造出迥异于日常生活且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异托邦”,揭示了表象之下更为深层的“真实”。这种“宣称说出真相的现实主义与看似与现实无关的科幻小说之间看似不可能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科幻史最曲折的言说维度,亦成为“新浪潮”的美学核心。13 在论述中,宋明炜回避了以“科幻现实主义”这样的混搭术语来简单指称科幻与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将分析重点放在“科幻小说是如何在诗学意义上建立具有真实性基础的语义、修辞和文本性”这一问题上。借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宋明炜指出了尤为重要的一点,即科幻小说文本本身作为语言空间就是一种异托邦的构造,它以极度陌生化的题材和叙事建构了超越现实的“看的恐惧”,直接指涉那些人们不敢睁眼去看的异样真实和令人恐惧的真相,从而揭示现实层面内外的复杂向度。 晚清以来,由“未来中国自立自强”这一政治愿景所驱载的乌托邦叙事和技术乐观主义一直主导着科幻写作模式。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到吴趼人《新石头记》,从庄鸣山《生活在原子时代》到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无不如是。 其间为数不多的例外或只有老舍的恶托邦寓言《猫城记》。一个世纪后,世界政治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梦”和“和平崛起”等政治构想下,当代科幻所建构的异托邦早已超越单纯的未来寓言式的乌托邦/恶托邦,它复杂而尖锐地内嵌于当下存在之中,成为现实中国的转喻场域,在逻辑上与真实世界发生既耦合又悖离的深刻联系。 一方面,科幻异托邦从不回避认知上的真实性与现实感。这种真实性未必已经在现实层面成立,但却必然或多或少建立在已有的认知逻辑、科学原则或拟科学思维之上。大量极具真实感的细节描写起到“增强现实”的效果,使得科幻小说中超越日常逻辑的镜像异世界具有强烈的说服力。无论是黄土高原上贫瘠落后的西部乡村和留守儿童生活现状(刘慈欣《乡村教师》),还是充斥着斑斓晕影和恶臭气息的东南沿海垃圾岛和宗族制下困兽般的新人类(陈楸帆《荒潮》),科幻故事中无不填充大量真实社会历史细节作为背景,一切恍如现实镜像。于此般镜像描写中,作家们将日常细节中或诡异或反常的细节提纯,准确切入现实中难以言说的幽暗一面,通过不断重组各种文化元素、科技因子和政治愿景,构造出一个个被隔离、被治疗、被规训的异托邦空间,将对现实的反思融入对异世界的总体性构想之中。 仅仅讨论异托邦是如何以虚构空间和另类视野再现已然存在的现实显然是不够的,它更作为与真实空间相对的“他者”而存在。“异托邦”的意义存在于它与现实之间曲折的转述关系,其结构性目标是通过反抗和揭示“看的恐惧”来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大众想象和现实秩序。于是乎,另一方面,异托邦又极度重视和强调创造认知上的陌生性,试图以略微超前的时空姿态反身回刺现实,完成对认知世界的重构。苏文·达恩将科幻定义为“认知上的陌生化”,其中的核心是奇观与新奇事物(novum)。科幻小说所创造的异托邦恰恰是不断被构造又不断被瓦解的奇观。 通过提供对现实有差异的另类认知和解读,异托邦将“深藏在我们时代中、不为我们在日常经验层面所感知的某种特征、某些力量释放出来”。科幻作家笔下创造的二维“异世界”与三维“现实世界”有某种互文性联系——拼凑文字碎片,便能得到通往真实世界的地图——此间种种异象充满了荒谬变形、无处不在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恍若梦魇。这一叙事特点在韩松的创作中尤为鲜明。通勤路上,拥挤地铁忽然失常,沿着铁轨永不停驻地前进,将乘客带去未知的地下世界,畸变和残食如藤蔓般缠绕着众人(《地铁》);大地震后,建筑师发明了混合着废墟和人类尸体制成的环保再生砖,以抚慰震后人们心中伤恸,再生砖中回响着的死者耳语和低泣竟意外使人沉迷,以至于人们不断寻找新的灾难(《再生砖》);平静夜晚,人们却倾城梦游,真相竟是政府为实现发展既定目标,决定放弃人民睡眠和做梦的权利,令睡梦中的人夜夜在梦游中完成额外工作任务(《我的祖国不做梦》)。在追求富强的现代化发展语境中,宏伟的“中国梦”畸变为鬼魅般的奇体中国。科幻小说打开书写中国发展现状和人们普遍心理状态的新面向,它挑战已有的“感觉结构”14,以技术化方式将细微而明确的社会事实转化为极度陌生的景象和体验,将超越性的抽象理念嵌入社会生活,对现实产生强大冲击并持续重塑感觉结构和日常认知。异托邦建构可被视作科幻言说中的重要方法,“新浪潮”由此提炼出讲述中国乃至世界“可见的正面”与“不可见的反面”的隐秘符码,并追问其作用与意义。 四、“人的存在”与后人类状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幻小说天生带有世界文学的意味。它超越了国家政治身份,在光年尺度上思考人性与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体现了“不可思议的崇高一面”。自图灵测试以后,后人类主义思潮愈发旗帜鲜明地挑战传统人本主义对人的定义。当后人类主义在谈论“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15的时候,实际上指向的是“什么是人”/“人何以为人”的本体论问题。以赛博朋克为代表的科幻文学想象中所描绘的“信息去身化”、“赛博格具象化”和“人类义体化”等现象无疑是这一思考后科技时代的新变体,诸类研究也几乎都将后人类的伦理难题等同于赛博格的困境。 然而,“科幻新浪潮”中的“后人类问题”指向一种更为复杂而广泛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结构。宋明炜并未将后人类难题局限于“自动化控制机体,机器和有机体的杂糅体,现实和虚构的混合体”16对人的存在本身的挑战,而是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延伸到科幻对于人类未来多种形态与生存境遇的凝视与想象。他敏锐地捕捉到后人类状况之下透射出的更深层问题,即同类与异类、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差异性”。自我与他者在差异之中互为观照、互相驯化,从性别、阶级、宗教、国族乃至物种等多个角度体现着“新的主体建构、政治身份和文化认同”17。由此,人类重新定义自我主体身份,改写自我建构规范。 宋明炜在论述中扩大了后人类的内涵边界。《新浪潮》中,“后人类”一词不仅包括“黑客帝国式”的人工智能和控制论中的虚拟意识与去身化主体,也包括从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到威尔斯《时间机器》中的地下人,从伊格言《噬梦人》中的生化人到刘慈欣《微纪元》中的微人,从韩松《红色海洋》中的海底人到陈楸帆《荒潮》中的赛博格。后人类以不同形象一再出现,然而不管它的分身幻象为何,都包含同一认识基础,即后人类主义是“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信念的质疑和消解”,“不确定性和无限性挑战着人文主义对于整体和谐的信念,瓦解了人文主义乐观精神下的理性主义和自我决定。”18 宋著将科幻作品对后人类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差异和未知的恐惧,另一类是对因差异而受难的他者近乎宗教感的同情,这两种态度既矛盾又融合。19前者来源于人类中心主义面临挑战时而产生的普遍危机意识。正如福山所忧虑的,受现代技术裹挟的人将逐渐沦为信息和数据符码化的后人类,人性悄然异化,“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20但这一观点依旧是建立在传统人文主义话语之上,始终未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认知盲区。而作为思想前沿的后人类形象倾向于在差异中重新结构对人和人性的定义,随之而来的第二种态度则是在理解、包容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超越性认同。它使得构筑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亦是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处理的重要命题。 在“更新代”中,陈楸帆或许是最具有全球视野和后人类书写自觉的科幻作家之一。借由跨越性别、阶层乃至物种的异视角通感与意识共情手法,陈的作品往往将悬置的人类感觉内嵌于他者的感官和生命体验之中,毫不避讳地暴露出后人类状况中的诸种伦理困境,并在极端异化和冲突中获得对世界的再理解。无论是以人造子宫体验原始的生育痛苦来跨越性别认同之差的行为艺术(《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或是在意识上切入巨型机械的网络神经而完成了从垃圾人到赛博女神的非我身份觉醒(《荒潮》),甚至是以消泯自我意识为代价融合入其他物种智慧意识的生命体验(《巴鳞》),陈楸帆笔下的故事无不证明着在对“差异”的包容和重构中蕴含着另一种平等想象个体、人类、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这恰如宋明炜在书中所写:“我们如何理解人,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非人”,“我们如何理解他者,关系着我们如何理解自己。”21也正因科幻对“差异性”葆有长久关切,使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类。 中国当代科幻正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向前行进:一面开启崭新的黄金时代,另一面又衍生出颇具颠覆性的新浪潮,两者齐头并进、双生共存。正如《三体》中地球向宇宙发出广播而显露坐标,当中国当代科幻唱响古老地球之歌时,也正以跨越光年的速度向全世界广播本土作家对宇宙存在的严肃思考。 事实上,如何定义科幻文学,如何定义“中国科幻的‘中国性’”22,这些问题迄今尚无定论。不同类型的科幻在“科学性”“未来性”“叙事性”“现实性”23四个向度中不断游移,其内部张力所带来的丰富可能性本能地拒绝任何一种欲将其符号化、秩序化和固型化的理论批评。正因如此,作为国内第一部科幻小说评论专集,《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并未试图建立某种统盖全局的科幻诗学。就论述内容而言,作者策略性地选择将科幻的“叙事性”和“现实性”作为分析重点来建构科幻小说的中国阐释,在系统介绍世纪末科幻新浪潮兴起始末、探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谱系的同时,分析中国科幻的先锋性、想象力、创造性之于世界的意义。 诚然,在这本十余年来陆续发表文章的结集中,其中难免出现一些重复甚或矛盾的痕迹。但这正是作者在提出新理论过程中留下的“未完成的仍在进行中的”思考痕迹,亦是其对新颖观点不断筛选、淘洗、打磨、统合的另一种证明。24以“新浪潮”一词形容科幻叙事的气势,不仅体现了宋明炜对科幻在当下引起关注之“此刻意义”的洞见和发掘文学新质的学术敏感,更显示了他试图打造“极具中国特色的科幻诗学”25和创新理论格局的雄心。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汪晓慧:1995年生,浙江临海人。曾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评论文章,另有小说发表于《钟山》。 注释 1:2010年,科幻作家飞氘曾在“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就当时的科幻文学景况做过精妙的比喻:“科幻更像是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着,也许某一天,……会斜刺里杀出几员猛将,从此改天换地。但也可能在荒野上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最后自生自灭,将来的人会在这里找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而锻造和挥舞过这把兵器的人们则被遗忘。” 2: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269页。 3: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4:刘亚光,宋明炜:《如何理解“中国科幻新浪潮”?》,《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7月23日。 5:科幻作家、评论家王瑶(夏笳)在博士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恐惧与希望:当代中国科幻文学及其文化政治(1991-2012)》中亦将“清污”运动以后科幻小说再出发的起点定位在了1990年前后。 6:宋明炜:《〈叔叔的故事〉与小说的艺术》,《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7: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页。 8:对于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的代际划分参见《中国百年科幻史话》,董威仁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9:吴岩:《科幻文学的中国阐释》,《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 10: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202页。 11: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12: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01页。 13: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页。 14:[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15:[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美]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陈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 17: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页。 18: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页。 19: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页。 20:[美]弗兰西斯·福山:《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序言。 21: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3页。 22:王瑶:《火星上没有琉璃瓦吗——当代中国科幻与“民族化”议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 23:张朔:《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研究刍议》,《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4:在即将出版的英文科幻理论专著《The Fear of Seeing》(《看的恐惧》)中,宋明炜对这些观点和动态思考进行了更为成熟透彻的系统性总结。 25:王德威:《想象世界及其外的方法》,《读书》,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