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荣芬: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http://www.newdu.com 2025/11/21 04:11:02 今日语言学 邵荣芬、张洁 参加讨论
邵荣芬(1922—2015),字欣伯,汉族,安徽寿县人。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历。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以前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2006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先后任《中国语文》杂志编委,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语言学科片研究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音韵学”副主编、《续四库全书·经部》特约编委、《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编辑部顾问等职。学术专长为汉语音韵学、词汇学。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邵荣芬先生在第1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泰国,1985 主要著作:《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华书局2011年校正)《中原雅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中华书局2008年校订本,2016年5月中华书局再版)《经典释文音系》(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年)《法伟堂经典释文校记遗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集韵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邵荣芬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 邵荣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汉语音韵学家,曾任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踏实努力地工作着,为我国音韵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音韵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邵先生为人宽厚正直、淡泊名利,他的学者风范在学界享有盛誉。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编纂出版一套《学问有道》丛书,内容是请社科院的学部委员谈人生和治学经验。当时邵先生在身体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在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 张洁:众所周知,汉语音韵学是一门绝学,晦涩难懂。您很早就对音韵学感兴趣了吗?为什么选择了以音韵学作为毕生从事的事业? 邵荣芬:我早年在浙江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开始对音韵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听说音韵学是一门绝学,艰深难懂,好奇心促使我想去挑战困难,一探其秘,看看它到底有多难,我能不能学好;而且音韵学是国学的基础,学好音韵学对于理解很多文字、词汇、语法上的语言现象很有益处,对于进一步学习古典文学也很有必要;就音韵学本身而言,语音变化规律性很强,对应严整,更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因而1948年毕业后,升读本校研究生时,就选择了音韵学专业,导师是任铭善先生。在学两年间读了不少音韵学方面的书,收集了一些资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毕业后到语言所工作,先后有机会直接受教于罗常培先生、丁声树先生、陆志韦先生。自此,我对音韵学的见闻日广,认识日深,兴趣也日益加强。从20世纪60年代起,语言所成立了汉语史组,我的研究工作正式转到音韵学方面,从此与音韵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洁: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分子,您的身上秉承着极强的“修身”理念。“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是您的座右铭,我理解为“从人格的自我完善出发,真诚、踏实、正直地做人,认真、细致地做事、做学问”。在人生的各种风风雨雨中,你坚守自己做人、做事、做学问原则。请谈谈您的心路历程。 邵荣芬:你的问题我理解为询问我的思想、人格的形成过程。首先家庭的影响对我人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父母善良本分,待人宽厚。父亲是小学教师,酷爱读书,是当时乡里最有学问的人。他要求我多读书,多学习,强调读书、掌握知识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他教我做人的道理,要求我从小要有远大志向,树立人生目标。 我十五岁时为躲避战乱而离开老家,在湘西一个收留流亡学生的中学上学。高中一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是张汝舟先生,他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张先生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在授业解惑、诲人不倦的同时,特别强调做人的道理。先生经常让学生去他家听他讲人生哲理,他常说:有好的品德,才能做好的学问。他身体力行,希望学生“以敦品励行为务”、“以修身为根本,博学为枝叶”。先生尤其注重国学,强调学习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对于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先生的言传身教,为我处世为人做出了榜样,并为我笃志国学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经历让我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决心。当时日本鬼子攻陷南京,为躲避战乱,我离开合肥来到六安的临时中学上学。一天,我们正在上课,日本飞机突然来轰炸,我逃出学校,跑到河边贴岸而立,日本飞机上的机关枪就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扫射过去,目睹着日本飞机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狂轰滥炸,机关枪到处扫射,街上尸横遍地,百姓痛哭流涕,劫后余生的我痛感只有强大的祖国才能摆脱他国的侵略,立志要为祖国的富强而学习。 我早期的人生经历中有很多的磨难,每一次磨难都锻炼了我的意志。抗日战争初期,我所在的中学学生流亡大西南,由安徽步行翻过大别山,经湖北、湖南,穿过洞庭湖,到达湘西麻阳。学生们背上背一床军用毯子、 一把雨伞。一路上,走的大多是坎坷不平的山路,赤脚穿草鞋,每天走四五十里,脚都磨烂了。晚上到老乡家借门板睡觉,真是风餐露宿,异常艰苦。 到了湘西后,政府在那里成立了国立安徽第八中学,我进入该校学习,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但我却得了很严重的细菌性痢疾,由于当时缺医少药,我的病久治不愈,已奄奄一息,是一位姓毕的校医给了我从德国带来的好药,才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 高中毕业后我去考大学,就奔向贵阳,因为当时很多大学都在贵阳招生。为节省费用,我当了一回“黄鱼”,就是沿路搭坐国民党军队的运水雷车。到了贵阳,我的痢疾又犯了,运水雷车的司机看我像个读书人,很照顾我,免费把我带到了遵义,正好赶上浙江大学招考。我带病上考场,时值盛夏,我穿着毛衣,由同学扶着进考场。考完后同学又给我买来了豆浆充饥。就这么艰苦,我竟然很幸运地考中了。 在浙大上学时,缺衣少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八个人一碗菜,上大一时,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裤,腿都冻肿了。由于缺乏维生素B,我得了脚气病,我的同学把自己的毯子、毛衣卖了,买了维生素B针剂,才治好了我的病。 这几次磨难,培养了我在艰苦的条件下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增强了我的爱国心。我深刻地认识到无国即无家,国家弱了就会受人欺负,祖国富强了才能抵抗外来侵略,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同时在困难中,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同学的友情、真诚与善良,更让我学会了待人宽厚、仁爱。 毕业后我从事研究工作,立志要做一名学者。我要求自己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尽心尽职,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对得起国家对我多年来的培养。 20世纪50年代,国家号召语文工作者致力于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的三大紧迫任务,我暂时中断了音韵学的研究,从事汉语规范化工作。我觉得作为一名学者,应该尽心尽力地服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且语言学的各领域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做汉语规范化工作对于音韵学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因此我很愉快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期间,我做的工作是研究外来语词汇的发展规律,与陆志韦先生合作制定俄英德法四种语言汉字译音表,以规范专名译音。与其他同志合作,撰写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为编写规范性的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国家任务做理论及方法上的准备。 20世纪60年代,我正式开始做历史语言研究,语言所成立了古代汉语组,陆志韦先生任组长,我开始搞专业研究。当时我们打算写一部音韵史,根据分工,我研究中古《切韵》音系,后来感到写音韵史的条件还不成熟,取消了原来的计划,而我仍然继续研究《切韵》,最后写成了《切韵研究》一书。  张洁: 您从事音韵学研究四十多年,成就斐然。请从音韵学研究的角度谈谈您的治学经验。 邵荣芬:科学研究都要从选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做结论四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就选题来说,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该选择所攻学科的根题,也就是关键性的有生长能力的课题。《切韵》音系就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根题。《切韵》是中古时期保存完整的音系资料,据此可以上推上古音,下连近现代音。对《切韵》音系的认识正确与否,是能否正确认识上古音和近现代音的关键。我刚开始研究音韵学时,选择的就是《切韵》音系这个课题。这是个大课题,包含问题很多,需要我们把问题排排队,一个一个加以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某些问题。而如果想研究上古音或近代音,也需要全面掌握前人对《切韵》音系的研究成果。 后续工作的选题最好选择与已经完成的首选之题有重要关联的课题,以便两者能够起到互相比较、互相启发的作用。我在《切韵》研究结束后,很自然地想到与它差不多同时的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音切的音系。我认为,《切韵》音系的基础方言基本上是当时的洛阳话,代表当时的北方标准音系。而《释文》音切的音系基础应当是当时的金陵话,因此它是南方的标准音系。对《释文》音系的研究,不仅关涉到《切韵》音系的性质,也关涉到对中古音南北大格局的全面了解。 因此我就选定《释文》作为我的第二个研究目标。 至于有人研究过的资料能否作为选题目标。我认为凡在方法或内容上你能提出与前人不同见解的,仍然可以作为选题目标。事实上,很多复杂的资料,不要说研究过一次,即使研究过十次八次,甚至于几十次,也未必能把里面所含有的全部语音信息彻底揭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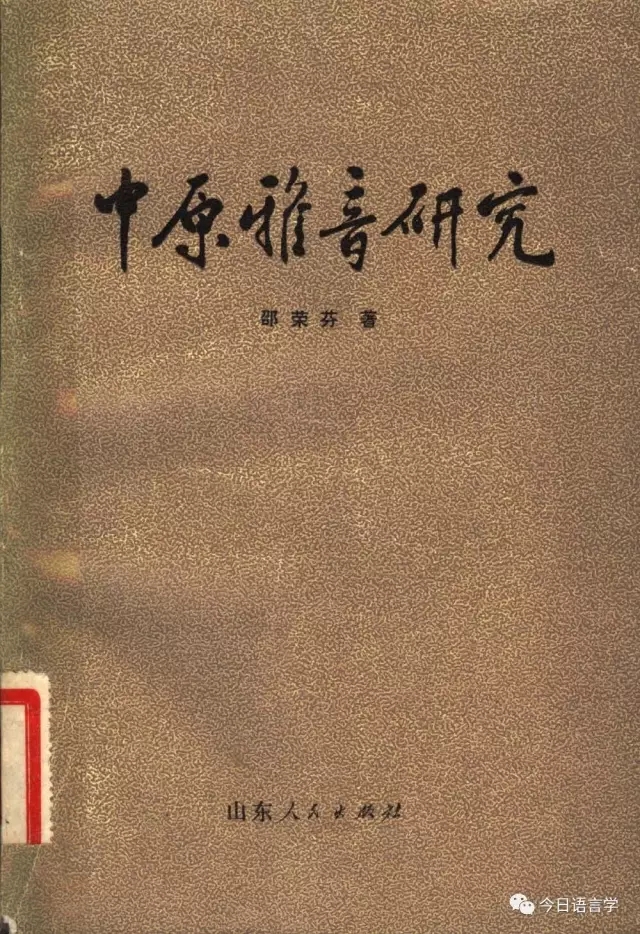 第二,就收集资料而言,最重要的是资料的准确性,也就是所收集的必须是自己课题范围内的资料。要做到这点,对有些资料来说并不容易。 对韵文韵脚字的识别,近体诗、词等比较容易,而没有固定格律的先秦韵文、散文中夹杂的韵语就比较困难。在收集韵字材料时,务必小心谨慎,对韵例要有正确的判断,绝不能掉以轻心。 对反切资料的识别也要仔细。比如《切韵》反切有正音与又音之分,两者性质不同,正音反映《切韵》自身音系,又音是一些古音或方音,与正音在体系上往往有矛盾。因而研究《切韵》音系时,应当依据正音,才能避免把体系搞乱。 通假字也存在辨别问题。通假字有两类:一类是学者们考辨出来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类是异文。异文见于不同的本子,往往比考辨出来的通假字更为可靠,但也需要仔细辨认,只有在彼此音同或音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通假字,而其中还要将异体字和形误字排除出去。 从以上诸例可知收集资料并不都是轻而易举的机械操作,其中还包含着比较繁难的挑选和识别工作。 收集资料从量的方面来说,当然越多越全备越好。有的资料集中于一本书内比较容易全部收集,比如《说文》的读若等。而有的资料繁多,又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难于收集齐全,比如通假字。面对这类比较繁难的资料,一般多把论题缩小到个别问题上,以便于收集资料。不过由于通假字在语音关系上比较宽泛,即使把论题缩小到观察某两音之间的关系,收集资料时也绝不能仅限于两音之间的通假资料,还必须全面收集两音与其他音之间的通假资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分析资料是研究工作的核心,分析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研究工作的成败。一些基本概念应该牢牢记住。 其一是资料的语音信息量,资料不同所含的信息量也很不同。反切所含的语音信息量较高,一般来说,凡反切上字相同的反切,所切字的声母就相同,反切下字相同的反切,所切字的韵母就相同。而谐声所含的语音信息量就比较低,同一个声符所谐的字,声母不一定相同,韵母也不一定相同。通假也是如此。谐声和通假的这一情况跟它们产生的时代和地域上的跨度较大有一定关系,另外,即使时、地跨度小,甚至同时同地,也并不能完全改变音近通假的现象。了解谐声和通假所含语音信息量不高的特点十分重要,否则见到送气与不送气、清与浊相通或相谐,就认为上古声母没有送气与不送气之别,没有清浊之别,见到声调不同的字相谐或相通,就认为上古无四声,那就很荒唐了。 其二是音变的总规则,即“语音在相同的条件下,不能有不同的变化”。这是一条比较语言学的规则,它管着一切语音分化。我们在分析资料、观察音变时应该牢牢记住。尤其是在假定后代两个不同的音是从古代同一个音分化出来时,必须说明它们的分化条件。如果不说明,或说明得不合理,便不能算是完整的或合理的假设。 其三是语音结构的规律性。语音是一个系统,它的结构都有规律性,分析语音时必须注意这点。比如董同龢在上古唇鼻音m之外又拟了一个清的唇鼻音hm,而舌尖和舌根鼻音的位置都没有构拟清鼻音,于是出现了不均衡状态。李方桂看出了这问题,在他的上古声母系统里,把鼻音都构拟了一个清鼻音,配列如下: 清 hm hn hng hngw 浊 m n ng ngw 这样系统就显得十分整齐,说服力就强多了。所以,结构的规律性不论是在启发分析思路方面,还是在判断是非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其四是音位学的基本概念。如最小对立、分布互补、音位变体等概念,在音韵分析时经常用到。比如《广韵》有些声母如帮组、见组等的反切上字三等跟一二四等有分组的趋势,高本汉认为分组是显示三等有一套j化声母,即pj-、kj-等。由于他认为喻四是四等,是不j化的,并与j化的喻三对立,他的j化声母就不是不j化声母的条件变体,而是两套真正不同的声母。其实反切上字所分的两组分布是互补的,且不说分得很不彻底,即使彻底,也不能把它们作为对立的音位来看待。高本汉的j化说可以说是在音位上处理不当的一个例子。 其五是音变的阶段性。汉语方言复杂,发展很不平衡。不过在先秦就已有共同语性质的雅言存在,往后汉语的发展当然就有了一条主线。汉民族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先秦雅言不用说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汉语的发展主线也就是以北方话为核心的发展路线,有其内部的一致性。它的每一发展阶段必然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在观察音变时务必要记住这些特征。比如,浊声母消失是《切韵》以后的事,有人却说汉代或更古时这种音变就已经存在;又比如,见系声母颚化是近代的音变现象,有人却说上古时就已经发生了。显然这些说法都犯了时代错误,忽视了音变的阶段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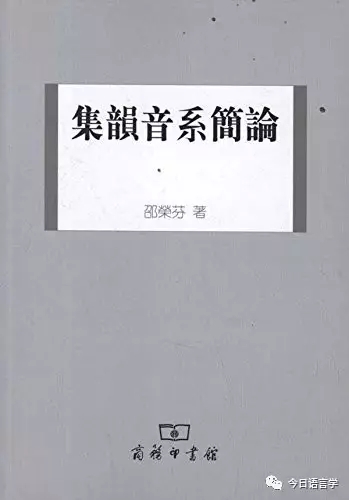 第四,做结论,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有两点要注意: 其一,要尊重前贤和时贤,但不要迷信。我们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不论大小都是在前辈学者辛勤劳动所得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对前辈学者要有足够的尊重和爱戴,这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基本道德。但尊重前辈并不等于迷信他们。事实上再大的权威,其研究工作都不可能完全没有缺点。改正这些缺点是后人责无旁贷的。因此资料分析要求我们做什么样的结论,就做什么样的结论。真正的学者都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对别人的不同意见都是能客观对待的。记得早年我写了一篇评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短文,里面指出了高书的一些不妥之处。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了王力先生的一封信,并把他的《汉语史稿》第三册即词汇部分送给我一本,要我给他提意见,并说我批评高先生的错误,大多也是他的错误。王先生这种从善如流、虚怀若谷的精神显示了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应该能够解除我们的顾虑,鼓起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勇气。 其二,不要先入为主。在接触资料之初,往往会产生某种或某些设想或假定。在整理分析资料之后,这些设想有可能跟资料一致,有的则可能不一致。不一致时就应该修改或放弃原来的设想,绝不能坚持原来的设想不放而强为之词。这是做结论时的一个基本态度,离开这个态度,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采访者张洁与邵先生和邵师母  张洁:作为音韵学会前任会长,您对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请问您对目前音韵学的研究状况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什么看法? 邵荣芬:现在的音韵学研究可以用“欣欣向荣”一词来形容。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中期,只发表了音韵学论著10种、论文115篇,音韵学的发展很一般;“文化大革命”时期,音韵学研究处于停顿状态;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到现在,音韵学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论文、著作数量大增,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硕士、博士数量相当可观。 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不再局限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代表音系上,而是对音韵史上的空白点和模糊点做了大量的探索,对各时代的各种与音韵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其中有很多材料都是新发现的,如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资料、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等,这对于探索汉语各阶段的语音特点、进一步掌握汉语语音史上语音演变的规律十分有利。 第二,研究水平大大提高,研究内容不断深入。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挖掘、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很多原来分歧比较大的观点渐渐趋向一致。比如, 在上古音方面,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已经基本成为共识,现在已很少有人提出一个韵部多元音说了。当然,各家拟音的元音系统并不一致,这还有待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于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声母的问题,随着汉语方言、同系属语言历时比较研究的逐步展开,已经渐渐明朗化,尽管目前还有部分人持怀疑态度,但大部分人已承认复辅音的存在了。 中古音方面,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原来有杂凑说、综合音系说、单一音系说三种看法,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单一音系。又如,高本汉针对反切上字的分组现象,曾提出过把《切韵》帮组、见组等声母构拟成j化和非j化两套,并把浊塞音和浊塞擦音构拟成送气声母,陆志韦先生提出了质疑,后来经过学者们的反复研究探讨,已经取得共识,高本汉之说已经被否决了。 重纽问题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目前学术界都承认了存在重纽的区别,而且对于重纽在音值上的差别,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介音区别说占了上风。 近代音方面,关于《中原音韵》的声母问题,曾有过二十个声母说、二十七个声母说、二十四个声母说、二十五个声母说、二十一个声母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二十一个声母说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这类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能尽举。共识范围的不断扩大,使音韵学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宽广、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从而又为音韵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的理论、新的假设和新的问题不断提出。新假设或新论点是新知获得和科学进步的起点,提出新假设或新论点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学科有没有获得良好发展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音韵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断探索挖掘,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新假设、新理论,这对于丰富音韵学的研究内容,活跃并推动音韵学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目前音韵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是,与同系属语言的比较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音韵学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上古音的一些问题,如果能通过与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也许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得以解决。我国境内有几十种可能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很方便,而且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近年来在国外学者的影响下,国内发表有关比较研究的论文已经有所增加,数量和质量也有所提高,今后还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对于解决音韵学中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很有好处。当然,历史比较研究并不容易,一方面要掌握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要对汉语及与之相比较的亲属语言具有相当深厚的根底,否则就不容易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  王显先生、管燮初先生、邵荣芬先生与第一届研究生 张洁:请谈谈您对青年音韵学工作者的期望。 邵荣芬:青年音韵学工作者是音韵学的未来和希望,我想在这里向他们提几点希望。 首先,年轻人要打好学科基础。要做好音韵学研究并不容易,不仅要学好音韵学、音系学等知识,还要懂古代汉语、方言、文字学、词汇训诂、少数民族语言等,还要懂一两门外语,以便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只有基础夯实了,研究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其次,要珍惜时间,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不能仅仅依靠八个小时。 再次,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青年人有新的想法、新的观点要大胆地说出来,特别是与前辈师长的观点相抵触时,不能有所顾虑,要发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但对前辈学者应该有足够的尊重。 最后,要善于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不要产生抵触情绪,不要把个人情绪掺杂到学术研究中,要敞开胸怀,以探索真理为目的,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正确对待批评,这样才有助于提高研究水平。学术争论在所难免,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学术争论,就能在学术界营造和谐的氛围,这对于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都大有裨益。 这些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但真正做起来,而且要做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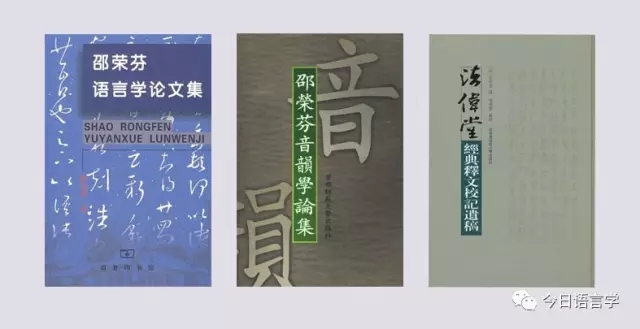 张洁:您曾经参加过汉语规范化问题的研究,并发表了很有影响的《统一民族语的形成过程》一文,提出了“基础方言以和平扩展的方式形成民族共同语”的观点。目前,我国由于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人口流动加剧,在使普通话得到进一步推广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方言迅速萎缩,乃至消失,一种语言的消亡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这是中华民族人文科学史上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有很多学者为此喊出了“抢救方言”的口号,还有些人甚至提出要“保卫上海话”、“保卫温州话”等。请您就目前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之间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邵荣芬:语言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方言消失而向普通话靠拢,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任何为了保存方言而排斥普通话的人为行为肯定是行不通的。语言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方言,尤其是与普通话差别大的方言,更要向普通话靠拢,这样才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然,我国各地方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民间文化宝库,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文化意义,抢救方言、保护方言,是要尽最大可能记录方言、描写方言,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这也是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事,这需要语言工作者投入大量工作。  左起:唐作藩先生、陈新雄先生、邵荣芬先生和杨耐思先生 原文刊于《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1059—1068页。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学术报告】张洪明:轻重音及其相关的韵律研究
- 下一篇:吴福祥研究员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