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梅研究员访谈
http://www.newdu.com 2025/11/20 11:11:00 今日语言学 方梅、王文颖 参加讨论
| 方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语文》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理事,现任中国语言学会秘书长(2010年起),国际语言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汉语语言与话语学报》,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编委,日本语言学期刊《中国语文法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Grammar,朋友书店)编委。 专业研究领域为语法学与篇章语言学。近期工作为运用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话语、语用和认知因素对语法范畴和句法结构形成的制约关系,以及共时语法化过程中的演变机制。长期从事语法学、篇章语言学和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  王文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方老师您好!语言研究所“今日语言学”微信公众号委托我来采访您。 在此之前呢,“今日语言学”也访谈过一些学者,大家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著名的语言学者是因何种机缘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的。您能不能也谈一下自己当初是怎么对语言学产生兴趣、同语言研究结缘的呢? 方梅:我是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北大中文系在恢复高考以后,77级有文学、新闻、古典文献专业,78级有文学和汉语专业。我那个时候对汉语专业的理解很有限,倒是对文学充满好奇。真正让我觉得这门学问有意思,还是在系统地学习了各门课程以后,发现这门学问在描写和解释现象的时候讲究论证。那时候听朱德熙先生的课,分析歧义结构,辨析“在黑板上写字”的不同解读,论证“的”字的不同语法功能,真是妙! 再一个就是语言学讲究调查。王福堂先生的方言课是本科生必修课,这门课有一学期,期末有一个月的方言调查。我们那一届的调查是王福堂先生和王理嘉先生带队,当时的研究生沈炯、陈泽平、贺宁基做辅导员,去了张卫东老师的老家胶东。1982年,林焘先生给本科高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北京话研究与调查”,这门理论学习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课程,对我而言可谓受益一生。那时,赵元任先生《汉语口语语法》的吕先生中文译本刚刚出版,而英文版只能作为内部印刷品“参考资料”在王府井锡拉胡同外文书店的后门买到。在那门课上,林先生带着我们读赵元任、俞敏先生的著述,讲他自己最新的研读心得。对我来说,对韵律模式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对语音现象的共时差异与历时演变的关系的认识,以及田野调查自然口语的基本方法等等,都是从这门课上开始起步的。这门课还包括在北京城区做北京话调查,期末作业是转写录音材料,并且从材料里发现有意思的现象。北京话两个去声字连读的时候前一字变阳平,这个现象就是那时在城区调查发现的,后来林焘先生的讨论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上。大家现在看到的北大CCL语料库的北京话材料,就是林焘先生带领我们79和80级同学两次课程的调查材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大学里还很少有实验语音学研究,而北大在林焘先生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建立语音实验室了。王理嘉先生给本科生讲授实验语音学,我们或许是国内最早接触语音实验的本科生了。王理嘉先生的话我至今记得。他说,你们或许将来不做实验语音学研究,但是这些语音学知识和实证研究的训练会对今后的工作有帮助。 现在想起来,学校提供前沿课程、带给学生国际化的视野非常重要。社科院语言所的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赵世开先生,中央民族学院的马学良先生,美国的罗杰瑞、王士元、梅祖麟先生都给我们上过选修课。开阔视野还包括鼓励学生读外文文献。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林焘先生的夫人北大西语系杜荣教授为我们班开设了一个学期的专业英语,教材是Fromkin和Rodman的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当时国内很难买到外文书,我们手里的教材是照着原版书打印后装订做成的油印本。 王文颖:现在回忆起来,您写作的第一篇语言学学术论文是什么?那时候是怎么发现问题、怎么来研究问题的呢?这对您后来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方梅:第一篇语言学学术论文是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陆俭明先生给的,《关于复句中分句主语省略的问题》。陆先生说,句子省略主语是汉语语法里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有很多文章讨论,但是省略究竟有多少花样,还得拿着一定量的文本做统计分析。于是我就用老舍的小说做材料,把凡是有主语省略的句子抄成卡片再作归纳。即便现在看,文章搜罗的省略类型也是很全。这篇文章有一个我自己比较得意的发现,即所谓“蒙后省略”是有篇章条件的。被“蒙后省略”的这个成分,它是整段话的话题。从篇章角度看,其实还是承前省略。这个观察特别得到陆先生的肯定,1985年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上,1986年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可以说,我做篇章语法的研究是从陆先生指导的这篇文章开始的。 王文颖:看来您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语言使用的问题了。那在此之后,您的研究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方梅:这还得从本科的时候帮助留学生学汉语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大有留学生陪住制度。为了让留学生在生活中有个良好的汉语环境,学校安排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宿舍。我的日本同屋很用功,写了作业先让我看。于是我就要给她讲,为什么这个句子不通,为什么这个词不能这样用。当时读大三,正在上马真先生的虚词研究课,学以致用,很得意。也正是这个原因,1983年在北大留校,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选择做对外汉语教学。教学中,随时把学生的病句做成卡片。有的问题能解释,有的问题解释不了。而解释那些“解释不了的”就是研究的动力。 对外汉语教学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角度看我们的母语,从比较中发现问题。1991年我在《中国语文》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研究的问题就来自于教学,文章讨论具有提示作用的“是”字句。比如对话里,“A:这裤子多长?B:这是尺子,自己量量。”对话中的“是”字句并非用来回答“这是什么”,不表达等同关系。1989年,我在语言所首届“五四”青年演讲报告的就是这个,文章讨论了口语里这类“是”字句的解读和构成限制,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肯定。吕先生说,一个“是”字看上去简单,其实非常有讲头。所谓的系词,在不同语言里面的功能有差别,对话里的用法和书面上的用法也有差别。这个题目有意思,文章把用法讲清楚了。报告获得了一等奖。吕先生的肯定是巨大的鼓励,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在做编辑的同时也做些研究。而且,着眼点就可以放在对日常口语的研究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语言所的廖秋忠、陈平等话语功能语言学家的研究,也给我们很多启发和帮助。我最早读到的功能语言学文献是陈平先生赠送的一个旅行袋的复印资料,是他在美国读博士期间的参考文献;我在《中国语文》上的第二篇文章讨论宾语和动量补语的次序问题,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经过廖秋忠先生的指点。我们的老所长刘坚先生、江蓝生先生,编辑部的主编侯精一先生、副主编饶长溶、徐枢先生和后来的副主编施关淦先生,他们的学术眼光、学者胸怀和敬业精神,他们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和鼓励,使后辈得以在工作实践中不断通过学习加强理论修养。语言研究所多学科高水平的研究平台,使青年学者有更多的机会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了解前沿性研究,在跨学科的交流中成长。  吕叔湘先生手书 王文颖:从功能语法研究到现在的互动语言学,研究思路上有没有什么内在的、根本性的关联? 方梅:功能语言学认为,对所有的语言来说,都是用法为根本,“语法以用法为基础”(Grammar is usage-based)。Newmeyer(2003)说“语法是语法,用法是用法”;Bybee(2005)针锋相对地说,“语法也是用法,用法也是语法”。  用法研究与动态语言观也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理论遗产。由于汉语缺少表面的句法形态,汉语语法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用法的描写和解释。这种研究传统贯穿于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赵元任先生的《汉语口语语法》和朱德熙先生的一系列汉语语法著述中,也成为汉语语法研究最为重要的研究取向。 吕叔湘先生说,“一个语法形式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研究它在语句结构里的地位:是哪种语法单位?是句子或短语里的哪种成分?跟它前面或后面的别的成分是什么关系?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研究它出现的条件:什么情况之下能用或非用不可?什么情况之下不能用?必得用在某一别的成分之前或之后?等等。前者是理论研究,后者是用法研究。”“一种语法形式可以分别从理论方面和从用法方面进行研究。哪方面更重要呢?这要看情况。首先,可能有某一种语法形式,在用法上没有多大讲究,在理论上很值得讨论;也可能有一种语法形式,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可讨论,可是在用法上很讲究。”“也有这种情况:不把用法问题摸透,理论问题也解决不好。”“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语法研究中用法研究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语法研究和探索(六)》序) 关于汉语中“用法”与“语法”的关系,沈家煊先生有一个准确的概括。“语法也是用法,用法不都是语法”。“从语言的原生态‘用法’出发,英语已经从‘用法’中分裂出一个‘语法’来,与‘用法’形成分立格局,有一个‘交界面’。而汉语是‘用法’中虽然有了一个‘语法’,但是还没有从‘用法’里分裂出来,还处于包含格局,不存在什么‘交界面’”。“汉语离开了用法就没有办法讲语法,或者没有多少语法可讲。”(《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一辑)  互动语言学(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是功能语言学近些年来着力推进的领域。互动语言学研究更加关注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动态表现,以及交际因素对编码方式的影响和塑造。互动语言学更强调以自然口语对话为研究对象,重视交际形态和会话组织结构对编码和理解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关注语法的互动性,探讨语法的在线生成现象及其影响因素;二是关注交际类型对表达形式的塑造,探讨不同语体功能类型的语法表达差异;三是探讨言者立场态度的表达策略和理解机制。相对于上世纪末期的研究,当前更加重视会话组织和会话序列与话语理解的关系,关注话语与副语言的整合效应,注重对会话的多模态表现的调查。 互动语言学这个提法是“外来”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西海岸功能语言学派的系列研究。但是从方法论上说,其思路是汉语研究的“本来”。吕叔湘先生(1961)在《汉语研究工作者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口语语法的研究”,“进行口语语法的研究,不光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口语,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书面语。比如对于语法分析很关重要的语调、重音、停顿,等等,在书面材料里就无可依据,非拿口语来研究不可。”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里,吕先生指出:“过去研究语言的人偏重书面语材料,忽略口头材料,这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在实际工作中,他鼓励研究人员作口语调查,使用转写材料进行研究。他说,“有一项工作很值得做,就是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话录下来,各种风格的话,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录下来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然后把它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拿这个去跟逐字记录的比较,可以看出人们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把口语变成书面语。”(陈建民著《汉语口语》序)在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的大力倡导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产生了一批对口语研究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成果,比如陆俭明先生关于能独用的副词的研究和易位现象的研究,孟琮先生关于北京话语法的系列研究,史有为先生关于易位现象和语气词的研究,沈家煊先生关于对话中话题与说明关系的研究和口误现象的研究等。 对于互动语言学,沈家煊先生有一个非常通俗的解释:语言不仅指说的话,还指说话本身,指说话行为。说还是不说,这么说还是那么说,现在说还是以后说,在什么场合什么心态下说。这都是语言研究的重要问题。说话很少是自言自语,至少是两个人对着说,所以说话就是交谈者之间的“互动”。语言共性何处求,不在语法在用法。而重要的用法就是交谈者之间的“互动法”。(《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一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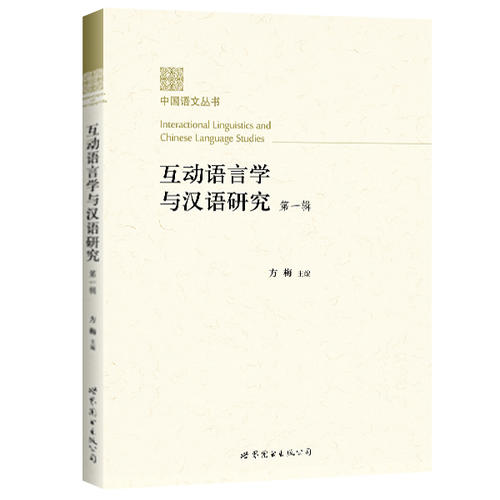 王文颖:作为在《中国语文》工作了近30年的编辑,杂志的副主编,您对于青年学者有哪些建议,投稿应避免哪些问题? 方梅:对于稿件的需求,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这本刊物的办刊宗旨和多学科的综合性特点。《中国语文》杂志1952年创刊,已经走过了近65年的历程。务实和创新是《中国语文》几代办刊学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追求。 语言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问,无论做语言历史的研究、现代语言的研究、还是对语言的载体——文字的研究,都讲究调查考证,讲究要用材料说话——包括对历史典籍的调查、对出土材料的调查、对正在使用中的当代共同语和方言的调查、对语言习得的调查,等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使得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从传统语文学逐步迈向现代语言学。但是,说到底,语言学的实证研究的基本特性没有变。《中国语文》作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园地,对务实的追求没有变。 说到创新,一本学术期刊的创新体现在哪里?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充分反映学界最具有前沿性的研究成果;第二,以新的学术思想、新的观察视野、新的研究方法,引导和推动学术发展;第三,不断发现和培养学术新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说到投稿要注意哪些问题,首先是要适合《中国语文》期刊特点,第二是要避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先说第一方面,要适合《中国语文》期刊特点。《中国语文》作为汉语语言学界的综合性刊物,一方面要求它几乎覆盖所有语言分支学科领域,另一方面与其他专门领域的期刊也有所不同。首先,基于期刊的基本定位,在众多的来稿中决定取舍,有时甚至不是文章本身有何重大失误,而是在该领域内横向比较是否出色。第二,作为一本语言学期刊,其优先选择的文章首先是能够回答汉语语言学问题的文章。比如:1)对于汉字字形的讨论有不同的方面,《中国语文》的文章应更关注“形-义”关系,对于字形的梳理和解释要回答语言问题。2)词汇研究的来稿量很大,具有竞争优势的文章要能得出概括性结论,能解释一类现象而不局限于一词一义;在材料、方法、观察视角上有新意,对同类研究具有启发性。3)方言研究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的文章,无论是探讨方言音韵还是方言语法问题,往往是这类描写的现象在该方言区的调查中还少为人知,或者这个现象对跨方言比较具有重要意义。4)鼓励新的观察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鼓励新兴领域和跨学科探索,但应是问题导向的实证调查研究。总之,要把汉语研究置于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大背景之下,发现和解释汉语事实。通过对汉语的调查分析,揭示语言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才能为汉语语言学真正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第二个方面,要注意的问题。举例来说:1)分析解释汉字的形义关系,在历史音韵上要能讲得通;2)描写方言语法,本字要找对;3)研究现代语法,避免以某种理论框架比附汉语事实,或者以汉语事实来修补已有理论框架内的技术处理方案;4)对局部现象作描写和分析时,要了解其他语言或者方言的相关现象;5)要关注海外发表的汉语研究成果,避免重复性劳动。 吕叔湘先生对《中国语文》编辑的要求很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吕先生还参加编辑部的会议,经常会问我们最近在读什么书。他希望编辑要做到“眼高手低”。“眼高”就是要有理论眼光,学术视野开阔;“手低”就是要在基础工作上用心,不放过细节问题。作为年轻编辑,要做到吕先生说的“眼高”,就需要通过不断学习站在研究的前沿。“眼高”的要求,促使我们的编辑人员保持“编研结合”的工作状态,这也成为保证期刊学术水准的最为重要的条件。而主编参与校对这个传统延续至今,也正是践行“手低”的精神。我想,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如果也能用“眼高手低”要求自己,一方面了解国际语言学界的理论前沿,另一方面踏踏实实调查汉语事实,肯花时间从一手材料做起,“了解外来,不忘本来”,一定会做出让国际语言学界耳目一新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张敏:汉语为什么(还是)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
- 下一篇:王洪君教授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