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兴:此生与辞书有缘
http://www.newdu.com 2025/11/21 03:11:02 今日语言学 张振兴 参加讨论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研究员2017年10月28日在“闽南方言与文化研讨会暨福建省辞书学会第23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稿。 辞书是知识的宝库,碰到不懂不明白的问题,首先就是想到查一查辞书里怎么说的。一个人的最初最早的学问,很多都来自各种各样的字典词典和辞书。我也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喜欢使用1979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任何时候她都出现在案头。我在多个场合说过,《现代汉语词典》不仅是用来查的,也可以是用来读的,很多条目解释之精到,只有读了才能领会。几十年了,这本词典翻的封面掉了,里面很多页面也模糊不清了,到了今年夏天不得不换用第七版的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可是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那份感情,那份感恩,将伴我终生,我不可能忘记。 我年轻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跟辞书有缘。由于我的方言背景,我到语言研究所工作以后被分配到方言研究室,调查研究汉语方言成为我的终生事业,就没有想到跟编纂辞书有什么关系。可是人算不如天算。199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投资立项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提出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由李荣先生亲自担任主编,二是必须由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出面组织。李荣先生首先找熊正辉先生和我讨论此事。我们都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推动整个方言学科的全面深入的发展。这件事情就这么应承下来了,至于会碰到什么困难,当时是考虑不多的。没有想到自此之后十年,竟然全部的学术生活都跟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联系在一起。  李荣先生担任主编,总筹大局,定夺决策;熊正辉先生和我担任副主编,辅佐李先生,主持实际事务。熊先生精于电脑,具体负责电脑排版等一大堆复杂事务,这是我不能做的事情;我则负责稿子的编校等日常专业编辑事务。有人评论说我们三个人的配合是“最好的组合”。从1992年开始至1998年,我们先后编纂了41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分卷本(2002年补了《绩溪方言词典》,成为42种分卷本),总字数多达2200多万字。从1999年开始在分卷本的基础上,编纂综合本,至2002年12月,正式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六卷本综合本,总字数也多达1300多万字。前后历经十年,总算告成。分卷本和综合本曾分别获得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的一等奖。经过这个十年历程,主编李荣先生来不及看到综合本正式出版,就驾鹤西归了;熊正辉先生白发丛生,退休了;而我也头发变白,过完人生中最美好的中年时代,开始步入老年。其中甘苦,心中自知。心里想着以后再也不编辞书了,不能再遭二茬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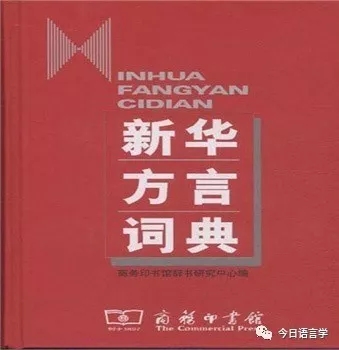 不料到了2003年底,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找我,希望我主持编纂一部中型的《新华方言词典》,供一般读者使用。我犹疑再三,不敢贸然。因为《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刚刚编成出版,苦楚犹在;何况我此时已经开始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A类重大课题《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与中国濒危方言调查研究》的任务,担子已经很繁重了。可是不知怎么的,最后还是承接了,由我、熊正辉先生、沈明先生等好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编纂组。这个中型词典一做又是五年,至2009年稿成,2011年秋季正式出版,全书150多万字。《新华方言词典》是个系列词典,好像没有获得什么奖,但读者似乎反映不错,因为很快2013年初就印刷第2版了。 就在编纂《新华方言词典》的过程中,我又陷进了另一部词典的纠葛之中了。2007年中,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应北京的一个民间文化机构的邀请,承担了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事情,亲自担任主编,并由山西大学的乔全生教授担任副主编。詹伯慧教授是我的一位交往多年的师友,他让我就近经常联系这家机构,代表他讨论有关事务。我不能拒绝,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就成了詹教授的“驻京办主任”,揽上了他在广州不方便办理的一切事情,包括交涉经费等等很麻烦的琐事。后来这家民间文化机构资金不济,最后资金链彻底断绝了,这时大词典还只是做了一些很基础的编纂框架设计工作,还没有进入正式的编纂阶段呢。詹教授和我,还有鲍厚星、刘村汉等几位业内的老朋友一再商议,觉得只有申请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才能把编纂大词典的工作继续下去。  詹伯慧教授是一个具有惊人意志力的人,有人说过,凡是他认为要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最终总是要做成的。果然,在甘于恩教授、乔全生教授的帮助下,2013年《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立项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负责出版的广东教育出版社也同时为这部大词典申请到国家重点书目的出版基金。于是2014年初,中断了一两年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全面重新启动了。就这样我也成为大词典的主要编纂人员之一。这么一做,又是整整四年,至2017年10月《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终于正式出版。我很荣幸与詹伯慧教授并列成为大词典的主编之一。其实这是让我感到很惭愧的。这部大词典分上下两卷,共460多万字,在首发式上受到学术界朋友的广泛赞誉。 从1992年至2017年的二十五年间,我前后参与并主持编纂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专业辞书。就这样,我在有意无意之中,在人生的学术之旅中与辞书编纂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真真实实尝到了辞书编纂之甘苦。 好像是《牛津大词典》哪一任的主编曾说过,如果想要惩罚一个人,最好就是让他去编辞典。据说辞书界还有一个共识,编纂大型辞书,是三分编纂,七分组织。这些话也许说得都有点过,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的时候,涉及50多位作者,他们的学术背景是不一样的,并且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各个分卷本涉及全国10类大方言,方言情况纷繁复杂,例外情况很多,很难统一要求。因此组织工作确实非常困难,偶然也有发急,发脾气的时候。  我除了主编《方言》杂志以及其他必要的学术活动、学术写作之外,几乎全部时间精力都用于编纂事务。那时社科院大楼里还是“鸽子笼”式的办公室,我的小屋大约只有不足5平方米,里面并列两张书桌,上面什么时候总是堆满要看的分卷本的初稿或校样,连转个身都不怎么方便。夏天的时候小屋里有时能达到38度,只靠地下一台小电风扇;冬天的时候日夜暖气不断,供应过分充足,大玻璃窗阳光暴晒,燥热异常。如有作者来讨论问题或朋友来访,他们只能坐在门外的走廊里跟我说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乎每天准时上下班,整整坚持了七年。我看过42卷本2000多万字的全部稿子和校样,很多稿子或校样都看过两遍或三遍,做了大量修改和校对的工作。遇到很难或不决的问题时,就请教李荣先生,由他最后定决。他的办公室跟我的只隔一层板壁,非常方便。 李荣先生的大脑里,总是充满了深邃的学问和智慧,严谨、缜密,而又简要、明了,在他那里几乎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有时也请教熊正辉先生,他为了大词典极其复杂的排版问题,也几乎每天准时上下班。在方言调查研究方面,他的学识和经验非常丰富,也经常帮助我解决难题。方言研究室的贺巍先生等人也会不时给我提供一些很好的主意和意见。记得那时还没有使用电子文件,所有改稿、编校,乃至与作者的往来讨论,都靠笔头和书信。我也没统计那些年里一共写过多少信件,只记得一次跟一位作者写信,讨论词典里的问题,一共写了28页信纸。至于写过三两页信纸的信件,那是常事。到最后1999--2002四年编纂综合本的时候,组织工作简单多了,条件好一些了,也用上电脑了,但大量的工作还是在纸本上进行。要安排新的体例,要对条目进行合并删除,要搜集并补充大量新的材料,很多条目要重新注释,同样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就是这样过了整整十个年头! 编纂《新华方言词典》的时候,组织工作当然简单多了,最主要的就是精选和补充方言条目,条目的分合和注释成为最大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表现汉语方言的一致性和分歧性特征。同时既要坚持专业性,又要做到通俗性,只有这样才能让一般读者所接受,做到这一点却是颇费斟酌的。参与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时候,詹伯慧教授和他身边的甘于恩教授、刘新中教授等人承担了全部组织统筹的工作,我觉得轻松多了。除了定期的讨论会之外,我们平时大量的编纂工作,包括跟出版社编辑组的联系,都是依靠电子文件,甚至是靠大量的微信短信来实现的。不过现代化的编纂手段经常让人无所遁形,源源不断的电子文件和微信短信,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有一次出差做语言保护的工作,上飞机前跟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微信往来不断,一直到不得不关机的时候。下飞机了一打开手机,跳出来全是新的要我及时回答的信息,坐在出租车上我们就不断往来讨论着,一直到进了旅馆房间。我于是弱弱地说:“能让我喘息一会儿吗?”对方才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暂时中断了讨论。 说到这里,其实我对三次编纂辞书的经历中所碰到的出版社编辑人员是满怀敬意的。就说广东教育出版社《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编辑组的几位编辑,经常让我钦佩不已。他们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方言专业的书稿,开始的时候大概对稿子上各种各样的符号会一筹莫展。他们在编校的过程中,就靠勤奋的学习,不断的询问,反复的实践,到了最后可以发现稿子里的很多专业问题,包括调值、调号之类的错漏或前后不一致。这个绝非一日之功。在他们面前,我经常有一种自责和歉意,由于我们的疏忽或大意,曾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困难啊!我们不能更小心一点儿吗?文章写成以后,能不能多看几遍,多校对几遍,尽量减少一些错误? 年纪大了,经常喜欢回忆往事。三次与辞书结缘的经历,令我难忘。其中最多想起的还是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那十年(还有1983到1989年编制《中国语言地图集》的那七年)!那时全力以赴,很艰苦但也很充实,很快乐。而且从其他很多分卷本的作者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懂或不知道的东西,有的是单从书本上得不到的。后来听到曾有人议论我说,如果不是这十年付出,我至少可以多写几本书,多写好几篇文章。也许是这样的,但我从来不后悔!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提振我们的学术自信心,是每一个研究人员的天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花掉我中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是值得的。  张振兴研究员 三次与辞书结缘的经历,也使我对各种辞书有感情,对辞书编纂人员也充满敬意。对于任何有责任心的辞书编纂人员来说,辞书一经正式出版就会感到遗憾,总会感到有什么地方有缺陷,有可以进一步改正的地方,恨不得重新再来一遍。所以后来我会以一种很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其他辞书中的一些缺点或毛病。我们不能苛求编纂人员“凡事通”“每事通”,也不能苛求绝对的“周全”,即使名家大师编纂的辞书也难免有瑕疵,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呢!竹子,一般辞书注释都说“茎圆柱形”,可是我们知道福建闽北山区有一种竹子,名叫方竹,茎是方的;西瓜,一般辞书注释也说“果实球形或椭圆形”,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有的地方专门种植一种方形的西瓜,售价比平常西瓜贵几倍;狐狸,辞书上都说“毛通常赤黄色”,不过加拿大北部地区的狐狸,却是通身黑色皮毛的,最近有报道,日本北海道地区也发现了黑色的狐狸;乌鸦,辞书上说“全身羽毛黑色”,俗语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可是南方有的乌鸦其颈部是白的,看上去很像平常见到的喜鹊,曾有报道说澳大利亚甚至有一种白“乌鸦”。还有一般辞书“有、无、在、是”都有一条注释管它们叫动词,这可是动词不动,跟一般语法教科书上说的不一样。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出这些例子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就据此说一般辞书这些条目都说错了。 世上万物,千奇百怪,辞书只能注释常例,不能顾及特例和例外。近日读《北京晚报》2017-10-20第39版有盛文强《夔一足》一文,颇有意思。该文引《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为夔。 这里的夔是一只脚的神兽,故名“夔一足”,并世代相传。但《吕氏春秋·察传》载有一则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讨论了“夔一足”的问题: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这里孔子一下子把一只脚的神兽“夔”,变成一个能正六律,和五声的乐正“夔”,是说得一个乐正“夔”就足够了,跟一只脚的“夔”没有关系。 要是我们编辞书,碰到“夔一足”,怎么下注?如果以《山海经 ·大荒东经》为据,当注为“一只脚的神兽”;如果以《吕氏春秋·察传》为据,当注为“传说为古人名”。查《汉语大词典》“夔一足”条,就是以《吕氏春秋·察传》为据,并引成语“一夔而足”为证加注的。这个大概差不多。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赵世开:我的语言学之路
- 下一篇:张伯江:文风问题的学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