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传统抒情向“个人话语”的诗意嬗变——浅析《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2017/2018年卷)
http://www.newdu.com 2025/09/13 05:09:46 文艺报 杨瑞芳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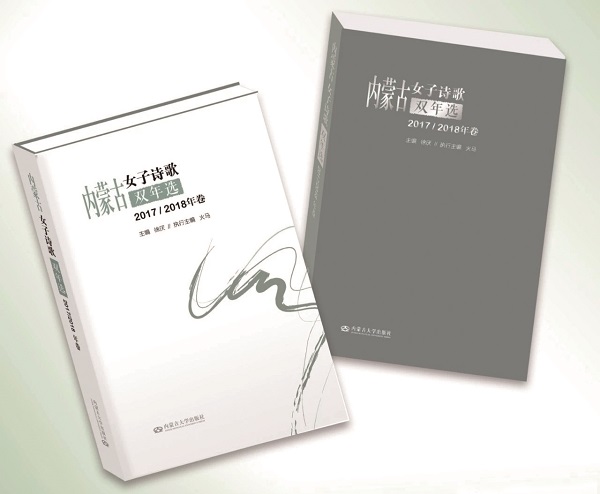 2019年,诗人徐厌策划、主编的《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2017/2018年卷)(以下简称《双年选》)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次关于女性诗歌的一次地域性大汇总。在“选本”文学泛滥的今天,本书能够立足地域、立足女性,无疑为“蒙地”诗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本范例。探析内蒙古诗歌创作,无论男性诗人还是女性诗人,始终有一股强劲的草原风在他们的头顶盘旋,有一种深切的关注与忧伤注入了草原的内核,如诗人、诗评家刘永所说,“草原话语对于内蒙古诗人而言,是一个宿命般的标识”。草原作为一个特定的地域标识早已在“蒙地”诗人们心中生根发芽,无论时隔多久、无论走出多远,草原是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的标引存在于他们心灵世界的。 纵观《双年选》文本,具有很高辨识度的地域性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草原传统的抒情因子仍是“蒙地”女诗人们选择的一个重要范式,民族文化仍是其重要的精神根脉和创作源泉。诗人们醉心于草原山川风貌的描摹并生发出生命咏叹式的讴歌,如崔荣对当代内蒙古诗歌的评价,“构建草原诗歌,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符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草原的生态环境引起了诗人们的普遍关注,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具有悲悯情怀的女性诗人以其精微观察与深刻体验直逼现实、直击人心,观照与慈悲、伤痛与追问构成了其诗歌的深度和力度,丝毫不逊于男性诗人们幽深刻骨的理性思辨,这是一种共时性的社会认同或集体情绪,尤其表现在8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群体中。如高金鹰的《命运》: 桑宝利格草原/半片儿半片儿的雪地/羊儿的毛呼着冬的风/用劲啃着地皮/它们走过雪地/逆转方向/我看见一卡车的羊/被拉进城里 这是现实的镜头,诗人冷静地处理着眼中所见,羊儿生存的艰难,以及等待它们的残酷命运。在草原,我们感受洁白羊群美感的同时,是否眼睛向下,是否感受到诗人为我们呈现出来的生命的无奈与悲壮。诗人仿佛是一个走入历史深处的孤独者,她正凝视着草原的羊群,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情境性述说,而是带着现代人的焦虑对草原生命的理性洞悉和由此及彼的关切与审视。 诗是存在忧患意识的,正如杨匡汉先生所说,“一旦诗人意识到历史的必然法门和人自身生命运动及其现实实践活动之间无法规避的冲突的时候,生命的困惑和体验的痛苦便开始折磨着他。”(《中国新诗学》)诗人在这里感受到的正是来自现实与想象差距的煎熬。辽阔的草原从历史走向现代,那种渗透到骨子里的草原情结仍在跳跃闪烁,但在这片“草原”上,诗人却无法行走,草原的空间感被延伸到时间的纵深中,这种内省的智慧和“与忧俱生”的情怀也随着心灵的折射,演化为一种“怨而不怒”型的含泪的低吟。 比较新中国成立后诗人们对于草原的尽情讴歌,《双年选》中诗人们在表达对于草原的钟情时多是忧心忡忡、欲言又止的,如李娜的《戈壁》(节选)、娜仁琪琪格的《我总是在母语的暖流里,流泪满面》、觉斓的《一匹受伤的骆驼》等。女诗人们以一颗赤子之心敏锐地观察着一切、感受着一切,在欣喜草原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同时更多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缅怀和叩问,回应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她们从诗情的角度进行着思考和陈述。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用汉语写作的“蒙地”诗人对“草原文化”逐渐疏离,草原的经典意象和场景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或精神的图腾。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女性诗人往往更侧重于个性化话语方式表达,“日常经验”被瞬间放大,诗人们通过冷静、客观的观察,不动声色地完成对客观生活的写实,并从繁杂的原生态生活中提炼思想,使诗歌从闭合的内在情绪中走出来,真切地敞开并凸显出生存的本象。正如诗人、批评家霍俊明所说,“蒙地的女性诗歌无论是个体日常经验、性别意识还是语言景观乃至时代的总体情势,从未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多元、广阔甚至芜杂、多变而难以进行任何总体性的概括。” 戏剧化叙事 所谓“戏剧化”,就是诗人通过情境戏剧化手段,组织诗歌材料实现叙事的一种技巧。这是诗歌由内心意识转向实境呈现的有效方式,并通过场景设置、人物对白,以及作者与隐性读者和主人公之间的间接对话,来建构自己的诗意世界。21世纪的诗歌写作结束了泛抒情,更多诗人以冷静、客观、深思来模拟着情绪的律动,并通过情境转化完成情感表述。如《双年选》中白晓光的《暮色旅馆》(节选)、王子晗的《写给母亲》(组诗)、弄月之喵的《我,从来处来》等。以大学生诗人陈静怡的《走廊》为例: 黑暗中出现一条/又长又宽的走廊/尽头处有光/光里有门/门上有窗/窗外有纷飞的大雪/有过路的行人/还有向外眺望的我自己 戏剧性的场景布置:黑暗、走廊、光、门、窗、我;窗外,又有大雪、行人。故事是空白的。我也是走廊中的一分子,和门、窗一样,安静地存在着,我生于世界,我融于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文本中褪去了抒情主人公,从另一个层面打开诗歌的一扇窗,通过简约的场景完成了诗意的对接和转化。 日常经验的艺术化处理 在日常经验里,每个人的情感都会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如大哭以伤悲,大笑以开怀,大骂以解恨,甚至用言不及义的穷聊天来印证此刻的无聊……这些经验支离涣散地在生活中漂流,而在诗人的世界中,如果以审美的心态去体验,就会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深层次体验。特别是新时期的女性诗歌,她们在着力表现个体经验时,除了私语式独白,更多倾向于曲折的表达、含蓄的退让,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寻求自我突破。她们一方面从里尔克的“诗歌是经验”的经典表述出发,另一方面又开始关注内心的审视,通过内省的精神品质构筑了主体和客体深深介入的完整经验,从而给精神以自由翱翔的空间。 纵观《双年选》文本,超越“直白地陈述”,把日常经验转化为精神世界的审美形态,这是“个人化写作”的另一种形式。如青蓝格格的《磨刀贴》,读着、读着,就让人很“疼痛”。诗人采用叙述的方法,铺陈了父亲磨刀的过程: 此刻,我一边炖肉/一边看着父亲为我磨刀/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是这样,他一边炖肉/一边磨刀……”“他磨着磨着/就将我磨成一柄/锋利的刃/但我流过多少血,父亲不知道/但我多么腐朽,父亲不知道/就像我并不了解我的父亲,就像我的父亲并不了解/他磨过的/每一柄/刀 诗人以“磨刀”为切入点,在“磨刀”的过程中,“父亲”渐渐老去,“我”也渐渐长大,但让诗人感到“揪心”的是她对于“父亲”并没有多少了解或关注,一种强烈的“虚无感”横亘于文本之中,“人情的虚无”“人的虚无”,即使最亲密的父女,有些事情、有些情感也是虚妄的。 如水孩儿的《今夜你说要来》、唐月的《煮妇说》、曾烟的《波斯菊时光》等,无论写人、叙事、状物,都是透过语言进行“自我”指涉,是混合着诗人激情、策略、幻觉和现实感的书写。 总之,“日常经验”被放大的“个体化写作”是《双年选》女性诗人的显著特征,也是诗歌走下神坛、融入大众生活的具体体现。毋庸置疑,“个体化写作”虽然带来诗歌话语方式的百花齐放,但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一种文体的嬗变。作为诗歌写作者,要真正理解什么是诗歌,无论是传统的“诗言志”“诗缘情”,还是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语言”变革,最终还是要把握现代诗的意识背景、语言态度、精神结构和基本的艺术符号。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蒙地”诗歌,融入固然重要,但强劲的抒情因子还是不应该被摒弃,虽然有些诗人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书写着蓝天、碧草、大漠、荒原……但读完以后感到了千篇一律的失落与遗憾,草原风明显内力不足,只是呈现出了自然的苍茫、荒凉、雄奇等境象,缺乏深刻的“内省”意识,无法给读者带来灵魂的震撼,在某种意义上让抒情变得苍白无力。诗歌是最躁动不安的艺术,也是最智慧的艺术,理性和激情永远同在,无论采用哪种话语方式,平淡或奇崛,但最终都要以深刻的思想支撑起诗意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